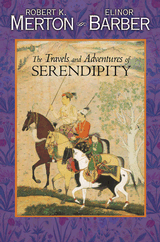李怡
反抗須拒絕手段之惡

存在主義大師沙特和卡繆,在「反抗」的問題上發生分歧,關鍵在於對馬克思主義及蘇聯的態度。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有固定的歷史規律:從原始共產社會,到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到共產社會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最終實現人類的終極理想──共產主義社會。這就是所謂歷史唯物主義。沙特戰後深受影響,卡繆卻一貫反對這種歷史主義。沙特是個哲學家,理念抽象得多,卡繆的哲學思想更多來源於感性生活,直接體驗。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歷史有種看不見的理性,朝向偉大目的前進。儘管過程中充滿暴力、不幸,但是就神聖目的來看,所有苦難都微不足道。卡繆則要揭示這種歷史主義掩蓋了多少苦難,容許了多少罪惡,充滿着多大荒謬。歷史主義的所謂「合理性」,包裹着虛假、殘忍、暴力、死亡,在歷史意義喊得響亮之際,掩蓋了受難者哀號。今天來看,感性體驗似乎勝過抽象思維。
對卡繆而言,反抗必須拒絕手段之惡,目的的崇高,只能藉由手段來檢驗。卡繆1949年的劇作《正直的人》*,故事是:社會革命黨打算用炸彈殺掉俄國的大公,時間到了,投擲炸彈的Yanek Kaliayev,看到大公的小孩在旁邊,所以他沒有下手。第二次,Kaliayev成功殺掉了大公,被逮捕入獄。大公夫人前去談條件,只要他供出同夥,就能獲自由。但是他拒絕;很快地,他被處絞刑。Kaliayev第一次因不願傷害無辜孩子而放棄刺殺;第二次,他寧願被處死,仍堅持拒絕說出同黨。這說明他拒絕「不擇手段」,拒絕為了自我保存而接受「私利的誘惑」。這些拒絕,對抗着荒謬,反抗那些讓正直妥協的力量。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歷史有種看不見的理性,朝向偉大目的前進。儘管過程中充滿暴力、不幸,但是就神聖目的來看,所有苦難都微不足道。卡繆則要揭示這種歷史主義掩蓋了多少苦難,容許了多少罪惡,充滿着多大荒謬。歷史主義的所謂「合理性」,包裹着虛假、殘忍、暴力、死亡,在歷史意義喊得響亮之際,掩蓋了受難者哀號。今天來看,感性體驗似乎勝過抽象思維。
對卡繆而言,反抗必須拒絕手段之惡,目的的崇高,只能藉由手段來檢驗。卡繆1949年的劇作《正直的人》*,故事是:社會革命黨打算用炸彈殺掉俄國的大公,時間到了,投擲炸彈的Yanek Kaliayev,看到大公的小孩在旁邊,所以他沒有下手。第二次,Kaliayev成功殺掉了大公,被逮捕入獄。大公夫人前去談條件,只要他供出同夥,就能獲自由。但是他拒絕;很快地,他被處絞刑。Kaliayev第一次因不願傷害無辜孩子而放棄刺殺;第二次,他寧願被處死,仍堅持拒絕說出同黨。這說明他拒絕「不擇手段」,拒絕為了自我保存而接受「私利的誘惑」。這些拒絕,對抗着荒謬,反抗那些讓正直妥協的力量。
《卡繆全集:戲劇卷:正義者》1950 (序寫於1949)
PARIS
Beguiled, divorcèd, wrongèd, spited, slain!
Most detestable Death, by thee beguiled,
By cruel, cruel thee quite overthrown!
O love! O life! Not life, but love in death.
《卡繆全集:戲劇卷:信奉十字架》1953改編自
《卡繆全集:戲劇卷:信奉十字架》1953改編自
- La devoción de la Cruz (Devotion to the Cross) (1637) 原劇
one of his most famous plays, La Vida es sueño, Life is a Dream, in which Segismundo claims:
¿Qué es la vida? Un frenesí.¿Qué es la vida? Una ilusión,
una sombra, una ficción,
y el mayor bien es pequeño.
¡Que toda la vida es sueño,
y los sueños, sueños son!
Translation:
What is life? A frenzy.
What is life? An illusion,
A shadow, a fiction,
And the greatest good is small;
For all of life is a dream,
And dreams, are only dreams.

Caligula and Cross Purpose
by Albert Camus
Paperback, 156 pages
Published 1965 by Penguin Book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bhuDH25_Po
Published on Aug 2, 2013
Two thousand years ago one of history's most notorious individuals was born. Professor Mary Beard embarks on an investigative journey to explore the life and times of Gaius Julius Caesar Augustus Germanicus - better known to us as Caligula.
Caligula has now become known as Rome's most capricious tyrant, and the stories told about him are some of the most extraordinary told about any Roman emperor. He was said to have made his horse a consul, proclaimed himself a living God, and indulged in scandalous orgies - even with his own three sisters - and that's before you mention building vast bridges across land and sea, prostituting senators' wives and killing half the Roman elite seemingly on a whim. All that in just four short years in power before a violent and speedy assassination in a back alley of his own palace at just 29-years-old.
Caligula has now become known as Rome's most capricious tyrant, and the stories told about him are some of the most extraordinary told about any Roman emperor. He was said to have made his horse a consul, proclaimed himself a living God, and indulged in scandalous orgies - even with his own three sisters - and that's before you mention building vast bridges across land and sea, prostituting senators' wives and killing half the Roman elite seemingly on a whim. All that in just four short years in power before a violent and speedy assassination in a back alley of his own palace at just 29-years-old.
Born Gérard Philip[1] in Cannes, France as a teenager Philipe took acting lessons before going to Paris to study at the Conservatory of Dramatic Art. At age 19, he made his stage debut at a theater in Nice and the following year his strong performance in the Albert Camus play, Caligula, brought an invitation to work with the Théâtre national populaire (T.N.P.) in Paris and Avignon, whose festival, founded in 1947 by Jean Vilar, is France's oldest and most famous.
cross–purposes
: a purpose usually unintentionally contrary to another purpose of oneself or of someone or something else —usually used in plural
----
《卡繆全集:散文選I》
《反與正》丁世中譯---可能是Camus很令人動容的22歲少作。丁先生的翻譯很流暢。
《婚禮集》丁世中譯
《西西弗神話》沈志明/譯
《反抗者》呂永真/譯
杜小真、 顧嘉琛/譯,《置身於苦難與陽光之間:加繆散文集》
《反與正》
諷刺 不置可否
靈魂之死
生之愛
反與正
《反抗者》與呂譯同,"適度與過度"一節標題、順序不同
反叛者
形而上學的反叛
歷史 的反叛
反叛和藝術
正午的思想
適度與過度
《置身於苦難與陽光之間:加繆散文集》 :《反抗者》末段 (頁223-24),遠比呂譯好得多
.......在一個人終於誕生的時刻,必須留下時代和他青春的狂怒。弓在緊張狀態的頂點馬上將射出最沉重又最自由的一箭。
----
郝明義Rex How的相片。
我讀卡繆的《反抗者》,看到他談反抗和憤恨的不同;以及反抗和革命的不同。
憤恨是一種被欺侮之後,感受到自己的無能為力,對欺壓自己的人會產生嫉妬,並渴望有朝一日目睹對方遭受痛苦而暗自欣喜。所以卡繆說這是「一種有害的分泌」。
反抗則不是。在被欺侮到一個臨界點之前,反抗者也只是沉默無語。但他心裡會告訴自己:到這裡我還可以接受,你 可別再來了。而一旦對方超越某個界限之後,反抗者就會說「不」。所以,何謂反抗者?卡繆說,就是一個說「不」的人。然而,反抗者在說「不」的時候,其實也 是在說「是」:他所相信的「是」,或者說要的「是」。並且,就算他說不清楚,他可以體會到這種「是 」還涉及一種超越其個人之上的價值觀。而反抗者的原則僅止於拒絕接受侮辱,但並不去侮辱對方。因此,卡繆說這種反抗是「脫離現狀,打開閘門讓停滯的水傾瀉 而下。」
憤恨是一種被欺侮之後,感受到自己的無能為力,對欺壓自己的人會產生嫉妬,並渴望有朝一日目睹對方遭受痛苦而暗自欣喜。所以卡繆說這是「一種有害的分泌」。
反抗則不是。在被欺侮到一個臨界點之前,反抗者也只是沉默無語。但他心裡會告訴自己:到這裡我還可以接受,你 可別再來了。而一旦對方超越某個界限之後,反抗者就會說「不」。所以,何謂反抗者?卡繆說,就是一個說「不」的人。然而,反抗者在說「不」的時候,其實也 是在說「是」:他所相信的「是」,或者說要的「是」。並且,就算他說不清楚,他可以體會到這種「是 」還涉及一種超越其個人之上的價值觀。而反抗者的原則僅止於拒絕接受侮辱,但並不去侮辱對方。因此,卡繆說這種反抗是「脫離現狀,打開閘門讓停滯的水傾瀉 而下。」
卡繆從西方的「形而上的反抗」,也就是對神性的反抗談起,一路來到「歴史性的反抗」,主要是近代由國家主義而馬克思思想與蘇維埃革命,一直到法西斯主義所涉及的反抗。所以另有一點很有意思的是,他拿「反抗」和「革命」,尤其蘇維埃革命的對比。
首先,如他所說,所有的「反抗」之開始,都是超越個人,為某個可能還說不清的價值觀而採取的行動。但偏偏在蘇維埃革命所標舉的唯物歴史哲學思想中,「價值觀是行動最後獲得的結果」。
此外,他也提醒我們:「評論每一次反抗的行動或結果時,都要檢視它是否忠於崇高的初衷,或是疲軟或變了調,乃至於忘記初衷,沉陷於殘暴專制與奴役。」
《反抗者》不是一本容易讀的書。但是一本值得讀的書,尤其如果你願意照著書裡提到的諸多線索對應著讀。
最後就引一段他話吧:
「在我們每天遭受的試煉中,反抗的角色就如同『我思』(cogito)在思維範疇裡起的作用:它是首要明顯的事實。這個事實讓人擺脫孤獨的狀態,奠定所有人首要價值的共通點。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首先,如他所說,所有的「反抗」之開始,都是超越個人,為某個可能還說不清的價值觀而採取的行動。但偏偏在蘇維埃革命所標舉的唯物歴史哲學思想中,「價值觀是行動最後獲得的結果」。
此外,他也提醒我們:「評論每一次反抗的行動或結果時,都要檢視它是否忠於崇高的初衷,或是疲軟或變了調,乃至於忘記初衷,沉陷於殘暴專制與奴役。」
《反抗者》不是一本容易讀的書。但是一本值得讀的書,尤其如果你願意照著書裡提到的諸多線索對應著讀。
最後就引一段他話吧:
「在我們每天遭受的試煉中,反抗的角色就如同『我思』(cogito)在思維範疇裡起的作用:它是首要明顯的事實。這個事實讓人擺脫孤獨的狀態,奠定所有人首要價值的共通點。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
作品リスト
小説
- 1942年 『異邦人』
- 1947年 『ペスト』
- 1956年 『転落』
- 1957年 『追放と王国』(短編集)
- 1971年 『幸福な死』 - 『異邦人』の初期草稿で、1936年から1938年にかけて執筆された。大筋は完成していたが放棄され、カミュの死後に刊行された。
- 1994年 『最初の人間』 - 1950年代半ばに構想し、1959年から執筆を開始したが、翌1960年にカミュが交通事故により早世したため未完に終わった遺作
戯曲
- 1936年 『アストゥリアスの反乱』 - 3人の友人との合作
- 1944年 『カリギュラ』
- 1944年 『誤解』
- 1948年 『戒厳令』
- 1949年 『正義の人びと』
- 1953年 『十字架への献身』 - スペインの作家ペドロ・カルデロン・デ・ラ・バルカの神秘劇の翻訳
- 1953年 『精霊たち』 - 16世紀の劇作家ピエール・ドゥ・ラリヴェイ作のコメディア・デラルテの翻案
- 1955年 『ある臨床例』 - ディーノ・ブッツァーティ作の小説の翻案
- 1956年 『尼僧への鎮魂歌』 - ウィリアム・フォークナー作の小説の翻案
- 1957年 『オルメドの騎士』 - 16-17世紀スペインの劇作家ローペ・デ・ベーガ作の戯曲の翻訳
- 1959年 『悪霊』 - ドストエフスキーの小説の翻案
エッセイ、評論など
- 1936年 『キリスト教形而上学とネオプラトニズム』 - 学位論文
- 1937年 『裏と表』
- 1939年 『結婚』
- 1942年 『シーシュポスの神話』
- 1943年 - 1944年 『ドイツ人の友への手紙』
- 1951年 『反抗的人間』
- 1954年 『夏』
- 1957年 『ギロチン』
小說
- 《異鄉人》,或《局外人》("L'Étranger")(1942)
- 《鼠疫》,或《瘟疫》("La Peste")(1947)
- 《墮落》,或《墜落》("La Chute")(1956)
- 《快樂的死》("La Mort heureuse")(1936-1938年間完成,逝世後於1971年出版)
- 《第一人》,或《最初之人》("Le premier homme")(未完成,逝世後於1995年出版)
短篇故事
- 《放逐和王國》("L'exil et le Royaume")(短篇小說集)(1957)
- 〈成熟的女人〉("La Femme adultère")
- 〈困惑靈魂的叛變〉("Le Renégat ou un esprit confus")
- 〈沉默之人〉("Les Muets")
- 〈賓客〉( "L'Hôte")
- 〈喬那斯或工作中的藝術家〉("Jonas ou l'artiste au travail")
- 〈石頭在長〉("La Pierre qui pousse")
劇作
- 《卡里古拉》("Caligula")(四幕劇)(1938年完成,1945年演出)
- 《修女安魂曲》("Requiem pour une nonne",改編自福克納的同名小說)
- 《誤會》("Le Malentendu")(三幕劇)(1944)
- 《圍城狀態》("L'Etat de Siege")(1948)
- 《義人》("Les Justes")(五幕劇)(1949)
- 《附魔者》("Les Possédés",改編自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同名小說)(1959)
論文
- Create Dangerously (Essay on Realism and Artistic Creation) (1957)
- The Ancient Greek Tragedy (Parnassos lecture in Greece) (1956)
- The Crisis of Man (Lecture at Columbia University) (1946)
- Why Spain? (Essay for the theatrical play L' Etat de Siege) (1948)
- Reflections on the Guillotine (Réflexions sur la guillotine) (Extended essay, 1957)
- Neither Victims Nor Executioners (Combat) (1946)
論文集
- 《存在,反抗與死亡》(1961)
- Lyrical and Critical Essays (1970)
- Youthful Writings (1976)
- Between Hell and Reason: Essays from the Resistance Newspaper "Combat", 1944–1947 (1991)
- Camus at "Combat": Writing 1944–1947 (2005)
- Albert Camus Contre la Peine de Mort (2011)
散文集、札記
- Christian Metaphysics and Neoplatonism (1935)
- 《反與正》("L'envers et l'endroit")(1937)
- 《婚禮》("Noces")(1938)
- 《薛西弗斯神話》("Le Mythe de Sisyphe")(1942)
- 《反抗者》("L'Homme révolté")(1951)
- 《夏天》("L'Été")(1954)
- 《時事集》
- 一,評論集("Chroniques"),1944 - 1948(1950年出版)
- 二,評論集("Chroniques"),1948 - 1953
- 三,阿爾及利亞評論集("Chroniques algériennes"),1939 - 1958(1958年出版)
- 《卡繆札記》("Carnets")
- 一,1935/2 - 1942/2 (1962)
- 二,1943-1951 (1965)
- 三,1951-1959 (2008)
- 《致德國友人書》("Lettres à un ami allemand",給Louis Neuville)(1948)
作品在台灣的出版
- 卡繆的作品「異鄉人」
- 王潤華/譯,《異鄉人》,台南市:中華,1966年初版、1968年再版。
- 尚適/譯,《異鄉人》,台中市:義士,1974年初版。
- 孟祥森/譯,《異鄉人》,台北市:牧童,1977年再版。
- 鍾文/譯,《異鄉人》,台北市:遠景,1981年初版。
- 康樂意/譯,《異鄉人:荒謬的存在》,台北市:萬象,1994年。
- 莫渝/譯,《異鄉人》,台北市:志文,1994年再版、1997年、2004年。
- 不著譯者,《異鄉人》,台北市:萬象,1998年。
- 林凱慧/譯,《異鄉人》,台北市:人本自然文化,1999年初版。
- 阮若缺/譯,《異鄉人》,台北市:天肯文化,1999年。
- 鍾文/譯,《異鄉人》,台北市:錦繡,1999年。
- 柔之/譯,《異鄉人》,台北市:小知堂文化,2000年。
- 莫渝/譯,《異鄉人》,台北市:桂冠,2001年。
- 李淑貞/編譯,《異鄉人》,台北市:經典文庫,2002年。
- 雨陶/編譯,《異鄉人》,台北縣中和市:華文網出版,2003年。
- 張一喬/譯,《異鄉人》,台北市:麥田,2009年。
- 卡繆的作品「瘟疫」
- 周行元/譯,《瘟疫》,台北市:志文,1969年初版。
- 徐蘋/譯,《黑死病》,台北市:世界文物,1970年。
- 李怡/譯,《瘟疫(黑死病)》,台南市:文言,1983年。
- 顧梅聖、徐志仁/譯,《大瘟疫》,台北市:業強,1994年。
- 顧方濟、徐志仁/譯,《鼠疫》,台北市:林鬱出版,1994年。
- 孟祥森/譯,林燿德/導讀,《瘟疫》,台北市:桂冠,1995年。
- 周行之/譯,《瘟疫》,台北市:志文,1998年再版。
- 諾貝爾文學編譯委員會,《卡繆:黑死病》,環華館,2002年。
- 顏湘如/譯,《鼠疫》,台北市:麥田,2012年。
- 卡繆的雜文集、札記與哲學作品
- 沙特、卡繆/同撰,何欣/主編,《從存在主義觀點論文學》,台北市:環宇,1971年。
- 劉俊餘/譯,《反抗者》,台北市:三民書局,1972年。
- 溫一凡/譯,《卡繆雜文集:抵抗、反抗與死亡》,台北市:志文,1979年初版、1985年、1990年。
- 張伯權、範文/譯,《卡繆札記》,台北市:楓城出版社,1976年、1981年第4版、1986年、1988年、1991年。
- 張伯權、範文/譯,《卡繆札記》,台北市:萬象出版社,1998年。
- 楊耐冬/譯註,《卡繆語錄:存在主義大師之壹》,台北市:漢藝色研出版,1994年。
- 黃馨慧/譯,《卡繆札記I》,台北市:麥田,2011年。
- 卡繆的其他作品
- 何欣/譯,《放逐與王國》,台北市:晨鐘,1970年、1975年。
- 戴維揚、黃美序/同譯,《卡繆戲劇選集:柯里古拉、正義之士》,台北市:驚聲文物,1970年、1984年。
- 孟凡/譯,《卡里古拉》,台北市:現代學苑月刊社,1969年。
- 阮若缺/導讀,《卡里古拉》,台北市:桂冠,1994年。
- 廖學宗/譯,《墮落》,台北市:正文,1973年。
- 陳山木/譯,《墮落》,台北市:水牛,1977年再版。
- 孟祥森/譯,《墮落》,台北市:遠景,1983年。
- 不著譯者,《墮落》,台北市:萬象,1992年初版。
- 徐進夫/譯,《快樂的死》,台北市:晨鐘,1973年。
- 傅佩榮/譯,《西齊弗神話》,台北縣新店市:先知,1976年。
- 張漢良/譯,《薛西弗斯的神話》,台北市:志文,1991年再版、1998年、2001年。
- 郭宏安/譯,《局外人》,台北市:林鬱出版,1994年。
- 顏湘如/譯,《局內局外》,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2000年初版。
- 《局外人》、《局內局外》即異鄉人,譯名不同。
- 出版社編輯室/譯,《災難》,台北縣中和市:兆瑞出版,2003年初版。
- 吳錫德/譯,《第一人》,台北市:皇冠出版,1997年初版。
-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編譯委員會/編,《卡繆(1957)》,台北市:九華出版:環華發行,出版年份沒有註明。
- 石武耕/譯,吳坤墉/校閱, 《思索斷頭台》,高雄市,無境文化,2012
作品在中國大陸的出版
- 杜小真、顧嘉琛/譯,《置身於苦難與陽光之間:加繆散文集》,上海市: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年。 la pensée de Midi, 翻譯為正午思想
- 袁莉、周小珊/譯,《第一個人》,南京市:譯林出版社,1999年。
- 柳鳴九、沈志明/主編,《加繆全集》(全四卷),石家莊:河北教育,2002年。
- 杜小真/譯,《西西弗的神話》,北京:西苑,2003年。
- 郭宏安、顧方濟、徐志仁/譯,《局外人‧鼠疫》,譯林出版社,2007年。
- 劉瓊歌/譯,《西西弗的神話》,光明日報出版社,2009年。
- 楊榮甲、王殿忠等人/譯,《加繆全集》,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年。
- 呂永真/譯,《反抗者》,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年。 la pensée de Midi,翻譯為南方思想
- 沈志明/譯,《西西弗神話》,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年。
- 柳鳴九/譯,《局外人》,浙江文藝出版社,2010年。
- 不著譯者,《局外人》,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年。
- 劉方/譯,《鼠疫》,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年。
- 郭宏安/譯,《西緒福斯神話》,新星出版社,2012年。
Jean-François Mattéi (dir.), Jean-Pierre Ivaldi, Frédéric Musso, Louis Martinez et al., Albert Camus & la pensée de Midi, Nice, Ovadia, coll. « Chemins de pensée », 2008 (ISBN 9782915741308)
midi
Pronunciation: /midi/
m
3le Midi the South of Fra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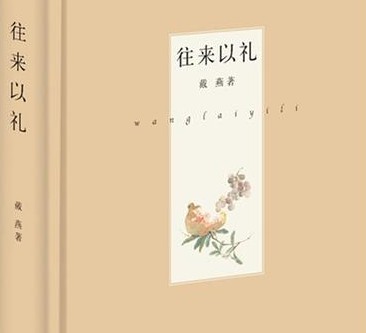

 更多資料
更多資料





 James C. Abegglen for nearly half a century has been in the forefront of Western efforts to analyze the institutions of the Japanese economy, both as a consultant (he represented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for many years, then started his own Asia Advisory Service K.K.) and as a scholar (until recently he was professor of business at Sophia University). In the process his name becam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 term that, slightly modified, has become the name of our magazine. We assigned former J@pan Inc contributing editor Bradley Martin, who is now Tokyo bureau chief for Asian Financial Intelligence (AFI.com), to interview Dr. Abegglen. Excerpts from the interview follow:
James C. Abegglen for nearly half a century has been in the forefront of Western efforts to analyze the institutions of the Japanese economy, both as a consultant (he represented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for many years, then started his own Asia Advisory Service K.K.) and as a scholar (until recently he was professor of business at Sophia University). In the process his name becam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 term that, slightly modified, has become the name of our magazine. We assigned former J@pan Inc contributing editor Bradley Martin, who is now Tokyo bureau chief for Asian Financial Intelligence (AFI.com), to interview Dr. Abegglen. Excerpts from the interview follow: Was it hard to get citizenship?
Was it hard to get citizenshi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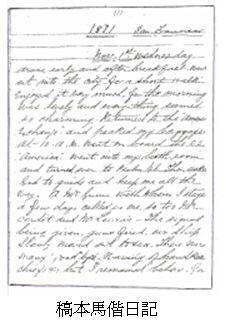
![[item image] [item image]](http://ia700305.us.archive.org/34/items/blackbeardedbarb00macg/blackbeardedbarb00macg.gif?cnt=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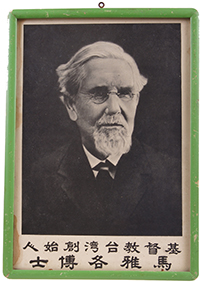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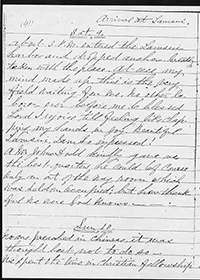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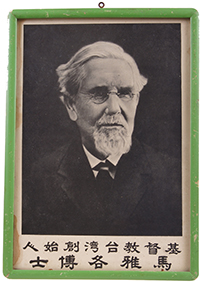










 (2013-06-19 19:19:24)
(2013-06-19 19:19:24)









 叢書名稱:
叢書名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