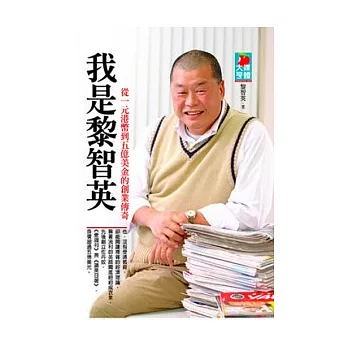1996 年6 月23 日作者孫康宜與施蟄存的合影。(本文圖片均由作者本人提供。)
施蟄存的詩體回憶:《浮生雜詠》八十首
作者:孫康宜
一九七四年,施蟄存先生七十歲。 那年他“偶然發興”,想動筆寫回憶錄《浮生百詠》,“以志生平瑣屑”。1 那年正是他自一九五七年(因寫了一篇雜文《才與德》、 以“極惡毒的誣衊歪曲國家幹部”的罪名)被打成右派、又在文革期間被打成牛鬼蛇神以來的第一次“解放”。我在此之所以美其名曰“解放”,是因為七十歲的施先生被迫從華東師大的中文資料室退休了。那時他身體還很好,精力也十分充沛。但他們硬把他送回家,還祝頌他“晚年愉快”。當時他曾寫詩一首, 以記其事:“謀身未辦千頭橘,歷劫猶存一簏書。廢退政需遮眼具,何妨幹死老蟫魚。” 2 (後來1978 年7月他又復職了,此為後話)。
——————————————
*我要感謝沈建中先生供給有關施蟄存先生的寶貴資料。 同時,在撰寫文章的過程中,我曾得到陳文華教授的大力協助。我的博士生淩超在查考資料方面也幫了大忙。 此外,我要感謝林宗正教授、范銘如教授、黃進興博士等人的鼓勵和啟發。
1.《浮生雜詠》最初在《光明日報》連載發表,但最初刊印書籍是1995 年3 月施先生的散文集《沙上的腳跡》。見施蟄存,《沙上的腳跡》(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 190-219 頁。參見施蟄存,《北山樓詩》(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第125-183 頁。並見《浮生雜詠八十首》,《北山樓詩文叢編》,劉淩、劉效禮編,《施蟄存全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2 年),第10 卷,第133-155 頁。
2.《北山樓詩》,見《北山樓詩文叢編》, 《施蟄存全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2 年),第10 卷,第119 頁;並見《世紀老人的話:施蟄存卷》,林祥主編,沈建中採訪(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17 頁。
必須說明,在這之前那段漫長的二十年間,施先生先後被迫到嘉定、大豐勞動改造,文革時又被撤去原來的教授職務、學銜和工資, 最後才被貶到中文系數據室去搬運圖書、打掃衛生的。在那段期間, 紅衛兵不僅查抄了他的家產和藏書,還屢次把他推上批鬥台。 挨批鬥時,他的帽子被打落在地上, 他就從容地撿起來再戴上;被人推倒在地上,就“站起來拍拍衣服上的塵土,泰然自若地挺直站好並據理力爭。” 被剃了陰陽頭,卻連帽子也不帶,照樣勇敢地由家裡步行到華師大。有一次,紅衛兵突然沖進他家,他挨了當頭一棒,頓時血流滿面, 晚間疼痛得無法入睡,於是他“想了很多”,又“咬咬牙,就熬過來了”。 3
這樣一個百般受辱、一路走過“反右”及“文革”風潮的倖存者, 會寫出怎樣的回憶錄呢?當然, 上個世紀的七十年代, 施先生還沒有恢復發表文章和任何著作的權利。但如果我們聯想到八十年代初中國大陸那種傷痕文學的狂潮,我們一定會猜想:那個一向以文學創作著稱的施蟄存至少會寫一本“傷痕文學”式的回憶錄——或者題材類似的自傳小說吧!但與多數讀者的想像不同,施蟄存並沒有那樣做。他不想把精力放在敘說和回憶那種瑣碎的迫害細節。一直到九十六歲高齡, 在一次採訪中, 他還說道:
“……我卻想穿了,運動中隨便人家怎麼鬥我,怎麼批我, 我只把自己當作一根棍子,任你去貼大字報,右派也好, 牛鬼蛇神也好,靠邊站也好,這二十年[指1957-1977] , 中國知識份子的坎坷命運,原也不必多說, 我照樣做自己的學問。……文革前期, 在‘牛棚’度春秋的日子裡,我不甘寂寞,用七絕作了許多詩,評述我所收集碑拓的由來、典故、價值及賞析,後來我把這些‘牛棚戰果’編成約二萬字的《金石百詠》。” (沈建中採訪)。4
與撰寫《金石百詠》相同,當初1974 年施老開始想寫《浮生雜詠》時, 也是因“不甘寂寞”而引起的。本來他也計畫寫一百首(原來的題目是“浮生百詠”),但那年卻只作得二十餘首,因為“忽為家事敗興、擱筆後未及續成。”一直到十五年後、 八十五歲時, 施老才終於有機會續成該詩體回憶錄, 並將“百詠”改成“雜詠”。他曾在“引言”中解釋道:
“……荏苒之間, 便十五年, 日月不居, 良可驚慨。今年欲竟其事, 適《東風》編者來約稿, 我請以此詩隨時發表, 可以互為約束, 不便中止。但恐不及百首, 遽作古人。又或興致蓬勃, 卮言日出, 效龔定庵之《己亥雜詩》, 皆未可知。故題以《雜詠》, 不以百首自限。作輟之間、留有餘地也。一九九0 年一月三十日,北山施蟄存記。”5
後來《浮生雜詠》寫畢,卻只有八十首。這是因為他寫到八十首的時候, 才發現只寫完一九三0年代在上海之文學生活(即中日抗戰前夕), 而往後的數十年大半生卻無法在二十首詩中寫盡,所以他只得擱筆:
“……以後又五十餘年老而不死,歷抗戰八年、內戰五年、右派兼牛鬼蛇神二十年。可喜、可哀、可驚、可笑之事、非二十詩所能盡。故暫且輟筆,告一段落。一九九0年除夕記。”6
誠然,對施蟄存來說,把一個人的生命過程分成不同的“段落”來處理,是完全可以的。他曾說過:“因為我的生活‘段落’性很強,都是一段一個時期,‘角色’隨之變換,這樣就形成我有好幾個‘自己’。” 7 但據筆者猜測,施蟄存的《浮生雜詠》之所以在一九三七年抗戰前夕打住,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那是因為在往後的八年抗戰期間——即施先生先後逃難至雲南和福建的期間——他連續寫了大量的詩篇,那些詩歌完全可視為自傳性的見證文學, 無需在《浮生雜詠》中重複。至於在那以後, 內戰相繼而來,接著又有“反右”和“文革”的恐怖風潮,那也正是施老最不願意回憶的一段生活內容。但諷刺的是,那段飽受折辱的後半生卻成為他一生中學問成就最高、作品最多產的一段。他的女弟子陳文華曾感慨地說道:
“被稱為‘百科全書式專家’的施蟄存先生,學識之淵博,涉獵之廣泛,用學貫中西、融匯古今來形容毫不過分。他晚年曾說:自己一生開了四個視窗:東窗是文學創作,南窗為古典文學研究,西窗是外國文學翻譯和研究,北窗為金石碑版之學。施氏‘四窗’在學術界名聞遐邇, 因為,推開每一扇窗戶,我們都能看到他留下的辛勤足跡,品嘗到讓我們享用不盡的累累碩果。”8
不用說,施先生那動人的詩體回憶錄《浮生雜詠八十首》也正在他爐火純青的晚年完成的。雖然那段“回憶錄”主要關於他幼年和青年時代的經驗, 但老人將近一世紀的“閱歷”所凝聚的詩心卻涉及所有“四窗”的內容,其才情之感人,趣味之廣泛,實在令人佩服。
同時,我們應當注意施蟄存為《浮生雜詠八十首》這組詩所選擇的特殊詩體和形式, 尤其因為他是一位對藝術形式體裁特別敏感的作家。在“引言”中他已經提到自己可能在仿效“龔定庵之《己亥雜詩》,皆未可知。” 我想這是作者給我們的暗示。在很大程度上,《浮生雜詠》確實深受龔自珍詩歌的影響,但重要的是,施蟄存最終還是寫出了自己的獨特風格。
首先,施先生的《浮生雜詠》與龔自珍的《己亥雜詩》都採取七言絕句的體裁, 同時詩中加注。對龔自珍而言,詩歌的意義乃在於其承擔的雙重功能:一方面是私人情感表達的媒介,另一方面又將這種情感體驗公之於眾。《己亥雜詩》最令人注目的特徵之一就是詩人本身的注釋散見於行與行之間、詩與詩之間。在閱讀龔詩時,讀者的注意力經常被導向韻文與散文、內在情感與外在事件之間的交互作用。如果說詩歌本身以情感的耽溺取勝,詩人的自注則將讀者的注意力引向創作這些詩歌的本事。因此兩者合璧,所致意的物件不僅僅是詩人本身,也包括廣大的讀者公眾。龔自珍的詩歌之所以能深深打動現代讀者,其奧妙也就在於詩人刻意將私人(private)的情感體驗與表白於公眾(public) 的行為融為一體。在古典文學中很少會見到這樣的作品,因為中國的古典詩歌有著悠久的托喻象徵傳統,而這種特定文化文本的“編碼”與“解碼”有賴於一種模糊的美感,任何指向具體個人或是具體時空的資訊都被刻意避免。但我以為,恰恰是龔自珍這種具有現代性的“自注”的形式強烈吸引了施蟄存。郁達夫也曾指出,中國近代作家作品中的“近代性”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龔自珍詩歌的啟發。 9
——————————————
3.《世紀老人的話:施蟄存卷》,第103-104 頁。
4. 《世紀老人的話:施蟄存卷》,第104-105 頁。
5.《浮生雜詠八十首》引言,《北山樓詩文叢編》, 《施蟄存全集》,第10 卷,第133 頁。
6.《浮生雜詠八十首》附記,《北山樓詩文叢編》, 《施蟄存全集》,第10 卷, 第155 頁。
7.《世紀老人的話:施蟄存卷》,第9 頁。
8.陳文華,《百科全書式的文壇巨擘——追憶施蟄存先生》,見《師魂》(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年),第410 頁。有關“四窗”的定義,這兒可能有些出入。根據1988 年7 月16日香港《大公報》, 施先生曾對來訪者說道:“ 我的文學生活共有四個方面,特用四面窗來比喻:東窗指的是東方文化和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西窗指的是西洋文學的翻譯工作,南窗是指文藝創作, 我是南方人,創作中有楚文化的傳統,故稱南窗。”見 言昭,《北山樓頭‘四面窗’——訪施蟄存》,香港《大公報》,1988 年7月16日。
9.郁達夫,《郁達夫全集》(香港:三聯書店,1982),第5冊。亦見孫文光、王世芸編,《龔自珍研究資料集》(合肥:黃山書社,1984),第248-249頁。
施蟄存在“引言”中已經說明,他在寫《浮生雜詠》詩歌時,“興致蓬勃, 卮言日出,”因而使他聯想到龔定庵的《己亥雜詩》。10 這點非常重要。原來1838 年龔自珍突然遇到一場飛來橫禍, 據說是某滿洲權貴將對他進行政治迫害。為了保身,龔必須立刻離開北京。他當時倉皇出京,連家小都沒帶上。在浪跡江南的漫漫長途中,龔寫下了總共315首七言絕句。出於某種奇妙的靈感,自從龔離開京城以後,他產生了難以遏止的創作衝動,寫詩的靈感如流水般奔湧不息,正如《己亥雜詩》第一首所言:“著書何似觀心賢,不奈卮言夜湧泉。”現在施蟄存的《浮生雜詠》也是在“興致蓬勃、卮言日出”那種欲罷不能的情況中寫就,足見施老也具有同樣的浪漫詩人情懷。唯一不同的是,龔自珍寫《己亥雜詩》那年,他才四十七歲;但施老寫完《浮生雜詠》那年,他已是八十五歲的老人。施蟄存這種在文壇上“永葆青春”的創作力, 大陸學者劉緒源把它稱為一種奧秘的文學“後勁”——那是一些極少數的文壇老將,由於自幼具備特殊的才情和文章素養,早已掌握了自己的“創作個性和審美個性”, 因而展現出來的“強韌而綿長的後勁”。11我想施蟄存的“後勁”還得力于劉緒源先生所謂的“趣味”:劉以為施老的“獨特處和可貴處,就在於一切都不脫離一個‘趣’字。” 12
我想就是這個“趣”的特質使得施先生的《浮生雜詠》從當初模仿龔自珍走到超越前人典範的“自我”文學風格。最明顯的一點就是,施的詩歌“自注”已大大不同于龔那種“散見”於行與行之間、詩與詩之間的注釋。施老的“自注”,與其說是注釋,還不如說是一種充滿情趣的隨筆, 而且八十首詩每首都有“自注”,與詩歌並排;不像龔詩中那種“偶爾”才出現的本事注解。值得注意的是,施先生的“自注”經常帶給讀者一種驚奇感。有時詩中所給的意象會讓讀者先聯想到某些“古典”的本事, 但“自注”卻將讀者引向一個特殊的“現代”情境。例如,我最欣賞的其中一個例子就是第24 首:
鵝籠蟻穴事荒唐,紅線黃衫各擅場。
堪笑冬烘子不語,傳奇志怪亦文章。
第一次讀到這首詩,我以為這只是關於作者閱讀“鵝籠書生”(載于《續齊諧記》)的故事、《南柯太守傳》、《紅線》、《霍小玉傳》、《子不語》等傳奇志怪的讀書報告。但施先生的“自注”卻令我大開眼界:
“中學二年級國文教師徐信字允夫,其所發國文教材多唐人傳奇文。我家有《龍威秘書》,亦常閱之, 然不以為文章也。同學中亦有家長對徐師有微詞,以為不當用小說作教材。我嘗問之徐師,師云此亦古文也,如曰敘事不經,則何以不廢《莊子》。”
才是一個十二、三歲的中學生,已從他的老師那兒學到“傳奇志怪亦文章”的觀點,而且還懂得《莊子》乃是“敘事”文學中的經典作品,也難怪多年之後施先生要把《莊子》介紹給當時的青年人,作為“文學修養之助了”。13
這個有關《莊子》的自注,很自然地促使我進一步在《浮生雜詠》中找尋有關《文選》的任何資料。這是因為,眾所周知,施蟄存於1933年因推薦《莊子》與《文選》為青年人的閱讀書目,而不幸招致了魯迅先生的批評和指責;後來報紙上的攻擊愈演愈烈, 以至於施先生感到自己已成了“被打入文字獄的囚徒。”14 那次的爭端使得施蟄存的內心深受創傷,而且默默地背上了多年的“惡名”。我想,在施老這部詩體回憶錄《浮生雜詠》中大概可以找到有關《文選》的蛛絲馬跡吧?
——————————————
10. 《浮生雜詠八十首》引言,《北山樓詩文叢編》, 《施蟄存全集》,第10 卷,第133 頁。
11. 見劉緒源,《儒墨何妨共一堂》,收入《世紀老人的話:施蟄存卷》,第175-193 頁。
12.劉緒源,《儒墨何妨共一堂》,《世紀老人的話:施蟄存卷》,第191 頁。
13.施蟄存,《〈莊子〉與〈文選〉》,1933 年,10 月8日。見徐俊西主編,《海上文學百家文庫》, 第79卷,《施蟄存卷》,陳子善編,(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0),第366-367 頁。
14. 施蟄存,《突圍》,《申報·自由談》,1933 年10 月29日。
於是我找到了第41 首。詩曰:
殘花啼露不留春, 文選樓中少一人。
海上成連來慰問,瑤琴一曲樂嘉賓。
在看“自注”以前,我把該詩的解讀集中在“文選”一詞(第二行:“文選樓中少一人”)。我猜想,這個“文選”會不會和施先生後來與魯迅的“論戰”有關?至少這首詩應當牽涉到有關《昭明文選》的某個典故吧?還有,蕭統的《文選》裡頭會有什麼類似“殘花啼露不留春”的詩句嗎?
然而,讀了施老的“自注”之後,我卻驚奇地發現,原來作者在這首詩中別有所指:
“創造社同人居民厚南裡,與我所居僅隔三四小巷。其門上有一信箱,望舒嘗以詩投之, 不得反應。我作一小說,題名《殘花》,亦投入信箱。越二周,《創造週報》刊出郭沫若一小札,稱《殘花》已閱,囑我去面談。我逡巡數日,始去叩門請謁,應門者為一少年,言郭先生已去日本。我廢然而返。次日晚,忽有客來訪,自通姓名,成仿吾也。大驚喜,遂共坐談。仿吾言,沫若以為《殘花》有未貫通處,須改潤, 可在《創造週報》發表。且俟其日本歸來, 再邀商榷。時我與望舒、秋原同住,壁上有古琴一張,秋原物也。仿吾見之, 問誰能彈古琴。秋原應之,即下琴為奏一操。仿吾頷首而去。我見成仿吾,生平惟此一次。《創造週報》旋即停刊,《殘花》亦終未發表。”
沒想到,原來“文選樓”是指《創造週報》的編輯室,與昭明《文選》毫無關聯。由於主編郭沫若等人乃是“選文”刊登的負責人,所以施老就發明了這樣一個稱呼:“文選樓”。當年施蟄存只是一個二十一、二歲的大學生,就得到主編郭沫若和成仿吾等人如此的推重,所以施老要特別寫此詩以為紀念。至於他是否有意用“文選”一詞來影射他後來與魯迅之間的矛盾,那就不得而知了。詩歌的意義是多層次的,讀者那種“仿佛得之”的解讀正反映出詩歌的複雜性。施蟄存自己也曾說過:“我們對於任何一首詩的瞭解,可以說皆盡於此‘仿佛得之’的境地。”15 儘管如此,作者的“自注”還是重要的,因為它加添了一層作者本人的見證意味。
作為一個喜愛闡釋文本的讀者,我認為我對施老以上兩首詩有關《莊子》和《文選》的解讀也不一定是捕風捉影。至少我的“過度闡釋”突出了施先生的幽默, 那就是“趣”, 是一種“點到為止”的趣味。他利用詩歌語境的含蓄特質,再加上充滿本事的“自注”,就在兩者之間創造了一種張力,讓讀者去盡情發揮其想像空間。其實,詩歌一旦寫就,便仿佛具有了獨立的生命,對其涵義的闡發也不是作者的原意所能左右或限制的。所以,儘管我對以上兩首詩的揣測之詞或許出於我對施蟄存和魯迅從前那場論戰的過度敏感,但一個讀者本來就有考釋發掘文本的權利。何況我以為詩有別“趣”,有時“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詩歌自有其美學的層面,不必拘泥於本事的局限。我相信,施老也會同意我的看法——在他一篇回答陳西瀅的文章裡(即回答陳君對他那篇解讀魯迅的《明天》的文章之批評),他曾寫道:“也許我是在作盲人之摸象,但陳先生也未始不在作另一盲人……而我要聲明的是:我並不堅持自己的看法是對的,也並不說別人是錯的……我還將進一步說:這不是一個對不對的問題,而是一個可能不可能的問題。” 16
施先生提出的這個“可能不可能的問題”正是我們解讀他的詩歌之最佳策略。而他的詩中“趣味”也會因這樣的解讀方法進一步啟發讀者更多的聯想。我以為,真正能表達施蟄存的“詩趣”的莫過於《浮生雜詠》的第68 首:
粉膩脂殘飽世情,況兼疲病損心兵。
十年一覺文壇夢, 贏得洋場惡少名。
“自注”中說明,此詩的“第三、四句乃當年與魯迅交誶時改杜牧感賦。”據沈建中考證,那兩句詩原來發表於1933 年11 月11 日的《申報·自由談》。在那篇《申報》的文章裡,年輕的施先生曾寫道:“我以前對於豐先生[指魯迅],雖然文字上有點太鬧意氣,但的確還是表示尊敬的,但看到《撲空》這一篇,他竟罵我為‘洋場惡少’了, 切齒之聲儼若可聞。我雖‘惡’,卻也不敢再惡到以相當的惡聲相報了。” 17 令人感到驚奇的是,當年在那種天天被文壇左翼包圍批判、被迫獨自“受難”的艱苦情況中,一個29 歲的青年居然還有閒情去模仿杜牧的《遣懷》詩,而寫出那樣充滿自嘲的詩句。我以為, 年輕的施先生能把杜牧的“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改寫成自己的“十年一覺文壇夢,贏得洋場惡少名”乃為古今最富“情趣”的改寫之一。
——————————————
17. 施蟄存, 《突圍(續)》,《申報·自由談》,1933 年11 月1 日。有關“洋場惡少”,以及近人為施蟄存的正名論,請見王福湘,《“洋場惡少”與文化傳人之辨——施蟄存與魯迅之爭正名論》,《魯迅研究月刊》2013 年第2 期。(該雜誌是北京魯迅博物館主辦出版的)。
更有趣的是,半個世紀之後,85 歲的施老在寫他的《浮生雜詠》第68首時,為了補足一首完整的七言絕句 (第68首), 他不但採用了從前年輕時代所寫的那兩句詩,而且很巧妙地加了上頭兩句:“粉膩脂殘飽世情,況兼疲病損心兵。”這樣一來,施老就很幽默地把讀者引到了另一個層面——那就是性別的越界。他用“粉膩脂殘”一詞把自己比成被社會遺棄的女人, 就如“自注”的開頭所述:“拂袖歸來,如老妓脫籍,粉膩脂殘。”在這裡,他借著一個老妓的聲音,表達了一種在現實生活中難以彌補的缺憾,以及一種無可奈何的心態。“自注”中又說:“自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七年, 混跡文場,無所進益。所得者惟魯迅所賜‘洋場惡少’一名,足以遺臭萬年。”
其實“性別越界”(我在從前一篇文章裡稱為 “gender crossing”)乃是中國傳統文人常用的“政治托喻”手法。18 傳統男人經常喜歡用女人的聲音來抒情,因為現實的壓抑感使他們和被邊緣化的女性認同。但我以為,施蟄存的詩法之所以難得,乃在於他能在傳統和現代的情境中進出自如,他幼年熟讀古代詩書,及長又受“五四”新文學影響, 並精通西洋文學。他不但寫舊詩,也寫新詩。凡此種種,都使得他的詩體亦新亦舊、既古又今。或從內容、或從語言、或從性別的意識,他的詩歌都能提供深入的解讀和欣賞的新視點。可以說,他的詩歌一直是多層次的。
我們也可以用同樣的“多層次”之角度來解讀《浮生雜詠》第67 首。該詩描寫有關當年施先生在被文壇左翼圍攻擊得無處可逃的時候、所遇到的尷尬情境:
心史遺民畫建蘭,植根無地與人看。
風景不多文飯少,獨行孤掌意闌珊。
本來施蟄存自從1932 年3 月被現代書局張靜廬聘請來當《現代》雜誌的主編之後,他已經走上文學生涯最輝煌的道路。在那之前,他早已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將軍的頭》、《鳩摩羅什》、《石秀》等, 接著他最得意的心理小說《梅雨之夕》、以及《善女人行品》也在1933 年先後問世。同時,作為主編,他在上海文壇所產生的影響是空前的。就如學者李歐梵所說:“《現代雜誌》被認為標誌著中國文學現代主義的開始,”“在很多方面,施蟄存似乎都在領導著典型的上海作家的生活方式;而且他因編輯《現代雜誌》獲得了更多的‘文化資本’,從而迅速地在上海文壇成了名。” 19此時,《現代》的聲譽也隨著提高, 而雜誌的銷路“竟達一萬四千份”,令那個現代書局的老闆張靜廬好不開心,20 一直慶倖他聘對了人——從一開始他就想辦一個採取中間路線的純文藝雜誌, 而那政治上“不左不右”的施蟄存正好合乎他心目中的理想。
但沒想到這個“不左不右”的中間路線也正是施蟄存被文壇左翼強烈打擊的主要原因。到了1934 年4 月,《現代》已經快撐不下去了。其實這也是魯迅早已預料到的:“想不到半年,《現代》之類也就無人過問了。”21 據施蟄存後來自述:“我和魯迅的衝突,以及北京、上海許多新的文藝刊物的創刊,都是影響《現代》的因素。從第4卷起,《現代》的銷路逐漸下降,每期只能印二三千冊了。” 22 最後現代書局只好關門, 各位同人也紛紛散夥,所謂“風景不多文飯少,獨行孤掌意闌珊。”所以施先生在第67 首的自注中寫道:
“一九三四年,現代書局資方分裂。改組後,張靜廬拆股, 自辦上海雜誌公司……我與杜衡、葉靈鳳同時辭職。其時水沫社同人亦已散夥,劉呐鷗熱衷於電影事業,杜衡……另辦刊物。穆時英行止不檢,就任圖書什志審查委員。戴望舒自辦新詩月刊。我先後編《文藝風景》及《文飯小品》,皆不能久。獨行無侶,孤掌難鳴, 文藝生活從此消沉……。”
應當說明的是,當時除了《文藝風景》及《文飯小品》以外,還有1935年施先生與戴望舒合辦的《現代詩風》,由脈望出版社出版。施蟄存並出任《現代詩風》的發行人,該雜誌創刊號的扉頁刊有他的撰文《〈文飯小品〉廢刊及其他》,還刊有他的新詩《小豔詩三首》以及他的譯作美國羅蕙兒《我們為什麼要讀詩》(署名“李萬鶴”),此外還刊登了“本社擬刊詩書預告”,可惜《現代詩風》僅出一期就夭折了。
這就難怪《浮生雜詠》第67首把作者當時那種無可奈何的“消沉”心境比喻成一個傳統“遺民”的心態——那是一種類似蘭花“有根無地”的心態:“心史遺民畫建蘭,植根無地與人看。” 施老在自注中進一步解釋道:“南宋遺民鄭所南畫蘭, 有根無地。人問之,答曰:‘地為人奪去。’”
所以,真正的關鍵乃在於:“地為人奪去。”所謂“地”就是一個人的生存空間。諷刺的是,施蟄存和他的現代派友人原來是擁有極大的“生存空間”的。就如李歐梵所說:“這個刊物[指《現代》雜誌]帶異域風的法文標題 Les Contemporains, 顯然是相當精英化的,同時也帶著點先鋒派意味:它是施蟄存這個團體的集體自我意象,這些人自覺很‘現代’。” 23 在現代文學的領域裡,他們無疑曾經佔據了一個最新、最先鋒的領導地位。然而, 當殘酷的現實使他們終於失去“生存空間”時,那對他們心中的打擊也就特別嚴重。1934年 7 月2日,施蟄存給好友戴望舒的信中說到:“這半年來風波太大,我有點維持不下去了,這個文壇上,我們不知還有多少年可以立得住也。” 24
——————————————
18. 见拙作《传统读者阅读情诗的偏见》,《文学经典的挑战》(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1 年),第292-303 页。参见康正果,《风骚与艳情》(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修订版,2001年),第48-57 页。
19. Leo Ou-fan Lee, 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30-132. 參見李歐梵,《上海摩登》,毛尖譯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年),第145, 147 頁。
20. 劉緒源,《儒墨何妨共一堂》,《世紀老人的話:施蟄存卷》,第187 頁。
21. 魯迅致姚克函,1934 年2月 11日,《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5 年),第13 卷,第24頁。
22. 施蟄存,《我和現代書局》,見《沙上的腳跡》,第64 頁。
23. 李歐梵,《上海摩登》,毛尖譯 ,第152 頁。
24. 孔另境編,《現代作家書簡》(上海:生活書店,1936 年),第124頁。並見孔另境編,《現代作家書簡》(廣州:花城出版社,1982 年),第84頁。
這是施先生有生以來體驗到的最大一次“空間”失落。為了生存下去,他必須另找生路。(此為後話。)然而,必須一提的是,施家幾代以來,早已有那種從一處漂泊到另一處的“萍浮”感,而那也正是《浮生雜詠》最重要的主題之一。第16 首寫道,“百年家世慣萍浮,乞食吹簫我不羞,”其實已經概括了他們家的奮鬥史。自注中也說:“寒家自曾祖以來,旅食異鄉,至我父已三世矣。”這就是施蟄存童年時代經常隨家人從一個城市遷居到另一個城市的原因。施家世代儒生,家道清貧。《浮生雜詠》第一首告訴我們,施先生的出生地在杭州水亭址學宮旁的古屋。但四歲時他便隨父母從杭州遷居蘇州烏鵲橋,因為當時剛罷科舉不久,其父施亦政頓失“進身之階”,故只得搬到蘇州以謀得一職。(見第二首:“侍親旅食到吳門,烏鵲橋西暫托根。”)在蘇州時,他的父親曾帶他到寒山寺,指著刻有張繼《楓橋夜泊詩》的碑,教他背誦唐詩,乃為讀古典詩歌之始。(見第6 首:“歸來卻入寒山寺,誦得楓橋夜泊詩。”)。後來,施蟄存8 歲那年,辛亥革命發生,其父因而“失職閒居”,也只得“別求棲止”,最後終於搬到松江。(見第11首:“革命軍興世局移,家君失職賦流離。”)
施先生後來在松江長大,居住了近二十餘年之後,才遷居上海。對於松江,他始終懷有一種深厚的鄉愁情感。《浮生雜詠》第14 首描寫在他幼時、母親每晚“以縫紉機織作窗下”,他在旁“讀書侍焉”的動人情景。(“慈親織作鳴機急,孺子書聲亦朗然。”) 在《雲間語小錄》的“序引”中,25 施先生一開頭就強調:“我是松江人,在松江成長,”雖然他的出生地是杭州。有趣的是,在《浮生雜詠》中,他經常喜歡與那些原本為外來者、最終定居在松江的古代前賢認同。例如,第17 首詩曰:“山居新語曲江篇,挹秀華亭舊有緣。他日幸同僑寓傳,附驥濩落愧前賢。”自注:“元楊瑀著《山居新語》,錢惟善以賦曲江得名,皆杭州人僑寓華亭者,《松江府志》列入《寓賢傳》。”同時,他也喜歡與古代詩人陸機、陸雲二兄弟認同,因為他們是松江人:“俯顏來就機雲裡,便與商人日往還。”(第12首)。自注:“松江古名華亭,陸機、陸雲故里也。”此外,晚年的施先生特別懷念松江的山水勝地——尤其是帶有歷史淵源的景點。例如城西的白龍潭是他一直喜歡提起的。《浮生雜詠》第19首主要在詠歎錢謙益和柳如是定情于白龍潭的故事:
樺燭金爐一水香,龍潭勝事入高唐。
我來已落滄桑後,裙屐風流付夕陽。
自注:“白龍潭在松江城西,明清以來,為邑中勝地。紅蕖十畝,碧水一潭,畫舫笙歌,出沒其間。錢謙益與柳如是定情即在龍潭舟中。牧齋定情詩十首, 有‘樺燭金爐一水香’之句,為松人所樂道。入民國後,潭已汙瀦蕪穢,無複游賞之盛。餘嘗經行潭上,念昔時雲間人物風流,輒為憮然。” 26
但令施蟄存最念念不忘的乃是,他自幼在松江所受的古典文學教育。據《浮生雜詠》第23 首, 他才上小學三四年級時,就能從課文中體會到“清詞麗句”的美妙:“暮春三月江南意,草長花繁鶯亂飛。解得杜陵詩境界,要將麗句發清詞。”所以當他才十來歲時,他早已熟讀古書,也學會作詩。《浮生雜詠》第25首,“自君之出妾如何,隨意詩人為琢磨,”主要記載當年初擬漢魏樂府“自君之出矣”的詩句之情況。他曾說:“我的最初期所致力的是詩……那時的國文教師是一位詞章家,我受了他很多的影響。我從《散原精舍詩》《海藏樓詩》一直追上去讀《豫章集》《東坡集》和《劍南集》,這是我的宋詩時期。那時我原做過許多大膽的七律,有一首云:‘揮淚來憑曲曲欄,夕陽無語寺鐘殘。一江煙水茫茫去,兩岸蘆花瑟瑟寒。浩蕩秋情幾洄澓,蒼皇人事有波瀾。邇來無奈塵勞感,九月衣裳欲辦難。’一位比我年長十歲的研究舊詩的朋友看了,批了一句‘神似江西’,於是我歡喜得了不得,做詩人的野心,實萌於此。”27 又,周瘦鵑主編的《半月》雜誌曾於1921年出版施蟄存為該刊封面《仕女圖》所作的題詞15闋, 一時頗為轟動;那年施先生才17歲。28
——————————————
25. 施蟄存,《雲間語小錄》,沈建中編(上海:文匯出版社,2000),第1頁。
26. 並參見施蟄存,《雲間語小錄》,沈建中編,第43-47頁。
27. 施蟄存,《我的創作生活之歷程》,見應國靖編,《施蟄存散文選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6年),第96 頁。
28. 必須一提,周瘦鵑當時也請杭州才女陳小翠(即天虛我生之女公子)續作9闋,以補足“全年封面畫24 幀之數”;“瘦鵑以二家詞合刊之,題雲《〈半月〉兒女詞。”見施蟄存,《翠樓詩夢錄》,寫於1985 年7 月1日。參見《施蟄存先生編年事錄》, 沈建中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 1921 年9 月21 日條。
半月封面之一
我想,促使施蟄存文學早熟的另一個原因,可能是他從小就喜歡與人訂“文字交”的緣故。他自己說,在松江念中學時“與浦江清過從最密。”兩人經常在一起讀詩寫詩。有一次兩人“共讀江淹《恨》、《別》二賦,”並“相約擬作”。於是浦江清作《笑賦》,年輕的施蟄存作《哭賦》。《浮生雜詠》第26 首曾記載該事:“麗淫麗則賦才難,飲恨銷魂入肺肝。欲與江郎爭壁壘,笑啼不得付長歎。”雖然那次兩人的擬賦並不成功,但施老一直難忘那次的經驗。同時,他也難忘當年與浦江清和雷震同一起游景點醉白池, 三人互相“論文言志,臧否古今”,“日斜始歸”的情景。第21 首詩描寫其中的閒情逸致:
水榭荷香醉白池,納涼逃暑最相宜。
葛衣紈扇三年少,抵掌論文得幾時。
可以說,早在青年時代,施蟄存已經掌握了傳統的古典教育,也學會與人和詩、論詩,這與松江的文化背景不無關係。同時,由於松江的特殊教育制度,他上中學三年級時就已勤讀英文,並大量閱讀外國文學,從此水到渠成,也就打開了從事翻譯西洋文學的那扇窗。
然而他也同時受“五四”新文化的薰陶,所以經常利用課餘時間大量閱讀各種報章雜誌。據《浮生雜詠》第30 首詩的自注,當時他漸漸感到“刻畫人情、編造故事,較吟詩作賦為容易。”儘管還是個中學生,所創作的小說早已陸續刊於《禮拜六》、《星期》等雜誌。(當時他經常署名為“施青萍”或“青萍”。)對他來說,這是他人生“一大關鍵”, 也是“一生文學事業之始。” 不久,他也開始思考如何寫一種“脫離舊詩而自拓疆界”的新詩,以為郭沫若的《女神》頗可作為一種過渡時期的典範新詩, 所以他在《浮生雜詠》第29 首寫道:“春水繁星蕙的風,淩波女神來自東。鳳凰涅盤詩道變,四聲平仄莫為功。”
總之,施蟄存的文學早熟促成了他走向上海文壇的一大關鍵。但人生的際遇也有難以預料的巧合因素。1922那年,施蟄存上杭州之江大學一年級,有一回他與同學泛舟西湖,正好遇到幾位杭州文學社團“蘭社”的主要成員——即戴望舒、戴杜衡、張天翼、葉秋原等。當時這幾位蘭社成員才只是中學四年級生,但已經以文字投寄上海報刊,故與施蟄存一拍即合,遂有“同聲之契”。《浮生雜詠》第32 首寫道:
湖上忽逢大小戴,襟懷磊落筆縱橫。
葉張墨陣鵝堪換,同締芝蘭文字盟。
那次的結盟無疑給了施先生許多新的啟發和動力。不久他們在杭州戴望舒家中聯手籌辦刊物《蘭友》,望舒出任主編,施先生為助編,於1923年一月一日出版創刊號。同時施蟄存也寫《西湖憶語》,在《最小》雜誌連載。同年八月,他自費出版了平生第一部小說集《江干集》(收有《冷淡的心》、《羊油》、《上海來的客人》等多篇介於“鴛鴦蝴蝶派和新文學之間”文體的小說)。29 該集署名施青萍,所收的小說都是他在之江大學肄業那年寫的,因為“之江大學在錢塘江邊,故題作《江干集》”。《江干集》的《卷首語》以十分典雅的古典詩歌形式寫成,同時以“江上浪”做為人生譬喻,獨具魅力:
蹤跡天涯我無定,偶然來主此江干。
秋心寥廓知何極,獨向秋波鎮日看。
世事正如江上浪,傀奇浩汗亦千般。
每因觸處生新感,願掬微心托稗官。
施蟄存20 歲時的處女作《江干集》
晚年的施先生不願把這本集子視為他的第一部小說集,以為尚不成熟,只稱它為一部“習作”。30 但我始終以為施先生這一部處女作在中國文學史上頗有重要性, 尤其它代表一個早期從傳統過渡到現代的文人所經歷的複雜心思。《江干集》有一篇附錄,題為“創作餘墨”,是作者專門寫給讀者看的。它很生動地捕捉了一個青年作家所要尋找的“自我”之聲音:
“我並不希望我成為一小說家而做這一集,我也不敢擔負著移風整俗的大職務而做這些小說。我只是冷靜了我的頭腦,一字一字的發表我一時期的思想。或者讀者不以我的思想為然,也請千萬不要不滿意,請恕我這些思想都是我一己的思想,而我也並不希望讀者的思想都和我相同。我小心翼翼地請求讀者,在看這一集時,請用一些精明的眼光,有許多地方千萬不要說我有守舊的氣味,我希望讀者更深的考察一下。我也不願立在舊派作家中,我更不希望立在新作家中,我也不願做一個調和新舊者。我只是立在我自己的地位,操著合我自己意志的筆,做我自己的小說。” 31
施蟄存手跡
這是時代的影響,同時也是施蟄存本人的文學天分之具體表現。他不久和他的蘭社友人一起到上海去, 他們合力奮鬥了幾年(包括建立文學社團“瓔珞社”和創辦《瓔珞》、《新文藝》等雜誌),最後由於《現代》的空前成就、一躍而成為三十年代初上海文壇現代派的先鋒主力。在他的《浮生雜詠》中,施老花了很大的篇幅回憶這一段難以忘懷的心路歷程。從第33首到66首,我們讀到有關他那不尋常的大學生涯(“計四年之間,就讀大學四所”),還有他與戴望舒、杜衡如何“在白色恐怖中倉皇離校,匿居親友家”的情景,以及他和劉呐鷗刊編《無軌列車》、《新文藝》月刊、 後又開水沫書店的甘苦談,最後他終於得到上海現代書局經理張靜廬的賞識,成為“現代”雜誌的主編,真可謂 “天時地利人和”。(見第61首:“一紙書垂青眼來,因緣遇合協三才。”)。
1923年的《蘭友》,戴望舒主編
可以想見,1934 年當現代書局瓦解、《現代》雜誌同人解散之時,施蟄存和他的青年朋友們(他們都還不到三十歲)有多麼頹喪。難怪施蟄存要說:“獨行孤掌意闌珊。”據他後來自述:1935年, 春節以後,他“無固定職業,在上海賣文為生活。”他曾說:“度過三十歲生辰,我打算總結過去十年的寫作經驗,進一步發展創造道路……以標誌我的‘三十而立’。”32 那時出版界突然流行晚明小品熱, 所以施蟄存就為光明書店編了一本《晚明二十家小品》。但主要還是因為周作人在北京大學作“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之演講,以為新文學“起源於晚明之公安竟陵文派”,因而提高了晚明小品的身價。當時上海書商個個“以為有利可圖”、就紛紛“爭印明人小品。”(參見《浮生雜詠》第69、70、71、72首)。重要的是,周作人當年還為施先生題簽《晚明二十家小品》的封面, 也難怪晚年的施蟄存念念不忘此事:“知堂老人發潛德,論文忽許鍾譚袁。”(見第69 首)。但那次編《晚明二十家小品》曾再次得到魯迅的攻擊:“如果能用死轎夫,如袁中郎或‘晚明二十家’之流來抬,再請一位活名人喝道,自然較為輕而易舉,但看過去的成績和效驗,可也並不佳……五四時代的所謂‘桐城謬種’和‘選學妖孽”,是指做‘載飛載鳴’的文章和抱住《文選》尋字彙的人們的……到現在,和這八個字可以匹敵的,或者只好推‘洋場惡少’和‘革命小販’了罷。” 就在那以後不久,施蟄存開始為上海雜誌公司主編《中國文學珍本叢書》,其中包括《金瓶梅詞話》的標點工作。(見《浮生雜詠》第73、74、75、76 首)。
但1936年6月施蟄存黃疸病復發,故只得離開上海,轉到杭州養病。但這一“養病”卻改變了施先生的人生方向,使他培養了一種寧靜恬適的生活方式。他先在西湖畔的瑪瑙寺(即他所謂的“釋氏宮”)居住月餘。在那兒他整天過著安靜清淡的書齋生活,佛教尤其對他影響深厚。《黃心大師》那篇充滿佛教背景的小說也就在杭州休養的期間寫成。(請注意:小說中的主角黃心大師,閨名原叫“瑙兒”,而他的父母也把她當作“瑪瑙”看待。)34 不久施蟄存從瑪瑙寺轉到附近的行素女子中學執教。從此更是利用課餘的閒暇時光沉浸在欣賞自然風光的樂趣中。正巧行素女中的校園就是清初文人龔翔麟(1658年-1733年)的宅院故址,其“宅旁小園即所謂蘅圃、有湖石名玉玲瓏、宣和花石綱也。” 石旁又有著名的玉玲瓏閣,乃為龔氏藏書之所,而施先生“授課之教室即在閣下”。每回他下了課沒事,就在玉玲瓏旁邊一邊品茶一半欣賞周遭的美景。《浮生雜詠》第78 首正在描寫那種閒適的心境:
橫河橋畔女黌宮,蘅園風流指顧中。
罷講閒居無個事,茗邊坐賞玉玲瓏。
這首詩韻味十足,頗有言外之意。從詩中的優美意境,讀者可以感受到一種大自然的“療傷”功能——可以想見,當年施蟄存雖然懷著“海瀆塵囂吾已厭”的心情離開了上海, 他終於在他的出生地杭州找到了新的生存空間。那是一個富有自然趣味的藝術空間,也是一種心靈的感悟。(同年他也寫出《玉玲瓏閣叢談》一組隨筆, “聊以存一時鴻爪。”)35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杭州養病那年, 他開始了“玩古之癖”——也就是說,他多年後之所以埋首“北窗”(指金石碑版之學), 其最初靈感實來自那次的杭州經驗。《浮生雜詠》第79首歌詠這段難得的因緣:
湖上茶寮喜雨台,每逢休務必先來。
平生佞古初開眼,抱得宋元窯器回。
自注:“湖濱喜雨台茶樓,為古董商茶會之處,我每星期日上午必先去飲茶。得見各地所出文物小品,可即時議價購取。其時,宋修內司官窯遺址方發現,我亦得青瓷碗碟二十餘件,玩古之癖,實始於此。”
1936 年,施蟄存在杭州行素女中
從今日的眼光看來,這樣突然的興趣轉移——從現代派小說轉到“玩古之癖”——令人感到不可思議。但其實這正反映了施蟄存自幼以來新舊兼有的教育背景以及他那進退自如的人生取向。尤其在遭遇人生的磨難時,“進退自如”乃是一種智慧的表現—— 而且,能自由地退出已進入的地方,需要很大的勇氣,這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我想,年輕的施蟄存之所以把《莊子》推薦給當時的青年人,恐怕與他特別欣賞莊子的人生哲學有關。晚年的施先生曾經說過:“我是以老莊思想為養生主的。如古人所說:‘榮辱不驚,看庭前花開花落;去留無意,望天上雲卷雲舒’”。36
這樣的人生哲學使得施蟄存在1937年夏天做出了一個重要的決定:當他看見時局已變,整個文學創作的氣氛已非往昔,他就毅然決定受聘于昆明大學,從此講授古典文學。所以《浮生雜詠》最後以“一肩行李賦西征”為結,從此“漂泊西南矣“。(第80首)。
這就證實了施老所說有關他生命中的“段落”性。誠然,他的生命過程“都是一段一個時期”,而且“角色隨之轉換”。我想這就是《浮生雜詠》的主題之一;當85 歲的施老回憶他那漫長坎坷的人生旅途時,他尤其念念不忘年輕時那段充滿趣味和冒險的文壇生活。那段時光何其短暫,但那卻是他生命中(也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很重要的一段。
——————————————
29. 見沈建中,《遺留韻事:施蟄存遊蹤》(上海:文匯出版社,2007 年),第16-19 頁,有關《江幹集》的介紹和討論。
30. 施先生把小說集《上元燈》(1929年8 月由上海水沫書店初版印行;1932 年2 月由上海新中國書局出版改編本)以前的《江干集》和《娟子姑娘》——包括由水沫書店出版的《追》——都一併視為“文藝學徒的習作”。所以他認為《上元燈》才是他的“第一個短篇小說集”。見施蟄存, 《〈中國現代作家選集·施蟄存〉序》;《十年創作集·引言》。 參見《施蟄存先生編年事錄》, 沈建中編,1929 年8 月、1928 年1月條。又,有關《上元燈》的討論,請見陳國球,《從惘然到惆悵》,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1993年第4期 (11月), 頁83-95; 《文本言說與生活》,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1994年第3期 (8月), 頁180-190。
31. 施蟄存,“《江干集》附錄 《創作餘墨》(代跋),”見《施蟄存序跋》,沈建中編(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3),第31 頁。
32. 施蟄存,《十年創作集·引言》。參見《施蟄存先生編年事錄》, 沈建中編,1935 年1 月條。
33.魯迅(署名“隼”)《五論“文人相輕”—明術》, 見《文學》月刊,第5卷第3號,1935 年9月1日。 必須一提,儘管魯迅一再抨擊他,施先生多年後(即1956年)曾寫 《吊魯迅先生詩》,表達了自己“感舊不勝情,觸物有餘悼”的心情。 其序曰:“余早歲與魯迅先生偶有齟齬,竟成胡越。蓋樂山樂水,識見偶殊;巨集道巨集文,志趨各別。忽忽二十餘年,時移世換,日倒天回。昔之殊途者同歸,百慮者一致。獨恨前修既往,遺跡空存,喬木雲頹,神聽莫及。” 在這首詩中,施蟄存那種坦白、 誠懇的一貫風度被淋漓盡致地表達了出來。(施蟄存, 《吊魯迅先生詩》,見《北山樓詩》,《北山樓詩文叢編》, 《施蟄存全集》,第10 卷,第111 頁)。
34.施蟄存,《黃心大師》,見徐俊西主編, 《海上文學百家文庫》, 第79卷,《施蟄存卷》,陳子善編,第217 頁。
35.見沈建中,《遺留韻事:施蟄存遊蹤》,第29 頁。
36. 陳文華,《百科全書式的文壇巨擘——追憶施蟄存先生》, 見《師魂》,第406 頁。
(初稿載於《從北山樓到潛學齋》, 沈建中編, 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2014;修訂版載于 《從傳統到現代:歷史與批評視角下的近現代詩學轉變》, 林宗正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
孙康宜,美国著名华裔汉学家。原籍天津,1944年生于北京,两岁时随家人迁往台湾。1968年移居美国,曾任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馆长。现为耶鲁大学首任Malcolm G.Chance’56 东亚语言文学讲座教授,曾获美国人文学科多种荣誉奖学金。2015年4月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学院院士。2016年被选为台湾中研院院士。















 Index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Works of Aldous HuxleyAldous Huxley2019年4月25日
Index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Works of Aldous HuxleyAldous Huxley2019年4月25日 LimboAldous Huxley2017年6月11日
LimboAldous Huxley2017年6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