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讀他的中國美術史。90年代初,在哈佛買到他的Norton演講集。幾年前,在台灣大學聽過他一場演講,他當時有點急,想晚年開創著述新局,尤其是利用網路科技。
先生著作的漢譯,台北的石頭出版社有精美的印刷;北京三聯有平價的版本。
----
中國美術史家 高居翰的400 本書
http://jamescahill.info/the-writings-of-james-cahill/books-read
電影筆記
http://jamescahill.info/the-writings-of-james-cahill/movie-notes
---這幾年將它們當禮物送給謝立沛老師
從2009年起 三聯出版他的5本著作 有的台灣有更美麗的版本
高居翰(James Cahill,1926— )教授是美国学界著名的中国绘画史专家。曾长期执教于伯克莱加州大学的艺术史系,并担任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中国艺术部主任。他是最早将海外汉学研究与德国传统的艺术史研究相结合并取得成功的艺术史家,其著作多由在各大学授课时的讲稿修订或充分利用博物馆资源编纂而成,融会了广博的学识与细腻、敏感的阅画经验,皆是通过风格分析研究中国绘画史的典范。1997年,高居翰获得伯克莱加州大学颁发的终生杰出成就奖。
三联书店出版的“高居翰作品系列”共包括五册。其中三册属于他宏大的“中国晚期绘画史”写作计划:《隔江山色:元代绘画 1279-1368 》、《江岸送别:明代初期与中期绘画 1368-1580 》、《山外山:明代晚期绘画 1570-1644 》。另外两册分别是他1979年哈佛大学诺顿讲座、1991年哥伦比亚大学班普顿讲座的讲稿结集:《气势憾人:十七世纪中国绘画中的自然与风格》和《画家生涯:传统中国画家的生活与工作》(即出)。这是高居翰教授的著作首次以比较完整的面貌与大陆读者见面。
隔江山色
序言
導論
第一章 南宋的杭州
徽宗皇家畫院
詩畫對幅
畫院以外的院體畫
沒有詩文的詩意畫
詩之旅
第二章 晚明的蘇州
明前期的詩意畫
題有詩句的立軸
張宏、李士達和盛茂燁
盛茂燁的詩意畫冊頁
明末清代其他詩意畫
第三章 江戶時期的日本
南畫在日本的興起
彭城百川
池大雅
與謝蕪村︰早年生涯
佐貫時期及其後階段的蕪村
贊助人、詩人圈及詩歌理論
蕪村與中國詩歌
蕪村與詩之旅︰晚年作品
注釋
參考書目
HC:這本書的可爭議處很多. 譬如說圖1.32的所謂"絲綸圖"(題目很怪 它有特定的意思)又是連夜紡織又是暮色....
先生著作的漢譯,台北的石頭出版社有精美的印刷;北京三聯有平價的版本。
----
James Cahill, Scholar of Chinese Art, Dies at 87
February 20, 2014
訃告
美國著名中國美術史學者高居翰逝世
2014年02月20日
美國著名中國美術史學者高居翰(James Cahill)周五在加州伯克利家中去世,享年87歲。高居翰對中國美術作品的解讀影響了西方几代學者。
他的女兒薩拉·卡希爾 (Sarah Cahill)說,他因前列腺癌併發症去世。
- 檢視大圖
![1985年,高居翰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 Saxon Donnelly1985年,高居翰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
Saxon Donnelly1985年,高居翰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
高居翰教授從1965年開始到1994年退休前都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任教, 他是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對中國美術作品進行研究和編目造冊的一批著名美術史學家之一。伯克利分校研究中國藝術的白瑞霞 (Patricia Berger)教授說,當時的西方對中國藝術的興趣遠不能與現在相比。白瑞霞曾師從於高居翰。
她說,高居翰教授一開始是和瑞典學者喜仁龍(Osvald Siren)合作,後獨自展開工作,他對中國繪畫精品進行紀錄和拍照,建立起一套正典體系,在此基礎上去理解中國繪畫千百年來的發展。
在對繪畫作品的分析中,高居翰教授通常會儘可能透過畫的筆法來了解一位畫家的性格。這種形式分析演變成為對藝術品鑒定的興趣,而這是中國藝術研究中一個主要課題;中國有臨仿著名作品的傳統,一些臨仿作品本身也被認為是大作。
高居翰教授在1999年曾引發了一場關於作品鑒定的熱烈辯論,當時他說大都會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中國收藏中有一件重要藏品是偽作。
這部作品是據稱出自10世紀畫家董源之手的《溪岸圖》。高居翰教授當時說,此畫可能為張大千所作。張大千是20世紀中國畫家、收藏家以及臨仿大師,他自己的作品也價值連城。
高居翰在大都會博物館的一次內部研討會上提出了自己的結論,他說證據來源於這幅畫的筆法和印章。大都會博物館亞洲藝術部主任何慕文(Maxwell K. Hearn)認為這部作品是真品,至今該畫仍在館內展出,並標為董源作品,而高居翰教授始終認為其作者是張大千。
伯克利藝術博物館(Berkeley Art Museum)亞洲藝術高級策展人、高居翰教授的另一位學生白珠麗(Julia White)說,「我認為這個問題永遠不會有結論。」
何慕文周二在一封郵件中說,現在幾乎沒有學者相信《溪岸圖》是近代仿作。但他讚揚了高居翰教授的合理質疑,稱他是「我們所有人的導師」。
高居翰教授的兒子尼克(Nick)說,父親很享受這樣的爭辯,「不是因為爭議性,而是因為觀點、對話,和如同身臨戰場般的交鋒。」
高居翰1926年8月13日出生於加利福尼亞州的布拉格 堡。他最初是一名語言學家,1946年在日本、1946年到1948年在朝鮮擔任美國陸軍翻譯官,並在那裡萌生了對繪畫收藏的興趣。1950年他在伯克利 分校獲得了東方語言學士學位,後來又在密歇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獲得了藝術史碩士和博士學位。
1954年到1955年,他作為富布萊特(Fulbright)學者在京都大學(Kyoto University)訪學。1956年,他開始在華盛頓的弗瑞爾藝廊(Freer Gallery of Art)擔任中國藝術策展人直至1965年。
1973年,他隨一個藝術史學家代表團首次訪問中國。原本擔心許多作品已經被破壞或者流失到海外的他發現,之前只能在古舊的輯錄里看到的一些畫作,仍然藏於北京。
此後,他頻繁地訪問中國,在中國講課,並與中國的藝術專家見面,也獲得了一睹某些繪畫收藏的機會。
上世紀70年代晚些時候,他開始探究有關藝術的更深層次問題,比如中國的繪畫是否受到了西方形象的影響,他還從研究大師及其技法向外拓展,開始關注曾經被忽略的畫作,比如中國人家中掛着的通俗畫作,這些作品通常出自不知名的畫家。
1978年到1979年,他在哈佛大學(Harvard) 的諾頓講座(Charles Eliot Norton)進行講學。講學內容後出整理出版為《氣勢撼人:十七世紀中國繪畫中的自然與風格》(The Compelling Image: Nature and Styl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ese Painting)一書。
2010年,史密森尼學會(Smithsonian Institution)向高居翰教授頒發了查爾斯·朗·弗瑞爾獎章(Charles Lang Freer Medal),表彰他對亞洲和近東藝術史的終生貢獻。他把自己的許多畫作留給了伯克利藝術博物館。
高居翰與多蘿西·鄧拉普(Dorothy Dunlap) 以及曹星原(Hsingyuan Tsao)的婚姻均以離婚告終。除了他首次婚姻的子女尼克和薩拉,他還和第二任妻子育有兩個兒子——貝內迪克特(Benedict)和朱利安 (Julian)。他還有六個孫輩。高居翰教授去世前剛剛與白珠麗合作,在伯克利藝術博物館舉辦了一次展覽,關注的是清朝(1644-1911)繪畫中的 女性形象。
高居翰的女兒說,他在生命的最後幾個星期里一直卧病在床,但並沒有停下手頭的一部中國繪畫史系列教學視頻的製作。在高居翰的網站上可以看到這些視頻,此外還有一個名為「病榻日誌」(Bedridden Blog)的博客,他在其中回顧了自己人生和病情。
在12月的一篇博文中,高居翰寫道,講課視頻是自己遺產的一部分。他說,「這基本上是一個如何把我腦子裡的東西轉化成一種可以傳播的形式、從而得以保存下來的問題。因為我腦海中儲存了大量的信息、圖像和想法,它們不能被複制到任何一個活着的人的思想里。」
翻譯:張亮亮、王湛James Cahill, one of the foremost authorities on Chinese art, whose interpretations of Chinese painting for the West influenced generations of scholars, died on Friday at his home in Berkeley, Calif. He was 87.
The cause was complications of prostate cancer, his daughter, Sarah Cahill, said.
James Cahill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in 1985.
Professor Cahill, who taught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from 1965 until his retirement in 1994, was among a group of eminent art historians who, from the late 1950s to the 1970s, researched and cataloged Chinese painting. At the time, Western interest in Chinese art was far less than it is today, said Patricia Berger, professor of Chinese art at Berkeley and one of his former students.
Working with the Swedish scholar Osvald Siren and later on his own, Professor Cahill recorded and photographed Chinese masterworks, building a canon on which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ainting over the centuries, Professor Berger said.
In his analysis of paintings, Professor Cahill typically tried to learn as much as possible about the character of an artist from the brushwork. This formal analysis led to an interest in authenticity, a major theme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art; in China, copying revered works is a tradition, and some copies are regarded as masterpieces in their own right.
Professor Cahill set off an explosive debate about authenticity in 1999 when he said a painting that had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s Chinese collection was a fake.
The work, a scroll titled “Riverbank,” was said to be by Dong Yuan, a 10th-century painter. Professor Cahill said it was probably the work of Zhang Daqian, a 20th-century Chinese artist, collector and master forger whose own work sells for millions of dollars.
Professor Cahill presented his conclusions during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at the Met, citing evidence based on the brushwork and seals used in the painting. Maxwell K. Hearn, of the Met’s Asian department, defended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work, and it remains on display at the museum, attributed to Dong Yuan, although Professor Cahill remained convinced that it is by Zhang.
“I don’t think it will be ever finally resolved,” said Julia White, senior curator for Asian art at the Berkeley Art Museum and another student of Professor Cahill’s.
In an email on Tuesday, Mr. Hearn said that few scholars now believe “Riverbank” to be a modern forgery. But he praised Professor Cahill, whom he called “a mentor to us all,” for his healthy skepticism.
Professor Cahill’s son Nick said that his father reveled in such debates, “not for the controversy but for the argument, the dialogue, for the engagement in the field.”
James Francis Cahill was born on Aug. 13, 1926, in Fort Bragg, Calif. Originally a linguist, he worked as an Army translator in Japan in 1946 and in Korea, where he became interested in collecting paintings, from 1946 to 1948. He received his bachelor’s degree in Oriental languages in 1950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and his master’s and Ph.D. in art history from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In 1954 and 1955 he studied at Kyoto University on a Fulbright scholarship. He joined the staff of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in Washington in 1956 and was curator of Chinese art there until 1965.
In 1973 he visited China for the first time as part of a delegation of art historians. Fearing that many works had been destroyed or moved out of the country, he discovered instead that paintings he had been able to see only in old catalogs were still in Beijing.
After that he made frequent visits to China, where he lectured, met with other Chinese art scholars and was given access to painting collections.
Later in the 1970s he began exploring deeper questions about the art, like whether Chinese painting had been influenced by Western images, and he began to branch out from studying the masters and their techniques and look instead at paintings that had been ignored, like the popular works, often by unnamed artists, that Chinese people had in their homes.
In 1978 and 1979 he gave the Charles Eliot Norton lectures at Harvard. They were published as a book, “The Compelling Image: Nature and Styl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ese Painting.”
In 2010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awarded him the Charles Lang Freer Medal for his lifetim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Asian and Near Eastern art. He left many of his own paintings to the Berkeley Art Museum.
His marriages to Dorothy Dunlap and Hsingyuan Tsao ended in divorce. In addition to Nick and Sarah, children from his first marriage, his survivors include two sons from his second, Benedict and Julian, and six grandchildren. At his death Professor Cahill had just completed a collaboration with Ms. White on an exhibition at the Berkeley Art Museum focused on images of women in Chinese painting of the Qing dynasty (1644-1911).
He had been confined to bed in his final few weeks, his daughter said, but he continued to work on a video lecture serie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ainting. It can be seen on his website, where he also reflected on his life and illness in what he called Bedridden Blog.
In a December post, he wrote of the lecture series as one part of his legacy. “Basically,” he said, “it is a problem of how to convert what is in my mind, a great store of information and images and ideas that cannot be duplicated in the mind of anyone else alive, into a communicable form so that it is preserved.”
----中國美術史家 高居翰的400 本書
http://jamescahill.info/the-writings-of-james-cahill/books-read
電影筆記
http://jamescahill.info/the-writings-of-james-cahill/movie-notes
---這幾年將它們當禮物送給謝立沛老師
從2009年起 三聯出版他的5本著作 有的台灣有更美麗的版本
高居翰(James Cahill,1926— )教授是美国学界著名的中国绘画史专家。曾长期执教于伯克莱加州大学的艺术史系,并担任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中国艺术部主任。他是最早将海外汉学研究与德国传统的艺术史研究相结合并取得成功的艺术史家,其著作多由在各大学授课时的讲稿修订或充分利用博物馆资源编纂而成,融会了广博的学识与细腻、敏感的阅画经验,皆是通过风格分析研究中国绘画史的典范。1997年,高居翰获得伯克莱加州大学颁发的终生杰出成就奖。
三联书店出版的“高居翰作品系列”共包括五册。其中三册属于他宏大的“中国晚期绘画史”写作计划:《隔江山色:元代绘画 1279-1368 》、《江岸送别:明代初期与中期绘画 1368-1580 》、《山外山:明代晚期绘画 1570-1644 》。另外两册分别是他1979年哈佛大学诺顿讲座、1991年哥伦比亚大学班普顿讲座的讲稿结集:《气势憾人:十七世纪中国绘画中的自然与风格》和《画家生涯:传统中国画家的生活与工作》(即出)。这是高居翰教授的著作首次以比较完整的面貌与大陆读者见面。
隔江山色
译者: 宋伟航
作者: [美] 高居翰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09-8
作者: [美] 高居翰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09-8
本书是作者关于中国晚期绘画史写作计划的第一种,探讨元代绘画。元代是蒙古人统治中国的时代,却也是中国文人画发展最具活力与原创性的时代。在蒙古人废科举制度的情形下,读书人面临着变节或失业的两难窘境,很多文人政途不通,转而以为人占卜、代书或绘画为业。本书即讲述了在这个异族统治、志不得伸的年代里,画家如何以绘画来表达自己的看法与心声的故事。
隔江山色:元代繪畫(1279-1368)Hills Beyond a River: Chinese Painting of the Yuan Dynasty,1279-1368
- 作者:高居翰
- 原文作者:James Cahill
- 譯者:夏春梅
- 出版社: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出版日期:1994年
元代是蒙古人統治中國的時代,卻也是中國文人畫發展最為輝煌燦爛的時代。本書討論中國畫家如何在這個苦悶而不得伸志的年代裡,轉而以繪畫表達自己對時代的看法及心聲。
除了時代與歷史背景的提示和討論,作者還具體地敘述了元代藝術家與畫壇所面對的諸多創作課題,並且針對近40位重要畫家進行生平介紹,舉出傳統畫史與畫論對他們個別的評價。不但如此,作者還以傳世具體的畫作為例,分析每位畫家的創作形式、內涵與意義。書末並附詳盡〈註釋〉、〈參考書目〉與〈索引〉。
在作者與本地學者的協助下,中文版不但將原書的「古籍引文」還原為中文,同時還修正了原書許多誤植之處,中文版的圖版採圖隨文走的設計,而且,品質也比英文版的精彩、考究得多。整體而言,中文版更為完整而易讀。
無論您是初學者或已經是專家學者,本書都是引導您進入專家之門的必備藝術書籍。
****
江岸送别
***
译者: 夏春梅
作者: 高居翰
出版社: 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09.8
作者: 高居翰
出版社: 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09.8
朱元璋推翻蒙元政权,建立明朝以后,却也带来了一段腥风血雨的统治,许多文人画家都落得了身首异处的凄惨下场,形成明初画坛的空白时期。本书探讨明代初期与中期的绘画发展,除了讨论明代画家如何赓续元代的绘画成就,寻求创新之外,也探讨了宫廷绘画与浙、吴(苏州)、南京等地方画派的表现及其发展。书中对于画家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其绘画风格的关系,也有极为精彩透辟的讨论。
江岸送別:明代初期與中期繪畫(1368-1580)Parting at the Shore: Chinese Painting of the Early and Middle Ming Dynasty, 1368-1580
- 作者:高居翰
- 原文作者:James Cahill
- 譯者:王靜霏,夏春梅,王嘉驥
- 出版社: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出版日期:1997年
本書探討中國明代初期與中期(1368-1580)繪畫。除討論明代繪畫風格中承續自元代及新創的部份之外,也探討了宮廷繪畫與浙、吳(蘇州)、南京等地方畫派的表現及其發展。此外,書中對畫家的社會、經濟地位與其繪畫風格的關係,也有極為精彩透闢的討論。
本書的撰寫模式與上述《隔江山色》一書相同。除了時代、歷史背景、藝術家與畫壇創作議題的探討之外,書中析論了近50位明代重要畫家的生平遭遇。不僅提供傳統畫史與畫論對他們個別的評價,並一一以傳世具體的畫作為例,解剖每位畫家的形式語言、內涵與意義。書末附詳盡〈註釋〉、〈參考書目〉與〈索引〉。
在作者與本地學者的協助下,中文版不但將原書的「古籍引文」還原為中文,並修正了原書許多誤植之處,中文版的圖版採圖隨文走的設計,品質也比英文版精彩、考究得多。整體而言,中文版更為完整而易讀。
無論您是初學者或已經是專家學者,本書都是引導您進入專家之門的必備藝術書籍。
***
陳洪綬『畫論』:「…..諸公,雖千門萬戶,千山萬水,都有韻致。……..老蓮願名流學古人,博覽……老蓮五十四歲矣,吾鄉並無一人,中興畫學,.拭目俟之!」
----轉引自高居翰『山外山』(The Distant Mountains)結尾處
山外山
译者: 王嘉骥
作者: 高居翰
出版社: 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09.8
作者: 高居翰
出版社: 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09.8
晚明经历了“天崩地解”的改朝换代巨变。由于朝廷体制的松动,文人思潮活泼、多元而富批判性。艺术家与政治的关系诡谲而复杂,各种景况造成了画坛空前的大震荡。在书中,读者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类型的画家及其令人震撼惊异的绘画图像,也可以了解到,中国绘画到了晚明时期,无论在形式的发展、内涵与意义的丰富性以及实践上,都已经发展到空前未有的复杂程度。
***
山外山:晚明繪畫(1570-1644)The Distant Mountains: Chinese Painting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1570-1644
- 作者:高居翰
- 原文作者:James Cahill
- 譯者:王嘉驥
- 出版社: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出版日期:1997年
本書簡介
本書探討中國明代晚期(1570-1644)繪畫的發展。晚明經歷了「天崩地解」的改朝換代巨變。一方面,由於朝廷政治體制的鬆動,文人的思潮活潑多元而富批判性。藝術家與政治的關係詭譎難測。另一方面,卻也因為改朝換代的緣故,文人士大夫紛紛面臨了是否要繼續服事滿清新政權的難題。有的人選擇「反清復明」,有的人被迫剃度出家或甚至自戕謝國,有的人則選擇繼續為滿清政權服務。這種景況造成了畫壇空前的大震盪。傳統畫史是如何評價各類的文人或貴族畫家呢?而時至今日,我們又應該如何評判或看待晚明畫壇的詭譎波瀾呢?高居翰教授是當今研究十七世紀中國繪畫的權威學者。在書中,他除了讓我們看到明末畫壇各種令人震撼驚異的山水圖像表現之外,同時,藉由他的生動描述,讀者也會了解到:中國藝術的創作到了晚明時期,無論在形式的發展上、在內涵與意義的豐富性上、以及在實踐上,都已經發展到了前所未有的複雜程度。
本書的撰寫模式與《隔江山色》、《江岸送別》均同,譯文也同樣通順流暢。書中一共探討了42位畫家的生平及171幅畫作。高居翰教授自己坦承,本書是他耗時最久的嘔心瀝血之作。讀者透過本書,可以深刻了解藝術家與政治權力之間的複雜網絡關係,進而明白藝術創作的本質並不完全是自由的。但也因為有著許許多多的外因與內因牽絆及影響,藝術家的創作才會對時代產生意義與衝擊。
無論您是入門者,或已經在藝術的領域裡學有專精,本書都是不可多得的經典著作。
專家推薦
~石守謙(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所長、中央研究院研究員)
高居翰基本上倚賴著兩個工具:一為其對繪畫風格的精闢形式分析,另一則為其以畫家之身分背景及生活方式為探討作品內涵之切入角色。前者來自於他在西方美術史方面的訓練,非一般中國傳統學人所熟習,後者則出於他長年以來對中國文化傳統的鑽研,以及一種具有審慎批判態度的理解。透過這兩個利器在畫家作品上的聯繫,他遂得以引導讀者進入時代的文化深處。
~方聞(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史教授、大都會博物館東方部主任、中央研究院院士)
高居翰此書(《氣勢撼人》)……,是目前為止有關十七世紀中國繪畫的論著中,最具震撼力的一本。
~古原宏伸(日本奈良大學美術史教授)
高博士的論著讀來皆十分有趣,無一例外。然其中的趣味性乃深蘊睿智,此為作者之學識、分析問題與解析圖像的卓越能力、以及豐富的閱畫經驗,綜合所得之產物。高博士所閱之畫,甚至包含了大量中國大陸收藏的作品;像他那樣見過那麼多作品的幾乎沒有第二人。其分析力之敏銳與深刻,常令我不由得為之驚嘆。
~何懷碩(國立藝術學院教授)
高居翰教授﹒﹒﹒最可欽佩的特色,一是畫史的變遷,能扣緊時代、社會、文化、思潮乃至文學的發展脈絡來論述,極富深度與廣度﹒﹒﹒另一個特色是對重要作家作品的介紹不是一般概念化的陳述,而是極細膩的鑑賞與分析,不但深入淺出,引人入勝,而且以這種實證的方法,非常雄辯地印證了他的史觀。至於時常以中西藝術史的軌跡來對比說明,對畫史、畫跡的資料巨細無遺的排比解析,充份顯示作者知識博洽,見解獨到,令人擊節。
~何傳馨(故宮博物院書畫處副研究員)
高居翰先生﹒﹒﹒一九六○年他出版第一本通論性著作《中國繪畫史》,此後勤於研究、講學,及籌辦專題展,發表許多深具啟發性的論著,成為在美國研究中國繪畫具有領導地位的學者。十八年前,高居翰寫成《隔江山色:元代繪畫》,是中國晚期繪畫系列著作五冊的第一本(陸續有《江岸送別:明代初期與中期繪畫》、《山外山:晚明繪畫》,及計畫中的清代與近代繪畫),學習中國畫史的學生,也終於有一本講究架構,嘗試把藝術品和藝術家聯繫起來的教科書。
~林柏亭(故宮書畫處處長)
高教授從西洋美術史研究之基礎,轉至中國繪畫史,其研究之方法,還有一些異於傳統觀點之論述,皆值得我們參考省思。
~蔣勳(東海大學美術史教授)
中國美術由於傳統太長,無論是資料掌握或觀念的自由度,都形成入門的障礙。高居翰的中國美術史,提供了一個新穎而不同的視野,對我們重新面對自己的傳統有耳目一新的啟發性。
***
气势撼人
译者: 李佩桦
作者: 高居翰
出版社: 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09.8
作者: 高居翰
出版社: 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09.8
十七世纪的中国,是一个面临改朝换代、人心惶惶的混乱时代,但在艺术史上,却是画家创作力最旺盛的时代。高居翰在书中提到:“即使在世界艺术史上,欧洲十九世纪以前的画坛,也都难与十七世纪的中国画坛媲美。”这是一部以最浅显的方式带领读者由小见大,进而透视中国绘画本质的大书。透过作者雄辩而生动的解析,以及丰富细腻的图版对比,读者可以毫无困难地进入中国十七世纪多位艺术大师──包括张宏、董其昌、吴彬、陈洪绶、弘仁、龚贤、王原祁、石涛──的心灵与创作世界,同时也可以一窥中国艺术里自然与风格的复杂辩证关系。
氣勢撼人:十七世紀中國繪畫中的自然與風格The Compelling Image: Nature and Styl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ese Painting
- 作者:高居翰
- 原文作者:James Cahill
- 譯者:王嘉驥
- 出版社: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出版日期:1994年
***
The Painter's Practice: How Artists Lived and Worked in Traditional China (Bampton Lectures in America)
- Hardcover: 187 pages
- Publish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March 1994)
In The Painter's Practice, James Cahill reveals the intricacies of the painter's life with respect to payment and patronage - an approach that is still largely absent from the study of East Asian art. Drawing upon such unofficial archival sources as diaries and letters, Cahill challenges the traditional image of the disinterested amateur scholar-artist, unconcerned with material rewards, that has been developed by China's literati, perpetuated in conventional biographies, and abetted by the artists themselves. His work fills in the hitherto unexplored social and economic contexts in which painters worked, revealing the details of how painters in China actually made their living from the sixteenth century onward. Considering the marketplace as well as the studio, Cahill reviews the practices and working conditions of artists outside the Imperial Court such as the employment of assistants and the use of sketchbooks and prints by earlier artists for sources of motifs. As loose, flamboyant brushwork came into vogue, Cahill argues, these highly imitable styles ironically facilitated the forger's task, flooding the market with copies, sometimes commissioned and signed by the artists themselves. In tracing the great shift from seeing the painting as a picture to a concentration on the painter's hand, Cahill challenges the archetype of the scholar-artist and provides an enlightened perspective that profoundly changes the way we interpret familiar paintings.
画家生涯
译者: 杨贤宗 马琳 邓伟权
作者: [美] 高居翰(James Cahill)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11-12-31
作者: [美] 高居翰(James Cahill)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11-12-31
本书为“高居翰作品系列”第五种,也是中译本的首次面世,主题讨论中国古代画家,尤其是元、明、清晚期画家的工作与生活。高居翰在这本书中,试图打破文人画家“寄情笔墨、自书胸臆、不食人间烟火”的神话,从实际的社会生活层面,考察了不同阶层画家的状态,他们如何将作品作为社交的礼物与应酬,如何通过卖画来养家糊口,如何苦于画债繁多而草草了事或雇佣助手,而对赞助人、收藏家和顾主来说,他们如何从画家手中取得作品,他们的希冀和要求对画家创作能起多少权重,他们如何判断获得是一张应酬之作还是一幅真正有艺术价值的作品……总之,在出自文人之手的主流撰述之外,高居翰通过搜集大量信笺、笔记、题跋等容易被忽视的材料,向读者展开了一幅自宋末以后,随着商业繁荣、社会中对绘画需求增加,画家们在不同层面谋生与创作的生动场景,使我们更充分地了解和考虑到一幅作品创作的原初情境,从而重新调整对艺术风格、品评标准的看法,读来令人读来耳目一新,是同类书市场中难得而重要的学术普及读物。
十七世紀的中國,是一個面臨改朝換代、人心惶惶的混亂時代,但在藝術史上,卻是畫家創作力最旺盛的時代。高居翰教授在書中提到:「即使在世界藝術史上,歐洲十九世紀以前的畫壇,也都難以與十七世紀的中國畫壇媲美。」
一九七八至七九年間,高居翰教授應哈佛大學極富盛名的諾頓(Charles Eliot Norton)講座之邀,以明清之際的藝術為題,發表研究心得。根據諾頓講座以往的經驗指出,凡是在該講座發表並集結成書的著作,最終都成為文壇及藝壇的經典。本書也不例外地已經進入經典之林,並獲得全美藝術學院聯會選為最佳藝術史著作。
透過作者雄辯而生動的解析,以及豐富細膩的圖片對比,讀者不但可以毫無困難地進入中國十七世紀多位藝術大師──包括張宏、董其昌、吳彬、陳洪綬、弘仁、龔賢、王原祁、石濤──的心靈與創作世界當中,同時,也可以清楚地看見中國藝術裡,自然與風格的複雜辯證關係。
詩之旅︰中國與日本的詩意繪畫
- 作者:(美)高居翰
- 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出版日期:2012年
序言
導論
第一章 南宋的杭州
徽宗皇家畫院
詩畫對幅
畫院以外的院體畫
沒有詩文的詩意畫
詩之旅
第二章 晚明的蘇州
明前期的詩意畫
題有詩句的立軸
張宏、李士達和盛茂燁
盛茂燁的詩意畫冊頁
明末清代其他詩意畫
第三章 江戶時期的日本
南畫在日本的興起
彭城百川
池大雅
與謝蕪村︰早年生涯
佐貫時期及其後階段的蕪村
贊助人、詩人圈及詩歌理論
蕪村與中國詩歌
蕪村與詩之旅︰晚年作品
注釋
參考書目
HC:這本書的可爭議處很多. 譬如說圖1.32的所謂"絲綸圖"(題目很怪 它有特定的意思)又是連夜紡織又是暮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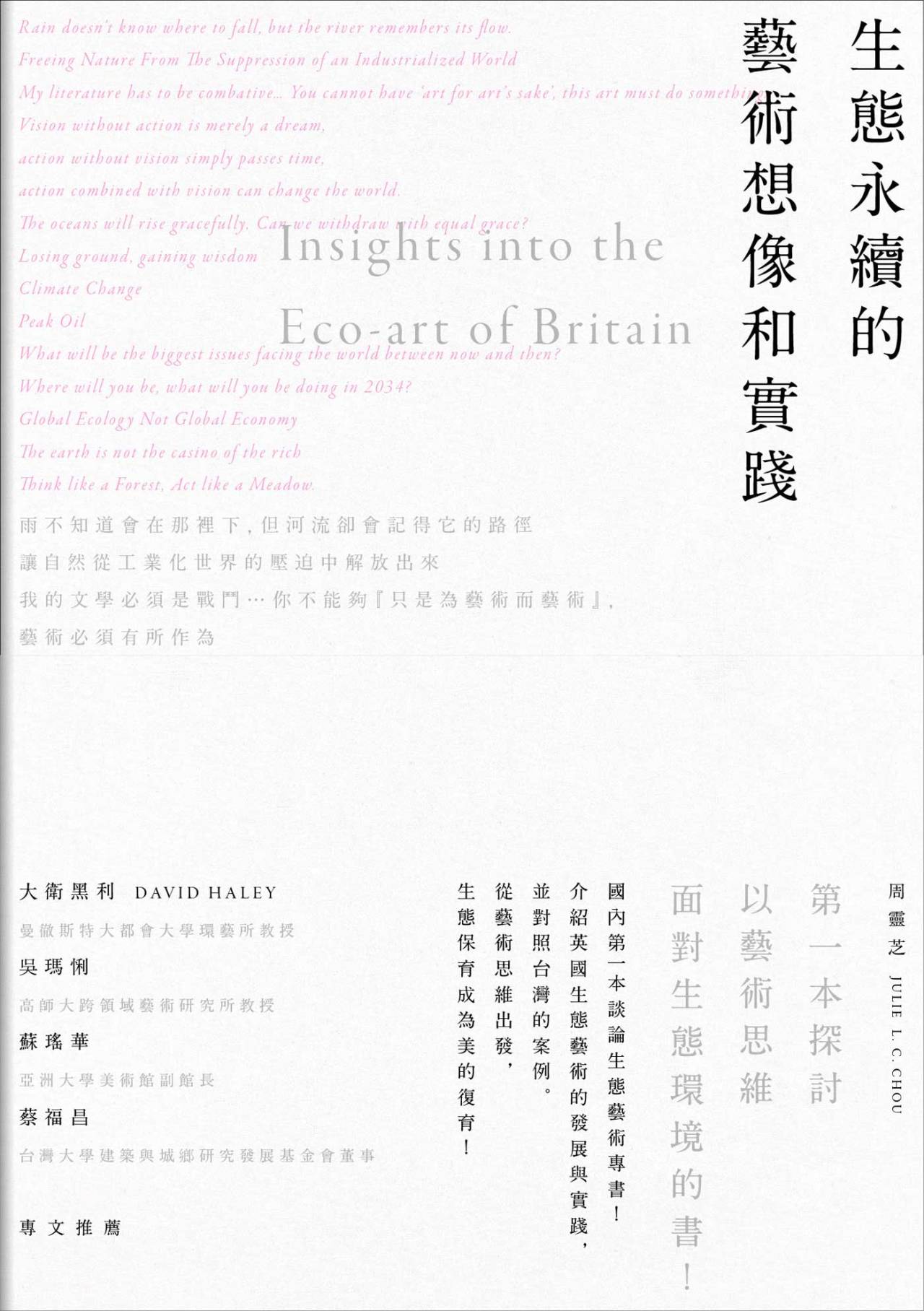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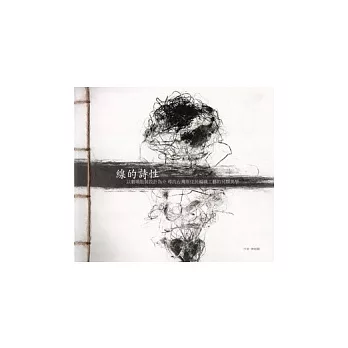





















 是他哀倦諷刺的眼睛)
是他哀倦諷刺的眼睛)
![[文學拍賣品]【當代文學低價拍】:李春生簽名本《李莎全集》上下兩冊全(稀見版本私藏95品台灣當代著名作家)](http://auctionimg2.kongfz.cc/20120716/1328727/1328727XiBma0_b.jpg)
![[文學拍賣品]【當代文學低價拍】:李春生簽名本《李莎全集》上下兩冊全(稀見版本私藏95品台灣當代著名作家)](http://auctionimg2.kongfz.cc/20120716/1328727/1328727pvDee0_b.jpg)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