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四大報2013.8.19/俄羅斯之聲VOR的日文報導
↧
Journals 1889-1949 (André Gide)《紀德日記卷選》/Henri Frédéric Amiel
一次覺醒: 這幾年有幾次動念翻譯:Journals 1889-1949 (André Gide): 詹宏志有一小本漢譯本(台北遠景) 也是有英文本的刪節. 前天拿到 李玉民《紀德文集‧日記卷》廣東:花城,2002,513頁 選集1888-1909,法國文學等注解不錯----今天比較英譯 發現英文本也刪掉許多
李是法國文學專家 (當然Gide很博學 李的英國文學的注解就很弱) 他說不定採全譯.....
我比較1904年末.(整年英文版5頁. 《紀德文集‧日記卷》在讀了尼采《通信集》讓他感覺平衡了許多 (李譯:恢復精神狀況)....之後李譯本省略5-6行--紀德記沿途所共讀的四本書---英文版都有注解...... 《紀德文集‧日記卷》還有一缺點是人名全用漢字.很不方便還原 譬如說1904年到到Sorrento拜訪神祕 (李:莫測高深)的Vollmoeller* (給Drouin的信中有詳述) (英頁76/《紀德文集‧日記卷》頁348)....
*Karl Gustav Vollmöller, usually written Vollmoeller (May 7, 1878 – October 18, 1948) was a German playwright and screenwriter.
He is most famous for two works, the screenplay for the celebrated 1930German film Der Blaue Engel (The Blue Angel), which made a star of Marlene Dietrich, and the elaborate religious spectacle-pantomime Das Mirakel (The Miracle), which he wrote in collaboration with Max Reinhardt, the famous director, and in which he cast his own wife Maria Carmi in the leading role. "The Miracle" retold an old legend about a nun in the Middle Ages who runs away from her convent with a knight, and subsequently has several mystical adventures, eventually leading to her being accused of witchcraft. During her absence, the statue of the Virgin Mary in the convent's chapel comes to life and takes the nun's place in the convent until her safe return. The play opened in Germany in 1911 and subsequently in London and on Broadway in 1924. Filmed twice as a silent movie, it was filmed once again in a much-altered version (with dialogue) in widescreen and Technicolor in 1959.
這是翻譯最好不要重譯 不要假內行的一例Journals 1889-1949 (André Gide)/Henri Frédéric Ami...
類似的說法 雪萊20歲的一首詩就說過--那年他到愛爾蘭 才知道貧民之慘狀比英倫的10倍差........
*****
昨天晚上睡前讀物是紀德1869-1951 的一輩子的日記 Journals 1889-1949
因為我買的廉價的企鵝版已經開始分解了
(1933年4月10日 頁559)
…We are entering a serious epoch.
有人預言紀德的日記就可以讓他不朽了
英文本略有刪節 不過 很不錯
詹宏志有一小本漢譯本(台北遠景) 也是有刪節.
李玉民《紀德文集‧日記卷》廣東:花城,2002,513頁 選集1888-1909,法國文學等注解不錯
GoogleBooks很保守 沒什麼意思 譬如說 有 ""在此書籍中有 5 頁符合 shakespeare"顯示3頁的小部份
隨便一字 lugubrious (p.240) 卻找不到
![封面 封面]()
***
紀德是讀 19 世紀的身後出版的日記大家Henri Frédéric Amiel 的作品而決定寫自己的日記
Henri Frédéric Amiel 的巨大日記
(該『日記』(「ひそかな日記」1839年-1881年、17,000頁)
尚無漢譯
除了梁宗岱先生翻譯過一篇約200字的散文詩
台大圖書館的日文翻譯
Henri Frédéric Amiel (28 September 1821 – 11 May 1881) was a Swiss philosopher, poet and critic.
Born in Geneva in 1821, he was descended from a Huguenot family driven to Switzerland by the revocation of the Edict of Nantes.[1]
After losing his parents at an early age, Amiel travelled widely, became intimate with the intellectual leaders of Europe, and made a special study of German philosophy in Berlin. In 1849 he was appointed professor of aesthetics at the academy of Geneva, and in 1854 became professor of moral philosophy. These appointments, conferred by the democratic party, deprived him of the support of the aristocratic party, which comprised nearly all the culture of the city.
This isolation inspired the one book by which Amiel is still known, the Journal Intime ("Private Journal"), which, published after his death, obtained a European reputation. It wa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Mary A. Ward at the instigation of Mark Pattison.
Although second-rate as regards productive power, Amiel's mind was of no inferior quality, and his Journal gained a sympathy that the author had failed to obtain in his life. In addition to the Journal, he produced several volumes of poetry and wrote studies on Erasmus, Madame de Stael and other writers. He died in Geneva.
2010
花城出版社的《纪德文集》分五卷,有《散文卷》、《传记卷》、《日记卷》、《游记卷》、《文论卷》。这五卷中,有五分之三的篇章是首次翻译介绍给我国读者的。这样,纪德的作品除晚年的日记、通信外,基本上全部呈现给了中国读者。
*遠景出版社**紀德日記1889-1914**紀德**民國70年
李是法國文學專家 (當然Gide很博學 李的英國文學的注解就很弱) 他說不定採全譯.....
我比較1904年末.(整年英文版5頁. 《紀德文集‧日記卷》在讀了尼采《通信集》讓他感覺平衡了許多 (李譯:恢復精神狀況)....之後李譯本省略5-6行--紀德記沿途所共讀的四本書---英文版都有注解...... 《紀德文集‧日記卷》還有一缺點是人名全用漢字.很不方便還原 譬如說1904年到到Sorrento拜訪神祕 (李:莫測高深)的Vollmoeller* (給Drouin的信中有詳述) (英頁76/《紀德文集‧日記卷》頁348)....
*Karl Gustav Vollmöller, usually written Vollmoeller (May 7, 1878 – October 18, 1948) was a German playwright and screenwriter.
He is most famous for two works, the screenplay for the celebrated 1930German film Der Blaue Engel (The Blue Angel), which made a star of Marlene Dietrich, and the elaborate religious spectacle-pantomime Das Mirakel (The Miracle), which he wrote in collaboration with Max Reinhardt, the famous director, and in which he cast his own wife Maria Carmi in the leading role. "The Miracle" retold an old legend about a nun in the Middle Ages who runs away from her convent with a knight, and subsequently has several mystical adventures, eventually leading to her being accused of witchcraft. During her absence, the statue of the Virgin Mary in the convent's chapel comes to life and takes the nun's place in the convent until her safe return. The play opened in Germany in 1911 and subsequently in London and on Broadway in 1924. Filmed twice as a silent movie, it was filmed once again in a much-altered version (with dialogue) in widescreen and Technicolor in 1959.
Vollmöller, Karl, 1878-1948¶
- Turandot, Princess of China
A Chinoiserie in Three Acts (English) (as Author)
這是翻譯最好不要重譯 不要假內行的一例Journals 1889-1949 (André Gide)/Henri Frédéric Ami...
1909.7.4(40歲) .......不存在籠統的智慧,人只有做這事,做那事的聰明,聰明只應當表現在所做的事情上
類似的說法 雪萊20歲的一首詩就說過--那年他到愛爾蘭 才知道貧民之慘狀比英倫的10倍差........
*****
昨天晚上睡前讀物是紀德1869-1951 的一輩子的日記 Journals 1889-1949
因為我買的廉價的企鵝版已經開始分解了
(1933年4月10日 頁559)
…We are entering a serious epoch.
他引蒙田的話:「人變老還可接受的,如果我們只向改善邁步:
它卻像醉漢跌破跌撞撞,東倒西歪,昏迷,不測。」 《惡之華‧仇敵》末段
痛苦啊!「時間」蠶食生命,
它咬住我們的心,像刀般利,
這「仇敵」吸我們的血而肥壯!
有人預言紀德的日記就可以讓他不朽了
英文本略有刪節 不過 很不錯
詹宏志有一小本漢譯本(台北遠景) 也是有刪節.
李玉民《紀德文集‧日記卷》廣東:花城,2002,513頁 選集1888-1909,法國文學等注解不錯
GoogleBooks很保守 沒什麼意思 譬如說 有 ""在此書籍中有 5 頁符合 shakespeare"顯示3頁的小部份
隨便一字 lugubrious (p.240) 卻找不到
Journals 1889-1949
| 書名 | Journals 1889-1949 Penguin modern classics第 2685 卷 |
| 作者 | André Gide |
| 編者 | Justin O'Brien |
| 譯者 | Justin O'Brien |
| 出版者 | Penguin, 1967 |
| 來源: | 威斯康辛大學曼迪遜分校 |
| 已數位化 | 2010年2月16日 |
| 頁數 | 797 頁 |
***
紀德是讀 19 世紀的身後出版的日記大家Henri Frédéric Amiel 的作品而決定寫自己的日記
Henri Frédéric Amiel 的巨大日記
(該『日記』(「ひそかな日記」1839年-1881年、17,000頁)
尚無漢譯
除了梁宗岱先生翻譯過一篇約200字的散文詩
台大圖書館的日文翻譯
1 勾選  |
|
勾選  |
|
Henri Frédéric Amiel (28 September 1821 – 11 May 1881) was a Swiss philosopher, poet and critic.
Born in Geneva in 1821, he was descended from a Huguenot family driven to Switzerland by the revocation of the Edict of Nantes.[1]
After losing his parents at an early age, Amiel travelled widely, became intimate with the intellectual leaders of Europe, and made a special study of German philosophy in Berlin. In 1849 he was appointed professor of aesthetics at the academy of Geneva, and in 1854 became professor of moral philosophy. These appointments, conferred by the democratic party, deprived him of the support of the aristocratic party, which comprised nearly all the culture of the city.
This isolation inspired the one book by which Amiel is still known, the Journal Intime ("Private Journal"), which, published after his death, obtained a European reputation. It wa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Mary A. Ward at the instigation of Mark Pattison.
Although second-rate as regards productive power, Amiel's mind was of no inferior quality, and his Journal gained a sympathy that the author had failed to obtain in his life. In addition to the Journal, he produced several volumes of poetry and wrote studies on Erasmus, Madame de Stael and other writers. He died in Geneva.
2010
安德烈·紀德《日記 1942-1949年》花城出版社的《纪德文集》
花城出版社的《纪德文集》分五卷,有《散文卷》、《传记卷》、《日记卷》、《游记卷》、《文论卷》。这五卷中,有五分之三的篇章是首次翻译介绍给我国读者的。这样,纪德的作品除晚年的日记、通信外,基本上全部呈现给了中国读者。
安 德烈·保尔·吉约姆·纪德(1867-1951),是法国二十世纪最活跃、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花城出版社《纪德文集》的编者和译者(散文卷、日记卷), 首都师大的李玉民教授向记者介绍,纪德是个少有的最不容易捉摸的作家,他的一生和他的作品所构成的世界,就是一座现代迷宫。变化和否定,贯穿纪德的一生和 他的全部作品。纪德是在人生探索、文学创新两方面都给后人留下最多启示的作家。
李教授说,每次重读纪德的作品都有新发现,他的作品是让人思考、让人参与的作品。
北 京大学罗芃教授认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纪德被看作文学的“颠覆者”,更糟糕的是他还背上了道德“颠覆者”的恶名。这种双重“颠覆者”的身份一度曾使纪 德很有点“声名狼藉”。有人嘲笑他的作品形式不伦不类,有人声色俱厉地谴责他伤风败俗,当然也有人双管齐下,从两个方面作了否定和抨击。如今,纪德伟大作 家的地位已经毋庸置疑,历史已经下了结论,但是对他在小说革命方面所做的试验性探索究竟应该如何评价,仍旧是可以讨论的问题,而他对传统思想道德的叛逆和 颠覆,情况更为复杂,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纪德文集》的出版,为我国读者和外国文学研究者在这方面的工作创造了条件。
安德烈·紀德年表-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出版《與保羅·克洛岱爾通信集》。 1950年12月13日,劇本《梵蒂岡的地窖》在法蘭西喜劇院首演。出版《日記 1942-1949年》。 1951年2月19日,安德烈·紀德因肺炎在巴黎病逝 ...*遠景出版社**紀德日記1889-1914**紀德**民國70年
↧
↧
Baudelaire: Selected Poems/ 波特萊爾的《惡之華》/巴黎男女
過去一周每天一二首英譯 此書用字的確有些特色
But as for me, my limbs are rent
Because I clasped the clouds as mine.
---The Laments of an Icarus.
1889.3.11 Journals by Gide 引用過. 通行版{惡之華}待查
Online texts
- Charles Baudelaire—Largest site dedicated to Baudelaire's poems and prose, containing Fleurs du mal, Petit poemes et prose, Fanfarlo and more in French.
- Works by or about Charles Baudelaire at the Internet Archive (scanned original editions, color illustrated)
- Works by Charles Baudelaire at Project Gutenberg(French) and (English)
- La Nouvelle Décadence—Extensive online library of Baudelaire translations and biographies
- Poems by Charles Baudelaire—Selected works at Poetry Archive
- Baudelaire's poems at Poems Found in Translation
- Baudelaire - Eighteen Poems
- "baudelaire in english", Onedit.net—Sean Bonney's experimental translations of Baudelaire (humor)
- (French)Baudelaire, Les Fleurs du Mal and Petits Poèmes en Prose (Le Spleen de Paris), at athena.unige.ch
Single works
- FleursDuMal.org—Definitive online presentation of Fleurs du mal, featuring the original French alongside multiple English translations
- An illustrated version (8 Mb) of Les Fleurs du Mal, 1861 edition (Charles Baudelaire / une édition illustrée par inkwatercolor.com)
- "The Rebel"—poem by Baudelaire
- Les Foules (The Crowds)—English translation
2013.4.4 辜振豐老師送一本簽名的 "全新中譯本"《惡之華》(台北:花神文坊 2013)
漢清兄惠存:
悅讀法蘭西詩歌
我問些字體插圖等. 他希望我寫書評... (我說我不懂法文所以只能用英文和其他中文本"攻錯之: Baudelaire: Selected Poems 波特萊爾的《惡之華》/巴黎男女)
去年或全年我說這本名著的漢譯可能近10本以上. 何苦再多一本"非學術"之作?
不過 辜振豐老師的意志力強 他已展開波特萊爾的第2本之翻譯中. 而且他的作品都是"全方位設計" 很令人佩服 並要祝賀/祝服他成功!
*****
Baudelaire: Selected Poems (法英對照)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Joanna Richarson, Penguine, 1975/'77/'78
依1868《惡之華》版本及隨後在比利時出的禁詩序而編
惡之華
Les Fleurs du mal
《惡之華》(法語:Les Fleurs du mal)
Fro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這版本顯然一直在改進. 本文是2011年版. 只有"一首" 的翻譯比較中列出2種英文和三種中文.
For other uses, see Les Fleurs du mal (disambiguation).
Les Fleurs du mal (often translated The Flowers of Evil) is a volume of French poetry by Charles Baudelaire. First published in 1857 (see 1857 in poetry), it was important in the symbolist and modernist movements.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ese poems deals with themes relating to decadence and eroticism.[edit]Overview
The initial publication of the book was arranged in six thematically segregated sections:- Spleen et Idéal (Spleen and Ideal)
- Tableaux parisiens (Parisian Scenes)
- Le Vin (Wine)
- Fleurs du mal (Flowers of Evil)
- Révolte (Revolt)
- La Mort (Death)
Si le viol, le poison, le poignard, l'incendie,
N'ont pas encore brodé de leurs plaisants dessins
Le canevas banal de nos piteux destins,
C'est que notre âme, hélas! n'est pas assez hardie.
- If rape and poison, dagger and burning,
- Have still not embroidered their pleasant designs
- On the banal canvas of our pitiable destinies,
- It's because our souls, alas, are not bold enough!
In the poem "Au lecteur" ("To the Reader") that prefaces Les Fleurs du mal, Baudelaire accuses his readers of hypocrisy and of being as guilty of sins and lies as the poet: - ...If rape or arson, poison or the knife
- Has wove no pleasing patterns in the stuff
- Of this drab canvas we accept as life—
- It is because we are not bold enough!
- (Roy Campbell's translation)
C'est l'Ennui! —l'œil chargé d'un pleur involontaire,
Il rêve d'échafauds en fumant son houka.
Tu le connais, lecteur, ce monstre délicat,
—Hypocrite lecteur,—mon semblable,—mon frère!
- It's Ennui! — his eye brimming with spontaneous tear
- He dreams of the gallows in the haze of his hookah.
- You know him, reader, this delicate monster,
- Hypocritical reader, my likeness, my brother!
[edit]Literary significance and criticism
The author and the publisher were prosecuted under the regime of the Second Empire as an outrage aux bonnes mœurs (trans. "an insult to public decency"). As a consequence of this prosecution, Baudelaire was fined 300 francs. Six poems from the work were suppressed and the ban on their publication was not lifted in France until 1949. These poems were "Lesbos", "Femmes damnés (À la pâle clarté)" (or "Women Doomed (In the pale glimmer...)"), "Le Léthé" (or "Lethe"), "À celle qui est trop gaie" (or "To Her Who Is Too Gay"), "Les Bijoux" (or "The Jewels"), and " Les "Métamorphoses du Vampire" (or "The Vampire's Metamorphoses"). These were later published in Brussels in a small volume entitled Les Épaves (Jetsam).On the other hand, upon reading "The Swan" or "Le Cygne" from Les Fleurs du mal, Victor Hugo announced that Baudelaire had created "un nouveau frisson" (a new shudder, a new thrill) in literature.
In the wake of the prosecution a second edition was issued in 1861 which added 32 new poems, removed the six suppressed poems and added a new section entitled Tableaux Parisiens.
A posthumous third edition with a preface by Théophile Gautier and including 14 previously unpublished poems was issued in 1868.
[edit]Cultural references
- Dead Can Dance's second album, 1985's Spleen and Ideal, was named after the first passage in the poem.
- Folk band Spires that in the Sunset Rise take their name from a line in "The Voyage"[1]
- The show How I Met Your Mother briefly references this book when Ted finds his college girlfriend Karen in his bed with another man.
- In the volume of poetry The Pill vs. The Springhill Mine DisasterRichard Brautigan employs Baudelaire as a character in a series of poems.
[edit]See also
[edit]External links
 | Wikisource has original text related to this article: |
- Charles Baudelair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 s:fr:Les Fleurs du mal: complete work on French Wikisource
- Les Fleurs du mal: full online downloadable text
- Les Fleurs du mal (in French) at Project Gutenberg
- Fleursdumal.org, a collection of the various French editions and accompanying translations in English.
- An illustrated version (8 Mb) of Les Fleurs du Mal, 1.861 edition (Charles Baudelaire / une édition illustrée par http://www.inkwatercolor.com)
- ^ See Travelling Bell
惡 之花-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惡之華》(法語:Les Fleurs du mal),又譯《惡 之花》,是法國詩人夏爾·波德萊爾於1857年發表的詩集作品,內容以頹廢與性為材,並對象徵主義與現代主義文學發展有著 ...
zh.wikipedia.org/zh-tw/恶之花 - 頁 庫存檔博客來書籍館;惡之花
果然,《惡之花》遭到了「普遍的猛烈抨 擊,引起了人們的好奇。「好奇」,正是作者的追求;「抨擊」,也不能使他退縮;然而,跟在「抨擊」之後的卻是法律的追究,這是他 ...
作者 :杜國清
出版時間 : 2011年12月
出版單位 :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裝訂 : 精裝
| 波特萊爾的《惡之華》杜國清譯 神魔的眼神﹕談波特萊爾與《惡之華》 謝謝 妙 幾年前2008/2月阿擘請我和杜教授吃過晚餐 台大出版中心的訂價策略很奇怪 這本名著的最新修正本才350元 參考英日和中國的翻譯 2008年時杜國清先生對純文學出版社的《惡之華》的稿酬等, |
現在有難得的機會補強並修正它,無寧是譯者和讀者之福氣。
詩人老了......《諾貝爾文學獎全集50:米沃什》杜國清譯
1982(尚未翻閱)
***
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 頁88。無”因讓那‧杜瓦爾而作”字樣。***
昨晚讀《哥德談話錄》智慧老人哥德向年輕的艾克曼說
要珍惜每一刻每一分鐘 它們都是永恆的代表
上周”送陳忠信夫婦”之詩的更新 或可溫故知新
(又為陳巨擘昔日的晚餐而作)
*****
波特萊爾(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惡之華‧貓》杜國清譯。台北:
34 貓
來,美麗的貓,來到我愛的心上,
把你腳上銳利的爪隱藏,
讓我沉浸在你美麗的眼眸中
映出金屬與瑪瑙的亮光。
當我的手指,從容不迫地愛撫,
你的頭和那彈性的背脊,
當我的手陶然感到興奮的滿足,
一觸及你帶電的嬌軀,
我就幻見我的女人,她的眼神,
和你一樣,可愛的動物,
深邃冷轍,有如鏢槍尖銳刺人;
從她的腳尖到她的頭部,
一種微妙的氣色,危險的暗香,
在她褐色身旁漂浮蕩漾。
*****另一中國某書中的翻譯(這是上周從一本法國文人憶波特
萊爾的新書中抄下的。現在暫時找不到它。)《貓‧因讓那‧杜瓦爾而作》波特萊爾
|
日本小說家芥川龍之介曾為之傾倒自嘆:「
人生不如波特萊爾的一行詩」。
法國大文豪雨果給波特萊爾的《惡之花》的贊語:「
你向藝術的天空,擲去了一道攝人的光芒,創造了新的顫慄。」
這本新版《惡之華》,名符其實是波特萊爾一生詩作的全譯本,
包括第二版原著、《漂流詩篇》、六首禁詩、
這個新版,除了波特萊爾一生詩創作的全譯之外,
附錄有譯者的四篇文章﹕「波特萊爾與《惡之華》」簡介、「
杜教授以對波特萊爾與《惡之華》的了解,談論詩人心中的「惡」
與「花」,以及他一生追尋的「詩」與「美」的特質,
你的倦怠 來自愛與美的追尋
你愛的美 那明媚的眼眸
神魔合一 同時具有
致命的魅力與無限暴虐
使你在狂喜的瞬間 欲求毀滅
你愛的美 不管來自天上或地獄
不論來自上帝或惡魔
純粹的愛 無畏 無悔
只要能使你 一時迷醉
脫離 這個醜惡的世界
《惡之華》是詩人的精神在善惡衝突中迸出的火花,
也是受苦的靈魂綻放出的病弱花朵,散發著不吉的冷香,
| |||
現任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東亞語言文化研究系、
【譯者序】波特萊爾與《惡之華》/ 杜國清
致波特萊爾 / 杜國清
作者獻詞
致讀者 Au Lecteur/波特萊爾
惡之華Les Fleurs du Mal
憂鬱與理想 SPLEEN ET IDeAL1祝禱 Benediction
2信天翁 L’ Albatros
3高翔 Elevation
4萬物照應 Correspondances
5〈我喜愛對那些裸體時代……〉Jaime le souvenir de ces epopues nues
6燈塔 Les Phares
7生病的繆斯 La Muse Malade
8賣身的繆斯 La Muse Venale
9惡僧 Le Mauvais Moine
10仇敵 L’Ennemi
11倒運 Le Guignon
12前生 La Vie Anterieure
13踏上旅途的波希米人 Bohemiens en Voyage
14人與海 L’Homme et la Mer
15地獄的唐璜 Don Juan aux Enfers
16傲慢的懲罰 Chatiment de l’Orgueil
17美 La Beaute
18理想 L’Ideal
19女巨人 La Geante
20假面 Le Masque
21美的讚歌 Hymne a la Beaute
22異國的芳香 Parfum Exotique
23髮 La Chevelure
24〈我愛慕你……〉 Je t’adore a l’cgal de la voute nocturne
25〈你想將整個宇宙……〉Tu mettrais l’univers entier dans ta ruelle
26然而還不滿足 Sed non Satiata
27〈穿著波狀的……〉Avec ses veements ondoyants et nacres
28舞動的蛇 Le Serpent qui Danse
29腐屍 Une Charogne
30來自深淵的叫喊 De Profundis Clamavi
31吸血鬼 Le Vampire
32〈一夜我睡在……〉Une nuit que j’etais pres d’une affreuse Juive
33死後的悔恨 Remords Posthume
34貓 Le Chat
35決鬥 Duellum
36陽臺 Le Balcon
37著魔的男人 Le Possede
38幽靈 Un Fantome
Ⅰ黑闇 Les Tenebres
Ⅱ薰香 Le Parfum
Ⅲ畫框 Le Cadre
Ⅳ肖像 Le Portrait
39〈給你這些詩……〉Je te donne ces vers afin que si mon nom
40永遠一樣 Semper Eadem
41她的一切 Tout Entiere
42〈今晚你說什麼……〉Que diras-tu ce soir, pauvre ame solitaire
43活火炬 Le Flambeau Vivant
44恩賜 Reversibilite
45告白 Confession
46心靈的黎明 L’Aube Spirituelle
47黃昏的諧調 Harmonie du Soir
48香水瓶 Le Flacon
49毒 Le Poison
50陰空 Ciel Brouille
51貓 Le Chat
52優美的船 Le Beau Navire
53旅邀L’Invitation au Voyage
54不能挽救者L’Irreparable
55交談 Causerie
56秋之歌 Chant d’Automne
57給一位聖母 A une Madone
58午後之歌 Chanson d’Apres-Midi
59西西娜 Sisina
60給我佛蘭琪絲嘉的讚歌 Franciscae me Laudes
61給生長在殖民地的一位夫人 A une Dame Creole
62憂愁與流浪Moesta et Errabunda
63幽靈 Le Revenant
64秋的小曲 Sonnet d’Automne
65月的悲哀 Tristesses de la Lune
66貓 Les Chats
67貓頭鷹 Les Hiboux
68煙斗 La Pipe
69音樂 La Musique
70墓 Sepulture
71一幅幻想的版畫 Une Gravure Fantastique
72快活的死者 Le Mort Joyeux
73憎恨的無底桶 Le Tonneau de la Haine
74破鐘 La Cloche Felee
75憂鬱 Spleen
76憂鬱 Spleen
77憂鬱 Spleen
78憂鬱 Spleen
79著魔 Obsession
80虛無的滋味 Le Gout du Neant
81苦惱的鍊金術 Alchimie de la Douleur
82恐怖的感應 Horreur Sympathique
83自我懲罰者 L’Heautontimoroumenos
84無可贖救者 L’Irremediable
85時鐘 L’Horloge
巴黎寫景 TABLEAUX PARISIENS86風景 Paysage
87太陽 Le Soleil
88給一個紅髮的乞丐女郎 A une Mendiante Rousse
89天鵝 Le Cygne
90 七個老頭兒 Les Sept Vieillards
91小老太婆 Les Petites Vieilles這兩首是獻給雨果的雨果回信說令人......
92盲人 Les Aveugles
93給路上錯過的一個女人 A une Passante
94骸耕圖 Le Squelette Laboureur
95夕暮 Le Crepuscule du Soir
96賭博 Le Jeu
97死的舞蹈 Danse Macabre
98虛假的戀 L’Amour du Mensonge
99〈我仍忘不了……〉Je n’ai pas oublie, voisine de la ville
100〈你曾嫉妒的……〉La servante au grand coeur dont vous etiez jalouse
101霧和雨 Brumes et Pluies
102巴黎之夢 Reve Parisien
103黎明 Le Crepuscule du Matin
酒 LE VIN104酒魂L’Ame du Vin
105拾荒者的酒 Le Vin des Chiffonniers
106殺人犯的酒 Le Vin de l’Assassin
107孤獨者的酒 Le Vin du Solitaire
108熱戀者的酒 Le Vin des Amants
惡之華 FLEURS DU MAL109毀滅 La Destruction
110一個受難的女人 Une Martyre
111 該入地獄的女人 Femmes Damnees
112一對好姊妹 Les Deux BonnesSoeurs
113血泉 La Fontaine de Sang
114寓意 Allegorie
115貝雅翠斯 La Beatrice
116西堤爾之旅 Un Voyage a Cythere
117愛神與腦殼 L’Amour et le Crane
叛逆 ReVOLTE118聖.彼得的否認 Le Reniement de Saint Pierre
119亞伯與該隱Abel et Cain
120 向惡魔的連禱 Les Litanies de Satan
死 LA MORT121熱戀者之死 La Mort des Amants
122窮人之死 La Mort des Pauvres
123藝術家之死 La Mort des Artistes
124一日之終 La Fin de la Journee
125好奇者的夢 Le Reve d’ un Curieux
126 旅航 Le Voyage
漂流詩篇(LES ePAVES)(1866)1浪漫派的落日 Le Coucher du Soleil Romantique
《惡之華》被禁詩篇 PIeCES CONDAMNeES
2麗斯波斯島 Lesbos
3墮入地獄的女人 (黛菲尼與伊波麗特) Femmes Damnees
Delphine et Hipolyte
4忘川Le Lethe
5給一位太快活的女人 A Celle Qui Est Trop Gaie
6首飾 Les Bijoux
7吸血鬼的化身Les Metamorphoses du Vampire
豔歌 (GALANTERIES)8 噴泉 Le Jet D’eau
9 貝爾特的眼睛 Les Yeux de Berthe
10 讚歌 Hymne
11容貌的期許 Les Promesses d’un Visage
12怪物(別題「恐怖趣味的林澤仙女的讚辭」) Le Monstre
Ou Le Paranymphe d’une Nymphe Macabre
13 給我佛蘭琪絲嘉的讚歌 Franciscae me Laudes
題詠 (ePIGRAPHES)14奧諾雷.杜米埃肖像題詩 Vers Pour Le Portrait de M. HonoreDaumier
15瓦倫西的羅拉 Lola De Valence
16題「牢中的塔索」(德拉珂羅瓦所畫) Sur <> d’Eugene Delacroix
雜篇(PIeCES DIVERSES)17聲音 La Voix
18意想不到者L’Imprevu
19贖金La Rancon
20給一位馬拉巴姑娘A Une Malabaraise
戲作 (BOUFFONNERIES)21 阿米娜.波雪蒂初上舞台(於布魯塞爾莫奈劇院)
Sur Les Debuts d’Amina Boschetti
22 致歐金.福洛曼丹氏(關於某個令人討厭者自稱是他的朋友)
A M. Eugene Fromentin / A Propos d’un Importun / Qui Se Disait Son Ami
23戲謔的小酒店(從布魯塞爾到約庫耳途中所見)
Un Cabaret Folatre / Sur La Route de Bruxelles a Uccle
《惡之華》第三版增訂稿(1866-1868) PIeCES AJOUTeES1一本禁書的題詞 epigraphe Pour un Livre condamne
2致邦維爾(一八四二年作) A Theodore de Banville—1842—
3和平的菸斗(仿朗費羅) Le Calumet de Paix
Imite de Longfellow
4異教徒的祈禱La Priere d’un Paien
5蓋子 Le Couvercle
6午夜的反省 L’Examen de Minuit
7悲情的戀歌 Madrigal Triste
8警告者 L’Avertisseur
9叛逆者 Le Rebelle
10離此遙遠Bien Loin d’Ici
11深淵 Le Gouffre
12伊卡洛斯的悲嘆 Les Plaintes d’un Icare
13靜思 Recueillement
14被冒犯的月亮La Lune Offensee
波特萊爾年譜
萬物照應.東西交輝 / 杜國清
波特萊爾與我/ 杜國清
《惡之華》初版譯者後記 (1977)
《惡之華》新版譯者後記(2011)
致波特萊爾 / 杜國清
作者獻詞
致讀者 Au Lecteur/波特萊爾
惡之華Les Fleurs du Mal
憂鬱與理想 SPLEEN ET IDeAL1祝禱 Benediction
2信天翁 L’ Albatros
3高翔 Elevation
4萬物照應 Correspondances
5〈我喜愛對那些裸體時代……〉Jaime le souvenir de ces epopues nues
6燈塔 Les Phares
7生病的繆斯 La Muse Malade
8賣身的繆斯 La Muse Venale
9惡僧 Le Mauvais Moine
10仇敵 L’Ennemi
11倒運 Le Guignon
12前生 La Vie Anterieure
13踏上旅途的波希米人 Bohemiens en Voyage
14人與海 L’Homme et la Mer
15地獄的唐璜 Don Juan aux Enfers
16傲慢的懲罰 Chatiment de l’Orgueil
17美 La Beaute
18理想 L’Ideal
19女巨人 La Geante
20假面 Le Masque
21美的讚歌 Hymne a la Beaute
22異國的芳香 Parfum Exotique
23髮 La Chevelure
24〈我愛慕你……〉 Je t’adore a l’cgal de la voute nocturne
25〈你想將整個宇宙……〉Tu mettrais l’univers entier dans ta ruelle
26然而還不滿足 Sed non Satiata
27〈穿著波狀的……〉Avec ses veements ondoyants et nacres
28舞動的蛇 Le Serpent qui Danse
29腐屍 Une Charogne
30來自深淵的叫喊 De Profundis Clamavi
31吸血鬼 Le Vampire
32〈一夜我睡在……〉Une nuit que j’etais pres d’une affreuse Juive
33死後的悔恨 Remords Posthume
34貓 Le Chat
35決鬥 Duellum
36陽臺 Le Balcon
37著魔的男人 Le Possede
38幽靈 Un Fantome
Ⅰ黑闇 Les Tenebres
Ⅱ薰香 Le Parfum
Ⅲ畫框 Le Cadre
Ⅳ肖像 Le Portrait
39〈給你這些詩……〉Je te donne ces vers afin que si mon nom
40永遠一樣 Semper Eadem
41她的一切 Tout Entiere
42〈今晚你說什麼……〉Que diras-tu ce soir, pauvre ame solitaire
43活火炬 Le Flambeau Vivant
44恩賜 Reversibilite
45告白 Confession
46心靈的黎明 L’Aube Spirituelle
47黃昏的諧調 Harmonie du Soir
48香水瓶 Le Flacon
49毒 Le Poison
50陰空 Ciel Brouille
51貓 Le Chat
52優美的船 Le Beau Navire
53旅邀L’Invitation au Voyage
54不能挽救者L’Irreparable
55交談 Causerie
56秋之歌 Chant d’Automne
57給一位聖母 A une Madone
58午後之歌 Chanson d’Apres-Midi
59西西娜 Sisina
60給我佛蘭琪絲嘉的讚歌 Franciscae me Laudes
61給生長在殖民地的一位夫人 A une Dame Creole
62憂愁與流浪Moesta et Errabunda
63幽靈 Le Revenant
64秋的小曲 Sonnet d’Automne
65月的悲哀 Tristesses de la Lune
66貓 Les Chats
67貓頭鷹 Les Hiboux
68煙斗 La Pipe
69音樂 La Musique
70墓 Sepulture
71一幅幻想的版畫 Une Gravure Fantastique
72快活的死者 Le Mort Joyeux
73憎恨的無底桶 Le Tonneau de la Haine
74破鐘 La Cloche Felee
75憂鬱 Spleen
76憂鬱 Spleen
77憂鬱 Spleen
78憂鬱 Spleen
79著魔 Obsession
80虛無的滋味 Le Gout du Neant
81苦惱的鍊金術 Alchimie de la Douleur
82恐怖的感應 Horreur Sympathique
83自我懲罰者 L’Heautontimoroumenos
84無可贖救者 L’Irremediable
85時鐘 L’Horloge
巴黎寫景 TABLEAUX PARISIENS86風景 Paysage
87太陽 Le Soleil
88給一個紅髮的乞丐女郎 A une Mendiante Rousse
89天鵝 Le Cygne
90 七個老頭兒 Les Sept Vieillards
91小老太婆 Les Petites Vieilles這兩首是獻給雨果的雨果回信說令人......
92盲人 Les Aveugles
93給路上錯過的一個女人 A une Passante
94骸耕圖 Le Squelette Laboureur
95夕暮 Le Crepuscule du Soir
96賭博 Le Jeu
97死的舞蹈 Danse Macabre
98虛假的戀 L’Amour du Mensonge
99〈我仍忘不了……〉Je n’ai pas oublie, voisine de la ville
100〈你曾嫉妒的……〉La servante au grand coeur dont vous etiez jalouse
101霧和雨 Brumes et Pluies
102巴黎之夢 Reve Parisien
103黎明 Le Crepuscule du Matin
酒 LE VIN104酒魂L’Ame du Vin
105拾荒者的酒 Le Vin des Chiffonniers
106殺人犯的酒 Le Vin de l’Assassin
107孤獨者的酒 Le Vin du Solitaire
108熱戀者的酒 Le Vin des Amants
惡之華 FLEURS DU MAL109毀滅 La Destruction
110一個受難的女人 Une Martyre
111 該入地獄的女人 Femmes Damnees
112一對好姊妹 Les Deux BonnesSoeurs
113血泉 La Fontaine de Sang
114寓意 Allegorie
115貝雅翠斯 La Beatrice
116西堤爾之旅 Un Voyage a Cythere
117愛神與腦殼 L’Amour et le Crane
叛逆 ReVOLTE118聖.彼得的否認 Le Reniement de Saint Pierre
119亞伯與該隱Abel et Cain
120 向惡魔的連禱 Les Litanies de Satan
死 LA MORT121熱戀者之死 La Mort des Amants
122窮人之死 La Mort des Pauvres
123藝術家之死 La Mort des Artistes
124一日之終 La Fin de la Journee
125好奇者的夢 Le Reve d’ un Curieux
126 旅航 Le Voyage
漂流詩篇(LES ePAVES)(1866)1浪漫派的落日 Le Coucher du Soleil Romantique
《惡之華》被禁詩篇 PIeCES CONDAMNeES
2麗斯波斯島 Lesbos
3墮入地獄的女人 (黛菲尼與伊波麗特) Femmes Damnees
Delphine et Hipolyte
4忘川Le Lethe
5給一位太快活的女人 A Celle Qui Est Trop Gaie
6首飾 Les Bijoux
7吸血鬼的化身Les Metamorphoses du Vampire
豔歌 (GALANTERIES)8 噴泉 Le Jet D’eau
9 貝爾特的眼睛 Les Yeux de Berthe
10 讚歌 Hymne
11容貌的期許 Les Promesses d’un Visage
12怪物(別題「恐怖趣味的林澤仙女的讚辭」) Le Monstre
Ou Le Paranymphe d’une Nymphe Macabre
13 給我佛蘭琪絲嘉的讚歌 Franciscae me Laudes
題詠 (ePIGRAPHES)14奧諾雷.杜米埃肖像題詩 Vers Pour Le Portrait de M. HonoreDaumier
15瓦倫西的羅拉 Lola De Valence
16題「牢中的塔索」(德拉珂羅瓦所畫) Sur <> d’Eugene Delacroix
雜篇(PIeCES DIVERSES)17聲音 La Voix
18意想不到者L’Imprevu
19贖金La Rancon
20給一位馬拉巴姑娘A Une Malabaraise
戲作 (BOUFFONNERIES)21 阿米娜.波雪蒂初上舞台(於布魯塞爾莫奈劇院)
Sur Les Debuts d’Amina Boschetti
22 致歐金.福洛曼丹氏(關於某個令人討厭者自稱是他的朋友)
A M. Eugene Fromentin / A Propos d’un Importun / Qui Se Disait Son Ami
23戲謔的小酒店(從布魯塞爾到約庫耳途中所見)
Un Cabaret Folatre / Sur La Route de Bruxelles a Uccle
《惡之華》第三版增訂稿(1866-1868) PIeCES AJOUTeES1一本禁書的題詞 epigraphe Pour un Livre condamne
2致邦維爾(一八四二年作) A Theodore de Banville—1842—
3和平的菸斗(仿朗費羅) Le Calumet de Paix
Imite de Longfellow
4異教徒的祈禱La Priere d’un Paien
5蓋子 Le Couvercle
6午夜的反省 L’Examen de Minuit
7悲情的戀歌 Madrigal Triste
8警告者 L’Avertisseur
9叛逆者 Le Rebelle
10離此遙遠Bien Loin d’Ici
11深淵 Le Gouffre
12伊卡洛斯的悲嘆 Les Plaintes d’un Icare
13靜思 Recueillement
14被冒犯的月亮La Lune Offensee
波特萊爾年譜
萬物照應.東西交輝 / 杜國清
波特萊爾與我/ 杜國清
《惡之華》初版譯者後記 (1977)
《惡之華》新版譯者後記(2011)
序
譯者序 波特萊爾與《惡之華》
《惡之華》中差不多有一半是與女人有關的情詩。波特萊爾詩中 的女人一共有四個;她們在不同的時期使詩人留下優美與痛苦的詩篇。第一個是「斜眼的莎拉」 (Sarah la Louchette) ,巴黎拉丁區的猶太妓女。詩人因她寫了三首詩:即第二十五首〈你想將整個宇宙都帶進閨房〉,第三十二首〈一夜我睡在醜惡的猶太女身邊〉,另一首沒收在《惡 之華》中。詩人與莎拉的交往是在十九歲到二十一歲之間的三年,其中一年詩人離開巴黎前往南洋。兩人的關係並不深切,但是這種早期的戀愛體驗,對於日後詩人 的戀愛觀以及對女人的看法具有莫大的影響。
詩人的第二個女人是珍妮.杜娃 (Jeanne Duval) 。詩人認識她時二十一歲,而前後來往共二十年(一八四二—六一),其中經過了多少次的分離與重歡。珍妮.杜娃(或露美Lemer)是個黑白混血的女伶,個 子高大,肉體豐滿,具有豐厚的黑髮,銅色的皮膚、大大的眼睛、稍厚的嘴唇。她脾氣彆扭、生性冷酷。她與詩人有著短暫的幸福生活,可是也帶來爾後多年的不 幸。詩人對她盡情盡義,幾次向監護人和他母親要求讓珍妮繼承他的財產,可是她幾乎從一開始就對他不忠實,騙他、搶他,故意傷他。即使如此,詩人從來沒有失 去對她的責任感;每次分離,仍在經濟上盡力照顧她的需要。她是詩人一生的十字架。詩人對她的熱情,時而優柔,時而幾乎是憎恨。他們兩人像是一對歡喜冤家, 具有拆不散的孽緣。詩人因她而寫的詩,亦即所謂珍妮.杜娃詩篇 (The Jeanne Duval Cycle) ,根據史加福 (Francis Scarfe) 教授的判斷,有第二十二首〈異國的芳香〉、二十三首〈髮〉、二十四首〈我愛慕你……〉、二十六首〈然而還不滿足〉、二十八首〈舞動的蛇〉、二十九首〈腐 屍〉、三十首〈來自深淵的叫喊〉、三十四首〈貓〉、三十五首〈決鬥〉、三十六首〈陽臺〉、三十七首〈著魔的男人〉、三十八首〈幽靈〉、五十八首〈午後之 歌〉、一一五首〈貝雅翠斯〉等。
詩人的第三個女人是瑪利.朵白蘭 (Marie Daubrun) 。詩人跟她的來往是在二十六歲到三十八歲之間。她是個女伶和模特兒;金髮美人,綠眼珠,鼻子稍為朝上,嘴唇像玫瑰花蕾。詩人曾在他的朋友德瑞 (Deroy) 的畫室中貪婪地注視她的裸體。一八四七年,她在聖馬丁劇院主演〈金髮美女〉,頗為成功。詩人在寫給她的信中說:「由於你,瑪利,我將堅強偉大。像佩脫拉克 (Petrarch) ,我將使我的羅拉 (Laura) 不朽。請當我的守護天使,我的繆斯,我的聖母,引導我走著「美」的道路。」最初,詩人的追求遭到拒絕,因她當時對他的朋友班維爾 (Banville) 更有興趣。因此,詩人對她反而寄以柏拉圖式的愛情,直到一八五四年詩人對她的熱情復燃。可是在詩人為她的戲劇前途奔走失敗以後,她就離開詩人再投到班維爾 的懷抱。這種三角關係使詩人感到莫大痛苦和嫉妒。根據史加福教授的判斷,所謂瑪利.朵白蘭詩篇 ( The Marie Daubrun Cycle) ,包括第四十九首到五十六首的〈毒〉、〈陰空〉、〈貓〉、〈優美的船〉、〈旅邀〉、〈不能挽回者〉、〈談話〉、〈秋之歌〉,以及第六十四首〈秋的小曲〉與 第九十八首〈虛假的戀〉等。
詩人的第四個女人是莎巴伽夫人 ( Madame Sabatier) 。詩人跟她的交往是在三十一歲到四十歲之間。她是一個銀行家的情婦;她家的沙龍在經濟上是由銀行家支持的。她是個白膚金髮碧眼的美人,五官端莊,嘴上常帶 著微笑。她較有教養,富於機智,但是道德觀念頗無原則。她不避與崇拜者逢場做戲。詩人愛她,把她當做精神戀愛的對象。從一八五二年起,詩人不斷以匿名寫信 給她,同時附上情詩。她是詩人理想的結晶、靈感的泉源、崇拜的繆斯。詩人寫給她的匿名信和情詩,繼續了五年,直到一八五七年八月三十日,莎巴伽夫人以身相 許。可是那晚的幽會,對詩人而言,不是狂喜而是幻滅。在第二天寫給莎巴伽夫人的信中,詩人說:「幾天前你是女神,如今你是女人。」詩人對她的精神戀愛,於 焉告終。《惡之華》中所謂莎巴伽詩篇 ( The Sabatier Cycle ) ,包括從第四十首到第四十八首的〈永遠一樣〉、〈她的一切〉、〈今晚你說什麼……〉、〈活火炬〉、〈恩賜〉、〈告白〉、〈心靈的黎明〉、〈夕暮的諧調〉、 〈香水瓶〉,以及第六十二首〈憂愁與放浪〉等。
除了女人,波特萊爾的一生中,曾有一時對政治社會現狀頗為關心和參與。一八四八年二月革 命時,他站在群眾的一邊。在一八四八到一八五一年(二十七歲到三十歲)的革命時期,他的行動相當複雜與狂熱,但大體上是由於感情的衝動與一時的憤慨。不久 也就對社會主義幻滅,接著是對政治的冷感。雖然革命時期的影響,並不直接表現在詩中,波特萊爾在一八五○年和一八五一年預告他的詩集即將出版,當時的書名 卻擬為《冥府》(Les Limbes) 。《冥府》雖是個帶有濃厚神學色彩的用語,當時的社會主義者用以形容社會的一個狀態,含有時代與政治的意義。波特萊爾的詩,雖然沒有政治性的革命氣息,但 是有些作品含有現實主義的寫實精神卻是無可否認的。例如,屬於〈冥府詩篇〉中的〈殺人犯的酒〉(第一○六首)、〈拾荒者的酒〉(第一○五首)、〈窮人之 死〉(第一二二首),以及〈巴黎寫景〉中的〈七個老頭兒〉(第九十首)、〈小老太婆〉(第九十一首)、〈夕暮〉(第九十五首)、〈賭博〉(第九十六首)等 等。
《惡之華》中差不多有一半是與女人有關的情詩。波特萊爾詩中 的女人一共有四個;她們在不同的時期使詩人留下優美與痛苦的詩篇。第一個是「斜眼的莎拉」 (Sarah la Louchette) ,巴黎拉丁區的猶太妓女。詩人因她寫了三首詩:即第二十五首〈你想將整個宇宙都帶進閨房〉,第三十二首〈一夜我睡在醜惡的猶太女身邊〉,另一首沒收在《惡 之華》中。詩人與莎拉的交往是在十九歲到二十一歲之間的三年,其中一年詩人離開巴黎前往南洋。兩人的關係並不深切,但是這種早期的戀愛體驗,對於日後詩人 的戀愛觀以及對女人的看法具有莫大的影響。
詩人的第二個女人是珍妮.杜娃 (Jeanne Duval) 。詩人認識她時二十一歲,而前後來往共二十年(一八四二—六一),其中經過了多少次的分離與重歡。珍妮.杜娃(或露美Lemer)是個黑白混血的女伶,個 子高大,肉體豐滿,具有豐厚的黑髮,銅色的皮膚、大大的眼睛、稍厚的嘴唇。她脾氣彆扭、生性冷酷。她與詩人有著短暫的幸福生活,可是也帶來爾後多年的不 幸。詩人對她盡情盡義,幾次向監護人和他母親要求讓珍妮繼承他的財產,可是她幾乎從一開始就對他不忠實,騙他、搶他,故意傷他。即使如此,詩人從來沒有失 去對她的責任感;每次分離,仍在經濟上盡力照顧她的需要。她是詩人一生的十字架。詩人對她的熱情,時而優柔,時而幾乎是憎恨。他們兩人像是一對歡喜冤家, 具有拆不散的孽緣。詩人因她而寫的詩,亦即所謂珍妮.杜娃詩篇 (The Jeanne Duval Cycle) ,根據史加福 (Francis Scarfe) 教授的判斷,有第二十二首〈異國的芳香〉、二十三首〈髮〉、二十四首〈我愛慕你……〉、二十六首〈然而還不滿足〉、二十八首〈舞動的蛇〉、二十九首〈腐 屍〉、三十首〈來自深淵的叫喊〉、三十四首〈貓〉、三十五首〈決鬥〉、三十六首〈陽臺〉、三十七首〈著魔的男人〉、三十八首〈幽靈〉、五十八首〈午後之 歌〉、一一五首〈貝雅翠斯〉等。
詩人的第三個女人是瑪利.朵白蘭 (Marie Daubrun) 。詩人跟她的來往是在二十六歲到三十八歲之間。她是個女伶和模特兒;金髮美人,綠眼珠,鼻子稍為朝上,嘴唇像玫瑰花蕾。詩人曾在他的朋友德瑞 (Deroy) 的畫室中貪婪地注視她的裸體。一八四七年,她在聖馬丁劇院主演〈金髮美女〉,頗為成功。詩人在寫給她的信中說:「由於你,瑪利,我將堅強偉大。像佩脫拉克 (Petrarch) ,我將使我的羅拉 (Laura) 不朽。請當我的守護天使,我的繆斯,我的聖母,引導我走著「美」的道路。」最初,詩人的追求遭到拒絕,因她當時對他的朋友班維爾 (Banville) 更有興趣。因此,詩人對她反而寄以柏拉圖式的愛情,直到一八五四年詩人對她的熱情復燃。可是在詩人為她的戲劇前途奔走失敗以後,她就離開詩人再投到班維爾 的懷抱。這種三角關係使詩人感到莫大痛苦和嫉妒。根據史加福教授的判斷,所謂瑪利.朵白蘭詩篇 ( The Marie Daubrun Cycle) ,包括第四十九首到五十六首的〈毒〉、〈陰空〉、〈貓〉、〈優美的船〉、〈旅邀〉、〈不能挽回者〉、〈談話〉、〈秋之歌〉,以及第六十四首〈秋的小曲〉與 第九十八首〈虛假的戀〉等。
詩人的第四個女人是莎巴伽夫人 ( Madame Sabatier) 。詩人跟她的交往是在三十一歲到四十歲之間。她是一個銀行家的情婦;她家的沙龍在經濟上是由銀行家支持的。她是個白膚金髮碧眼的美人,五官端莊,嘴上常帶 著微笑。她較有教養,富於機智,但是道德觀念頗無原則。她不避與崇拜者逢場做戲。詩人愛她,把她當做精神戀愛的對象。從一八五二年起,詩人不斷以匿名寫信 給她,同時附上情詩。她是詩人理想的結晶、靈感的泉源、崇拜的繆斯。詩人寫給她的匿名信和情詩,繼續了五年,直到一八五七年八月三十日,莎巴伽夫人以身相 許。可是那晚的幽會,對詩人而言,不是狂喜而是幻滅。在第二天寫給莎巴伽夫人的信中,詩人說:「幾天前你是女神,如今你是女人。」詩人對她的精神戀愛,於 焉告終。《惡之華》中所謂莎巴伽詩篇 ( The Sabatier Cycle ) ,包括從第四十首到第四十八首的〈永遠一樣〉、〈她的一切〉、〈今晚你說什麼……〉、〈活火炬〉、〈恩賜〉、〈告白〉、〈心靈的黎明〉、〈夕暮的諧調〉、 〈香水瓶〉,以及第六十二首〈憂愁與放浪〉等。
除了女人,波特萊爾的一生中,曾有一時對政治社會現狀頗為關心和參與。一八四八年二月革 命時,他站在群眾的一邊。在一八四八到一八五一年(二十七歲到三十歲)的革命時期,他的行動相當複雜與狂熱,但大體上是由於感情的衝動與一時的憤慨。不久 也就對社會主義幻滅,接著是對政治的冷感。雖然革命時期的影響,並不直接表現在詩中,波特萊爾在一八五○年和一八五一年預告他的詩集即將出版,當時的書名 卻擬為《冥府》(Les Limbes) 。《冥府》雖是個帶有濃厚神學色彩的用語,當時的社會主義者用以形容社會的一個狀態,含有時代與政治的意義。波特萊爾的詩,雖然沒有政治性的革命氣息,但 是有些作品含有現實主義的寫實精神卻是無可否認的。例如,屬於〈冥府詩篇〉中的〈殺人犯的酒〉(第一○六首)、〈拾荒者的酒〉(第一○五首)、〈窮人之 死〉(第一二二首),以及〈巴黎寫景〉中的〈七個老頭兒〉(第九十首)、〈小老太婆〉(第九十一首)、〈夕暮〉(第九十五首)、〈賭博〉(第九十六首)等 等。
↧
胡適 未完成的雕像 (夏菁 1963) 蒲公英/《窺豹集》
夏菁,科羅拉多大學碩士,曾任聯合國專家及科州大學教授。早年在台,曾發起「藍星詩社」,主編《藍星詩頁》、《文學雜誌》及《自由青年》等新詩刊。已出版詩集《噴水池》、《雪嶺》、《獨行集》、《折扇》等十二種,以及散文《落磯山下》、《船過無痕》等五本。現居美國。
日 前在秀威出版社所出版的新著《窺豹集》,是夏菁談論現代詩的文集,收集了他早年在《公論報》、《聯合報》、《藍星詩頁》、《文星雜誌》、《自由青年》等刊 出的作品;台灣新詩論戰時的文章,以及近年來在台、港和美國發表的對話及訪談錄等,共計四十篇。夏菁是台灣藍星詩社的成立者之一,後附〈早年的藍星〉一 文,是他對台灣早年三大詩社之一的「藍星詩社」成立經過及其成員,所作的生動描述,是台灣-新詩發展史上的寶貴資料。
*****
......你已走向歷史
塑成永恆的微笑
春來時
它將如迎面的蒲公英
對你的塑像
尚待我們自心底完成
胡適 未完成的雕像
此詩寫於1963年2月22日 胡適逝世周年
『山』夏菁著 民國66年初版台北: 純文學發行.頁106-110
夏菁在同一本詩集 再用過蒲公英
"一球蒲公英險將我擊中
那許是愛蜜麗的戲弄"
****
這樣的助人為樂的想法和行為,已像蒲公英似的向下傳播扎根。
---****
6 月 1, 2010 at 4:19 pm
春雪
春雪夾帶著和靄的氣氛灑落著片片的柔情
假如對嚴冬你感到厭棄
現在會掀起再生的歡喜
在這一年開始的時光
總會有一種希冀和渴望
不管今年會帶給我們
什麼樣的喧鬧或繽紛
此刻,世界是如此靜謐
遠遠只聽到微風的呼吸
可是,它短得像一幕啞戲
受不了太陽的逼視和妒嫉
看著一片片落地即融的雪花
今生今世有什麼可以真正留下?
二○○七‧五‧十五
◎資料來源﹕夏菁《獨行集》,秀威資訊科技有限公司,2010年1月。
6 月 1, 2010 at 4:17 pm
獨行
在四顧茫茫的雪地一個人踽踽獨行
沒有風,也無鳥啼
唯有雪的寧靜
我闖入一片林裡
只聽到自己的跫音
車聲已遠在天際
我有顆不競的心
回頭所能看見
一徑鴻爪般的腳印
這些能否留到明天
誰也不能肯定
也沒有什麼理由
踏上這一條僻徑
現在,已快到盡頭
無悔,靠一點自信
二○○五‧四‧十四
◎資料來源﹕夏菁《獨行集》,秀威資訊科技有限公司,2010年1月。
7 月 14, 2008 at 4:44 pm
手稿一

7 月 14, 2008 at 4:43 pm
作家身影一

8 月 11, 2006 at 8:34 pm
夏菁小傳
本名盛志澄,1925年10月6日出生,浙江省嘉興縣人。美國科羅拉多州立大學碩士,為土壤保持專家。浙江大學畢業隨即來台,並於花 蓮山林管理所木瓜山林場任職。之後被中美合作的農村復興委員會羅致,下山到台北,因而開啟創立「藍星詩社」的契機。1954年由於不滿當時口號充斥的詩 壇,於是邀集鄧禹平、余光中、覃子豪等人創立「藍星詩社」。在夏菁的主導之下,藍星詩社於1958年12月10日發行詩刊《藍星》詩頁。除了主編藍星詩社 詩頁外,也同時主編《文學雜誌》及《自由青年》之新詩專欄。1954年出版第一本詩集《靜靜的林間》。1968年首部散文集《落磯山下》出版。1968年 應聯合國聘請前往牙買加服務,1985年自聯合國退休,又任教於科羅拉多州立大學,現已退休,旅居美國。工作之餘,仍發表作品於台灣及美國中文報章刊中。1999年出版以森林文化和生態意識為主題的詩與攝影合集《回到林間去:山、林人的融合》,融合攝影與文學傳達出對大自然的愛。2004年散文 集《可臨視堡的風鈴》,讓人見到詩人永遠不老的創作精力。夏菁創作以詩和散文並行,詩風婉約典雅,具有濃厚的東方精神;散文則簡約生智,親和真摯。
散文家梁實秋曾評介夏菁的散文:「夏菁通數國文字,嗜英美文學,然其散文絕無時下習氣,清談娓娓,勝語直尋,中國人使用中國文字,固當如此。」 夏菁的詩在50年代初便已馳名,雖然70年代後便旅居海外,但對新詩投入的熱情絲毫不減。夏菁曾在70年代提出詩必具有「可讀性」的主張,他認為:「用字 不妨精簡、淺近,內容則新銳、深遠」,所以夏菁的詩作平易近人、清新可讀,無疑是服膺他的創作理念。
8 月 11, 2006 at 8:30 pm
夏菁大事年表
1925年 10月6日出生,為浙江省嘉興縣人。1954年 邀集鄧禹平、余光中、覃子豪等人創立「藍星詩社」。
同年由藍星詩社出版第一本詩集《靜靜的林間》。
1957年 出版詩集《噴水池》。
1958年 12月10日發行詩刊《藍星》詩頁。
1961年 由香港中外文化公司,出版詩集《石柱集》、《石標集》。
1964年 出版詩集《少年遊》。
1968年 應聯合國聘請前往牙買加服務。
出版第一本散文集《落磯山下》。
1999年 出版詩與攝影合集《回到林間去:山、林人的融合》,融合攝影與文學傳達出對
大自然的愛。
浙江文藝出版《夏菁散文》。
2003年 出版詩集《雪嶺》,收入1998~2003年的詩作,由未來書城出版。
2004年 香港銀河出版社發行《夏菁詩選》。
出版散文集《可臨視堡的風鈴》,收集夏菁到可臨視堡,在大學執教以及退休以來
的作品,為夏菁第四本散文集。
8 月 11, 2006 at 8:27 pm
出版書籍
出版書籍1954年 《靜靜的林間》,台北:藍星詩社。
1957年 《噴水池》,台北:明華。
1961年 《石標集》,香港:中外文化。
1961年 《石柱集》,香港:中外文化。
1964年 《少年遊》,台北:文星。
1968年 《落磯山下》,台北:藍星。
1977年 《山》,台北:純文學。
1980年 《落磯山下》,台北:遠流。
1985年 《悠悠藍山》,台北:洪範。
1998年 《澗水淙淙》,台北:九歌。
1999年 《回到林間去:山、林與人的融》,台北:台灣省林業試驗所。
1999年 《夏菁散文》,浙江:浙江文藝。
2003年 《雪嶺》,台北:未來書城。
2004年 《夏菁詩選》,香港:銀河。
2004年 《可臨視堡的風鈴》,台北:印刻。
8 月 11, 2006 at 8:24 pm
品評作家--〈清流一溪自在詩〉
◇文選自〈清流一溪自在詩〉橫貫整個二十世紀下半,夏菁的詩歌創作,始終如一溪細長的清流,不顯風浪、不事喧嘩,蜿蜒縈迴於台灣當代師各的浩浩流程之中。不即不離,欲忘尤 記,如此特別的創作型態,是理解夏菁詩歌的風貌的微妙入口。欣賞夏菁的詩,易,且親和無隔,很愜意,如沐清風,如飲清泉,如品「綠色食品」,爽目爽口(誦 之有音樂美感)爽心。評價夏菁的詩,則難,難在找不到特別的說法,那些新潮的、時髦的、所謂學術化的理論話語,在如此中正和平的詩風面前,皆難免失語。
8 月 11, 2006 at 8:21 pm
期刊論文彙編
期刊論文1969年 莫 渝:〈笠下影─夏菁〉,《笠詩刊》4月,頁48-50。
莫 渝:〈新詠舊唱,綜談夏菁的詩〉,《新詠舊唱》,頁45-47。
1970年 余光中:〈宛在水中央〉,《純文學》,頁47。
1972年 白 萩:〈評夏菁的詩集「靜靜的林間」〉,《現代詩散論》,頁149-163。
1977年 余光中:〈山名不用〉,《純文學》。
1985年 季 予:〈評《噴水池》〉,《文學雜誌》5卷3期,頁80-86。
1985年 梁實秋:〈(悠悠藍山)序〉,《悠悠藍山》。
1985年 楊 牧:〈夏菁的詩〉,《風簷展書讀》,頁372-377。
2004年 余光中:〈序短賀壽長〉,《可臨視堡的風鈴》。
8 月 11, 2006 at 8:15 pm
報上評論彙編
報上評論1953年 梁實秋:〈閒話新詩–讀余光中夏菁的新詩集〉,《中央日報》5版12月13日。
1985年 向 明:〈我讀悠悠藍山〉,《自立》11月7~9日。
1985年 梁實秋:〈平淡雋永〉,《聯合報》8版7月15日。
1998年 向 明:〈澗水淙淙流日月–讀夏菁的詩和人〉,《中央日報》22版11月14日。
1999年 麥 穗:〈靜靜林間的一潭澗水〉,《台灣新聞報》4月30日。
2000年 林峻楓:〈松林裡的清露〉,《青年日報》7月1日。
2003年 侯延傾:〈雪嶺〉,《中央日報》17版10月22日。
↧
余英時訪談錄
歷史學家余英時雖然堅持反共立場,但他的著作卻在大陸廣泛流傳,筆端飽含人文情懷,思想影響華人世界。有人形容繼2004年「錢穆熱」之後,中國知識界興 起「余英時熱」。余英時17日在普林斯頓寓所,欣然接受世界日報兩小時專訪,話題廣泛,從中共一黨專政到習李體制,從習近平的中國夢到他本人的「人類夢」 等。余英時表示,他對中國前途並不悲觀,並堅信中國傳統文化不會消失,總有一天會回歸文明的主流。以下是訪談摘要。
◆貪官妻、子送海外 對政權沒信心
問:近年來「中國崛起」似乎是海內外共同的看法,就您的觀察,中國是不是真正的崛起了?中國現狀究竟應該如何看待?
答: 我不認為中國真正崛起了,中共政權也不可能長期維持,政治制度一定要有變革。中國大陸現在貧富懸殊情況嚴重。沿海一帶上億人發財,但大都是跟共產黨官員有 密切關係的人,不是其家人就是親友。所謂「肥水不落外人田」。不知道有多少共產黨貪官,都把太太子女送到海外,也不知有多少錢存到海外,如果他們對自己的 政權有信心,就不會這樣做。
中共維穩費預算近年已超越軍費,兩會期間,北京動員80萬人安保維穩,更有異見人士被多人帶離京城去外地「公費 旅行」。我表妹是「天安門母親」,每次有人看望她或有什麼風吹草動,一家人就被送去福州、杭州等地旅行,一去就一、二十天,陪伴他們的官員也很高興,一起 免費旅遊。這也是維穩費為何支出如此巨大的原因。這樣的社會就維持長久嗎?任何有常識的人,都知道這是不可能長久的。
我相信中共政權將來是有變化的,總有一天維持不下去。但變得如何,尚不敢斷言。
◆集體世襲制度 貪污腐敗根源
問:您說不看好習近平的「中國夢」,您看好習近平的領導能力嗎?習李體制面臨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答: 不少人對習李體制有期待,其實能有什麼期待,只是喊喊口號而已。他們有個調查,訪問了幾千人,結果大約百分之七、八十的人不承認共產黨執政,本來他們以為 大家會熱烈響應,結果恰恰相反,只好不了了之,不敢公開。但仍然有部分資料漏出來,被香港雜誌發表。這反映一個很大問題,大家對共產黨沒有信心。
我 沒有把共產黨看得這麼偉大。因為中國的貪污腐敗現象太普遍了,很多有錢人都跑到外國,都在國外留了後路。有的人雖然留在中國工作,但有護照在手,準備隨時 可以走。這就表示,他們並不認同共產黨,並沒有認為中國有一個夢可以把他們留下來繼續工作。中共目前是集體世襲制度,108個太子黨擁有萬億財富,操控 168家國企。
另一方面,貪官每年逃出來的人數上萬,很多錢都流出來,抓到的雖然不少,但畢竟是小部分,像這樣的人是否認同中國夢?如果喊的口號連自己都不相信,什麼偉大社會?某些海外華人,可能因為民族主義情緒表示認同,但真正瞭解中共現實情況的人不會認同。
問:那麼,您的「中國夢」是什麼?
答: 我沒有「中國夢」,有的只是人類的夢,我的「夢」就是大家平平安安,要做什麼就做什麼,想說什麼就說什麼。這樣的社會才是我的夢。我沒有要中國非常強大, 凌駕於世界,這是中國人的虛榮心作祟。這種民族主義不是好東西,中共現在唯一能利用、有號召力的就是這點。民族主義應該只有被侵略時才應該有,那是為了讓 大家團結起來抵抗外侮。
我們看全世界最提倡民族主義的德國與日本,最後都沒有好下場。可是,現在一些人很受民族主義影響,認為一百多年來被人欺負,希望「站起來」,讓別人看到你就要膜拜,非要到這地步才能滿足,那恐怕會走上自我「毀滅之路」。
◆2.5億農民城鎮化 毛澤東式大躍進
問:您最近提到城鎮化時,認為這是對中國的一大傷害。但這項政策已開始推動,未來會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中國」?
答: 中共提倡的城鎮化,是毛澤東式的大躍進。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社會,把2億5000萬的農民從農村大批地搬遷到城市來,所有土地被中共拿掉,作為賺錢的手 段。現在大陸各地老百姓抗議最多的是拆遷。現在有些地區已開始實行城鎮化,如陝西已開始把農村人搬到城市,但困難非常多,首先是找工作極為困難,他們缺乏 這個基礎,有些人想回去,但原來住的地方沒有了。
中共有兩樣東西最可怕,一是勞教,一是城管。城管到處造成危害,動不動就把人抓起來,送去勞改或勞教,完全靠暴力征服。這樣搞下去,還是會回到秦始皇時代。
問:看到突尼西亞、埃及這樣阿拉伯之春的發展,難道北京當局不擔心?
答:中共對這種運動非常驚心注意,對他的政權是一大威脅。但民主也不是是那麼容易到手的,要取決老百姓的教育與品質,要相對的教育、相當的傳統、相當的尊重反對派,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
我 不認為一下子就可以跳到民主。台灣因為教育好、幾十年的發展,加上日本殖民的關係,還有中國五四以來的科學民主東西,都是可以公開談論的。但是現在共產黨 不准談民主科學,像是最近所謂的「七不講」,還是毛澤東那一套,什麼能講,什麼不能講,或是鄧小平的「四個堅持」,這些都是中共不能動、不能談、不能討論 的。
◆回中國須否定自己 並不心安理得
問:您追求自由、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隨著中國崛起與您的年齡增長,中國想盡辦法勸您回去,雖然您常公開批評中共政策,但大部分作品已在中國出版。許多海外的中國知識人,年老時都有懷鄉與文化歸屬的情懷,您堅持不回中國嗎?
答:第一我不喜歡熱鬧,如果我回去,到處開座談會、演講,我受不了,我現在也不談政治。第二基本上是價值問題,這與六四無關。但要我否定自己所有一切才能回去,並不心安理得,我首先就看不起自己了。
我去不去大陸不重要 ,我不去還好,至少有一個人、而且我相信不止一人,讓人知道有人這麼做,而且這人還活著,不是非回大陸才能吃飯,這還是有意義的。
美國給我最大的自由,生活在一個自由的世界,我不要求別人跟我的看法一樣,別人跟我的看法一樣,我並不特別高興,每個人都應有自己的看法和觀點。
問:若中共放棄一黨專制,您會否考慮回大陸?
答:如果中共放棄一黨專制,我馬上去。
問:六四與文革是中共至今不願面對的難堪,也是不能動搖的統治基礎。但北京當局對這個歷史傷痕始終不願認真面對,您看六四能平反嗎?
答:我認為六四不存在「平反」的問題,只要中共政權存在的一天,他們永遠不會面對六四問題,否則他們就垮台了,而且六四也不應叫「平反」。
「六四」後很多人認為中共很快會垮台,但他的組織太厲害,這裡面也有個氣數問題。
問:您為什麼堅持反共?您對中國前途還樂觀嗎?
答: 我的看法從19歲就形成了,但我不是為了反共而反共。我對中國前途並不悲觀,中國傳統文化不會消失,中國有些東西是生了根的,如祭祖、同鄉會等「老東 西」,還有溫柔敦厚、人情味等,我相信慢慢還會回來。將來我們還要過正常生活,現在鬥爭太多,尤其共產黨一天到晚講階級門爭,但相信共產黨不會永遠存在, 將來總有一天會回歸文明的主流。
◆堅守民主價值 台灣保持軟實力
問:您也提到台灣經驗,是否可輸出到中國大陸,可是近年來台灣因經濟起不來,似乎也沒有自信再常提台灣經驗?
答: 這就是台灣的最大問題,台灣有很大的心理問題,包括國民黨在內,就是畏共怕共,怕得不得了。一是怕他打過來,好像完全不能抵抗,另外一種就是怕台獨,於是 就想用對岸來控制台獨。這種想法是很自私的想法,說老實話,如果繼續這樣子顧忌下去,那最後只有向共黨產投降。如果這樣子,那當初何必跑到台灣來,在南京 簽字投降不就完了嗎。
台灣政府跟共產黨打交道要有原則,民主自由這套價值觀要保持。像是盲人維權人士陳光誠去台灣,不但總統馬英九不敢見, 連文化部長龍應台都不出來,沒有出息到極點了,在我看來是很丟臉,不是什麼光彩的事,好像擔心共產黨會找你麻煩。老實坦白的說,對台灣目前的態度,我很失 望,甚至不客氣的說,我看不起了。我以前對台灣有一種期待,我也知道台灣有不盡如意之處,但對抗共產黨的決心不能沒有。
一個以反共為始的政 府,怎麼能搞到這個地步呢?跟共產黨不是不可以打交道,三通都可以,但在政治上是不能讓步的。我對馬英九不瞭解,在我認識中是個蠻好的一個人。但我想他在 黨內的壓力很大,就像大陸內部一樣,有想法也施展不出來。配合有錢的台商做生意,少數人生活很舒服,就不管下面的人了,現在拚命拿大陸的好處,這樣百姓會 離政府越來越遠。
問:您認為兩岸之間來往,台灣自信何在,有沒有外界普遍認知的「軟實力」?
答:照理說,台灣在文化上有實 力,是絕對高於大陸的,特別是那種有人情味的中華文化。而且台灣現有的社會是大家都接受的,沒有人說要把他推翻來重新再搞一個。這是一個很大的穩定力量, 台灣自己不覺得,你看中共花多大的力氣去維穩,如果每個人都覺得不推翻這個制度否則自己不能活,就是很危險的狀態。
問:各國與中共打交道時,似乎都擔心萬一中共垮台,中國不穩會帶來災難……
答: 對,但大家把維穩不成的後果看的很嚴重,我覺得中共所謂的維穩,目的是在共產黨不要失去政權。可是我覺得中國不會大亂,只是慢慢的不聽中央指揮的情況。現 在,不會讓中共得心應手地使用暴力統治。所以中共所謂的維穩是誇張的,認為沒有中共,中國就會亡了,就會亂了,但沒有這麼可怕。
◆余英時小檔案
余英時,著名歷史學家、漢學家。祖籍安徽潛山,1930年1月22日生於天津。
●學歷:
燕京大學肄業,香港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生,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先後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和當代漢學泰斗楊聯陞。
●經歷:
美國密西根大學助教授、哈佛大學教授、香港新亞學院校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美國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康乃爾大學首任胡適講座訪問教授(1991-1992)。2001年6月自普林斯頓大學教職退休。
●學術榮譽:
台灣中央研究院第10屆院士(1974)
香港中文大學榮譽法學博士(1977)
美國明德學院榮譽文學博士(1984)
香港大學榮譽博士(1992)
美國哲學會院士(2004)
美國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2006)
●主要著作:
出 版書籍30多部,重要著作包括: 「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史學與傳統」、「歷史與思想」、「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方以智晚節考」、 「論戴震與章學誠」、「紅樓夢的兩個世界」、「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兼論他的學術精神與晚年心境」「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朱熹的歷史世 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等。
*****
這本書常提到胡適錢穆......等等人物
不只是"胡適的學位與自由之精神"一節
處處有識見
余先生很用功讀經典 諸如
余英時訪談錄北京 (3刷2萬本) /香港 中華書局 2012
我走過的路:余英時訪談錄
作者:陳致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2年
我走過的路(余英時)
直入塔中,上尋相輪克魯格獎
政治、黨爭與宋明理學
清代考據學:內在理路與外部歷史條件
最後一位風雅之士:錢鍾書先生
以通馭專,由博返約:錢賓四先生
國學與現代學術
學問與性情,考據與義理
「直入塔中」與「史無定法」
「哲學的突破」與巫的傳統
「內向超越」
胡適的學位與自由之精神
民族主義與共產主義
人文邊緣化與社會擔當
西方漢學與中國學
宗教、哲學、國學與東西方知識系統儒家思想的宗教性與東西方學術分類
國學、「國學者」與《國學季刊》
哲學與思想:東西方知識系統
哲學與抽象的問題
文化熱與政治運動
知識人:專業與業餘
治學門徑與東西方學術哈佛讀書經驗
早歲啟蒙與文史基礎
先立其大,則小者不能奪
洪煨蓮(業)與楊聯陞
俞平伯與錢鍾書
學術與愛國主義
取法乎上
西方漢學與疑古問題
為了文化與社會的重建(劉夢溪訪談)關於錢穆與新儒家
學術不允許有特權
學術紀律不能違反
「天人合一」的局限
怎樣看「文化中國」的「三個意義世界」
學術立足和知識分子的文化承擔
「經世致用」的負面影響
中國學術的道德傳統和知性傳統
中國傳統社會的「公領域」和「私領域」
中國歷史上的商人地位和商人精神
如何看待歷史上的清朝
東西方史學觀念和研究方法的異同
最要不得的是影射史學
文化的問題在社會
社會的問題在民間
後記
余英時教授著作目錄
陳:這兩年我們知道先生的《朱熹的歷史世界》在學界影響很大。我前段時間也在看這本書,您在自序中說到本來是給《朱熹文集》寫序的,結果寫成了一部大著作,這是不是有點兒像梁任公(啟超)寫《清代學術概論》那樣?
余:那倒還不一樣。梁任公寫清代學術,他本來已經很熟悉有清一代的學術變遷,然後用十幾天的時間概括出來,寫成六七萬字的長序,最後獨立成書。他 並沒有再作新的研究。我是本想介紹一下朱熹的思想怎麽産生的背景的,但研究不斷展開後,就發現了許多問題。以至範圍越來越大,最後變成思想史和政治史雙管 齊下,不是專講朱熹一個人了。我特別注意他的歷史背景。隨著問題的不斷複雜化,我又發現了許多前人未注意的新史料。比如說周必大的全集,有二百多卷,裡面 有很多源文件,還有許多奏摺,都沒有人看過。看過的人也對很多前因後果沒太注意,其中可以瞭解到朱熹和當時的政治關係有多深,比如慶元黨禁。我現在把朱熹 在政治上的活動,和他在政治上成爲精神領袖的原原委委全部找出來。這中間他和政治直接牽涉至少有十幾年的時間,的確牽連到權力集團和權力鬥爭,是保守的官 僚集團和一個想有作爲的以理學家爲中心的集團之間的矛盾衝突。後者是有理想有抱負的,希望革除弊政,有徐圖規複的宏偉計劃。這與希望維持現狀的一群人形成 矛盾。這中間還牽涉到祖孫三代皇帝之間的矛盾,所以頭緒繁多到不可想像的程度。我是足足花了兩三年的時間才整理清楚的。
陳:這部書的角度我覺得比較特別。因為以前研究宋代理學,主要是從思想史的內部看,很少從政治生態和政治文化的角度來看。而您在以前研究清代思想,認為清代考据學的興起是由宋明以下理學發展的內在理路(innerlogic)給逼出來的,這與研究朱熹的角度好像正好相反。
余:情況不同,因爲對清代的研究,以前從外部聯繫比較多,如說滿洲人入關以後大家不敢講大問題,有些歷史上的忌諱,逼得大家去做考證工作。這個我 覺得是一個解釋。還有解釋就是清朝人反對理學。這些解釋並不是說不對,而是偏了,把思想內部的問題反而忘了。內部有兩個線索,一個是哲學上的爭論,朱、陸 和朱、王之爭,使理學把考據給逼出來了,非考證不能解決問題。像毛西河(奇齡)是王學的人物,閻百詩(若璩)是尊朱子的。在此之前更早有與王陽明同時的羅 欽順,他在《困知記》裡已經提出取證經書,分判經書裡哪些是假的哪些是真的,這就逼著你回到原典。而王陽明一定要講《古本大學》,這一點就是哲學的爭辯引 向經典的真假遲早的問題,其中是有內在變化的。我研究宋代思想是因爲幾百年來多講內部思想紛爭。傳統的說法集中在「理」與「心」之爭,大陸上說客觀唯心論 主觀唯心論什麽的,都不免只講內部,不問外緣關係。這和清代學術研究的取向相反,也不免陷於一偏。但那時候思想的爭論事實上和黨爭之間有關係,這是沒有人 解釋的。好像北宋王安石的理學、新學到南宋時候已經沒有了。二程與王安石之間的新學之爭,由此發生的政治之爭,似乎到南宋時整個不見了,其實不然。王安石 改變社會並不是爲了只是發明一條道理,或者說與佛教鬥爭。這對兩宋的學術來說是講不清楚的。
陳:所以您講原來的兩宋思想研究有抽離的問題。但後來也有一些爭論,您又寫了文章叫《「抽離」、「回轉」與「內聖外王」》,再申論這個問題。那些文章我也 都看了。您講抽離是說哲學史家在談兩宋理學發生發展的研究中,一是把道學從儒學中抽離出來;二是把道體又從道學中抽離出來。您能不能再解釋一下這個「抽 離」的概念,您是怎麼想的?
余:我所說的「抽離」是就思想史或哲學史上對於宋、明「道學」(或廣義的「理學」)的處理方式而言,其中包括三個層次。第一層是將全部宋、明儒學 從一般政治、社會、文化的歷史脈絡中抽離出來,當做一種純學術思想的動態來觀察。第二層是進一步將「道學」從全部儒學中抽離出來,建構出種種形上系統。第 三層則是將「道體」從道學中抽離出來作精微的分析,以確定其作爲儒家形上實體的性質。這是因爲宋明道學中本有程、朱「性即理」和陸、王「心即理」的兩大對 立系統,一直存在著誰得「道統」真傳的爭論。在現代中國哲學史研究中,這一爭論又以不同的面貌出現。我並不是反對「抽離」,甚至承認以哲學分析而言,「抽 離」是必要的。但是我在《朱熹的歷史世界》一書中,是從歷史觀點處理宋、明道學和政治文化的關係,採取了與「抽離」相異的方式;在歷史分析之外,更注重綜 合。我一向強調「史無定法」,研究方法往往因物件而異。所以我用「抽離」一詞僅僅是關於研究方法的一種描述,並不含絲毫貶斥之意。
陳:您所建構的關於理學的歷史面貌好像和一般的講法很不一樣?
余:這是因爲我的觀察角度不同,提出的問題不同,對於儒學性質的斷定也不相同。宋儒繼承了孟子與韓愈的「道統」說,一開始便提倡回向「二帝」 (堯、舜)「三王」(夏、商、周)之「道」,可見他們最關切的中心問題是重建一個合於「道」的人間秩序,而政治秩序(「治道」)尤其處於關鍵性的地位。所 以在道學興起以後,張載就明白地說「道學」和「政術」是一事的兩面;他的《西銘》則代表了道學家理想中的人間秩序,因此成爲二程教學的經典文本。程頤也說 過「道學輔人主」的話。道學承北宋儒學復興大運動而起,整體的規劃並無改變。這一整體規劃,用孔子的話說,便是怎樣變「天下無道」爲「天下有道」,但北宋 儒者追求「天下有道」的使命感更強烈了,也更具體了。在這一理解下,強調「心、性」修養的「道學」也必須看做是當時儒家整體規劃(the Confucian project)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我們似乎不宜將「心、性之學」單獨挑出來,當做道學的全部。道學在心、性問題上確和佛教有分歧,但北宋儒學復興也不 能簡單地理解爲韓愈辟佛運動的延續和擴大。這是因爲北宋的佛教轉變了,同樣有「入世」的一面。釋氏之徒也希望「天下有道」,並且把這一希望寄託在儒家身 上,從智圓到契嵩無不如此。
陳:所以您對王安石改革和道學之間的關係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您是否可以簡單地概括幾句?
余:王安石改革代表了北宋儒家整體規劃的行動或實踐階段。行動的要求在范仲淹慶歷時期短暫改革中已出現,不過時機仍未成熟。範提倡「士」以「天下 爲己任」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是宋代「士」的精神最扼要的概括,影響極大,見於石介、蘇軾、黃庭堅等人的文集之中。王安石也是在這一 精神之下成長起來的。他的「新學」以儒家經典(特別是《詩》《書》《周禮》)爲根據,加上佛教大乘精神的啓發,已具備道學家以來所發展的「內聖」、「外 王」互相支援的規模。所以在熙甯變法開始時,道學家程顥也參加了王的改革總部—「三司條例司」。儘管道學與「新學」在具體內容上存在著不少差異,但二者的 目的和思想結構是大致相似的,因此才有極短暫的合流。後來雙方鬧翻了,王安石的固執固然要負一部分責任,道學家的意氣過盛也未嘗沒有責任。程頤事後反思, 也承認「吾黨爭之有太過……亦須兩分其罪」。總之,王安石能爭取到神宗的全力支援,使儒家的整體規劃有實現的可能—即所謂「得君行道」—這是當時各派士大 夫都一致擁護的。不但程顥參與新法,劉摯(胡瑗的弟子)和蘇轍最早也同在「三司條例司」工作。朱熹說「新法之行,諸公實共謀之」,這是很中肯的歷史論斷。 王安石與道學的關係在南宋仍然餘波不斷,這可以分兩方面來看。第一,就王氏「新學」而言,通過科舉,它已成爲官學。高宗一朝執政的官僚仍多由「新學」出 身。雖有人提倡「程學」與「王學」相抗,想用二程的道學在科舉考試上取代「王學」,終不能敵。關於這一點,只要讀朱熹的《道命錄》,便可知其大概。道學在 南宋成爲顯學是張栻、朱熹等人出現以後的事。第二,王安石所樹立的「致君行道」的典範對南宋道學家繼續發揮啓示作用。這是因爲南宋道學仍然遵守北宋儒學變 「天下無道」爲「天下有道」的大綱領。朱熹、張栻、呂祖謙、陸九淵等人在政治上都非常積極,希望說服孝宗進行「大更改」。他們並不是「袖手談心性」的人, 而是要改變現狀,建立合乎「道」的新秩序,然後恢復失去的半壁山河。所以他們先後都捲入了權力世界的衝突,終於慶元黨禁。詳情這裡不能談了。
陳:讀您的著作,我有一個很強的印象,就是您特別強調當時士大夫要與君主「共治天下」的觀念。特別講到宋代理學的出現這些問題,讓人覺得與以前的常識不太 一樣。您是不是認爲傳統士大夫的政治使命感超過了他們的道德使命感?在對王陽明研究的時候,您說他有一個很重要的思想就是「覺民行道」。這是宋代士大夫與 君主「共治天下」和「致君行道」不成功之後的邏輯發展,還是主要是明代的政治現實造成的?
余:士大夫與皇帝「共治天下」是宋代儒家政治文化的一個最突出的特色,已預設在「士當以天下爲己任」這句綱領之中。用現代話說,宋代的「士」充分 發展了「政治主體」的意識:他們要直接對政治秩序負起責任。所以「共治天下」的觀念同時必然涵蘊了對於皇權的限制。「天下」不屬於「一人」或「一家」,而 是「天下人之天下」;「士」則自居爲代「天下人」參與政治、議論政治,因爲他們來自民間各階層。「致君行道」首先要求「君」的言行必須合乎「道」,這也是 對「君權」的限制。從王安石、程頤到朱熹、陸九淵等都曾公開地強調「道尊於勢」的理念,他們心目中的「君」,通過分析,則可見只是「無爲」的虛君,程頤所 謂「天下治亂系宰相」便說得很露骨,因爲宰相代表了「在位」的「士」。至於「不在位」而在野的「士」則有「議論(批評)政事」的責任,因此宋儒把「士」分 成兩類,前者是「天下之共治者」,後者則是「天下之論治者」。這並不是他們的政治使命感超過了道德使命感,而是政治與道德爲一事的兩面,互相支援,互相加 強。一方面,重建一個合乎「道」的政治秩序,使天下人人都能各得其所,便體現了最高的道德成就。另一方面,道學家特重心性修養,也是以治國精英爲主要物件 (從皇帝到士),而不是一般的「民」。所以朱熹對孝宗專說「正心誠意」四字;個人的道德修養爲政治秩序提供了精神保證。至於王陽明的「覺民行道」,明代的 政治生態當然是一個極重要的背景。明代君主獨攬大權,已不容許士大夫有「共治天下」的幻想。而且明太祖一開始便對士階層歧視,「廷杖」便是專爲淩辱士大夫 而設的獨特制度。洪武十三年(1380)索性廢除了宰相的職位,便使「天下治亂系宰相」失去了制度的根據。所以黃宗羲把這件大事看作「有明一代政治之壞」 的起點。此中曲折已見我的專書與論文,略去不談。這裡我要特別指出的是在王陽明的時代,「民」的一方面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這才使「覺民行道」新心態的 出現成爲可能。所謂「民」的變化,即指十五六世紀「棄儒就賈」大運動的興起。一方面,由於科舉已不能容納越來越多的士人,另一方面又適逢市場經濟的迅速擴 張,許多士人都「下海」,向商業世界求發展,因而造成了一個士商合流的社會。商業財富開拓了新的社會、文化空間,當時書院、印刷、鄉約、慈善事業、宗教活 動等無不有商人參與其間。具有儒生背景的商人階層也積極創建自己的精神領域,他們對於理學表現出深厚的興趣,無論是王陽明的「致良知」或湛若水的「到處體 認天理」都對他們有極大的吸引力。王陽明對這一新的社會變化十分敏感,因此一則說「四民異業而同道」,再則說「雖終日作買賣,不害其成聖成賢」。陽明早年 繼承了宋代道學傳統,仍有「致君行道」的抱負。但王受廷杖、貶龍場之後,此念已斷。他在龍場頓悟所發展出來的「致良知」教,仍然以「治天下」爲最後的歸 宿,不過他對皇帝與朝廷已不抱多大指望,轉而訴諸民間社會。明代已不存在「聖君賢相」的格局,他的眼光從由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轉向由下而上的社會革新運動。 因此「覺民行道」代替了「致君行道」。這個轉變過程很複雜,詳見《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第六章。我對於宋、明理學演變的研究,最初只是想恢復歷史的客觀面 貌,但最後得到的論斷則有「通古今之變」的意外收穫。
◆貪官妻、子送海外 對政權沒信心
問:近年來「中國崛起」似乎是海內外共同的看法,就您的觀察,中國是不是真正的崛起了?中國現狀究竟應該如何看待?
答: 我不認為中國真正崛起了,中共政權也不可能長期維持,政治制度一定要有變革。中國大陸現在貧富懸殊情況嚴重。沿海一帶上億人發財,但大都是跟共產黨官員有 密切關係的人,不是其家人就是親友。所謂「肥水不落外人田」。不知道有多少共產黨貪官,都把太太子女送到海外,也不知有多少錢存到海外,如果他們對自己的 政權有信心,就不會這樣做。
中共維穩費預算近年已超越軍費,兩會期間,北京動員80萬人安保維穩,更有異見人士被多人帶離京城去外地「公費 旅行」。我表妹是「天安門母親」,每次有人看望她或有什麼風吹草動,一家人就被送去福州、杭州等地旅行,一去就一、二十天,陪伴他們的官員也很高興,一起 免費旅遊。這也是維穩費為何支出如此巨大的原因。這樣的社會就維持長久嗎?任何有常識的人,都知道這是不可能長久的。
我相信中共政權將來是有變化的,總有一天維持不下去。但變得如何,尚不敢斷言。
◆集體世襲制度 貪污腐敗根源
問:您說不看好習近平的「中國夢」,您看好習近平的領導能力嗎?習李體制面臨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答: 不少人對習李體制有期待,其實能有什麼期待,只是喊喊口號而已。他們有個調查,訪問了幾千人,結果大約百分之七、八十的人不承認共產黨執政,本來他們以為 大家會熱烈響應,結果恰恰相反,只好不了了之,不敢公開。但仍然有部分資料漏出來,被香港雜誌發表。這反映一個很大問題,大家對共產黨沒有信心。
我 沒有把共產黨看得這麼偉大。因為中國的貪污腐敗現象太普遍了,很多有錢人都跑到外國,都在國外留了後路。有的人雖然留在中國工作,但有護照在手,準備隨時 可以走。這就表示,他們並不認同共產黨,並沒有認為中國有一個夢可以把他們留下來繼續工作。中共目前是集體世襲制度,108個太子黨擁有萬億財富,操控 168家國企。
另一方面,貪官每年逃出來的人數上萬,很多錢都流出來,抓到的雖然不少,但畢竟是小部分,像這樣的人是否認同中國夢?如果喊的口號連自己都不相信,什麼偉大社會?某些海外華人,可能因為民族主義情緒表示認同,但真正瞭解中共現實情況的人不會認同。
問:那麼,您的「中國夢」是什麼?
答: 我沒有「中國夢」,有的只是人類的夢,我的「夢」就是大家平平安安,要做什麼就做什麼,想說什麼就說什麼。這樣的社會才是我的夢。我沒有要中國非常強大, 凌駕於世界,這是中國人的虛榮心作祟。這種民族主義不是好東西,中共現在唯一能利用、有號召力的就是這點。民族主義應該只有被侵略時才應該有,那是為了讓 大家團結起來抵抗外侮。
我們看全世界最提倡民族主義的德國與日本,最後都沒有好下場。可是,現在一些人很受民族主義影響,認為一百多年來被人欺負,希望「站起來」,讓別人看到你就要膜拜,非要到這地步才能滿足,那恐怕會走上自我「毀滅之路」。
◆2.5億農民城鎮化 毛澤東式大躍進
問:您最近提到城鎮化時,認為這是對中國的一大傷害。但這項政策已開始推動,未來會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中國」?
答: 中共提倡的城鎮化,是毛澤東式的大躍進。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社會,把2億5000萬的農民從農村大批地搬遷到城市來,所有土地被中共拿掉,作為賺錢的手 段。現在大陸各地老百姓抗議最多的是拆遷。現在有些地區已開始實行城鎮化,如陝西已開始把農村人搬到城市,但困難非常多,首先是找工作極為困難,他們缺乏 這個基礎,有些人想回去,但原來住的地方沒有了。
中共有兩樣東西最可怕,一是勞教,一是城管。城管到處造成危害,動不動就把人抓起來,送去勞改或勞教,完全靠暴力征服。這樣搞下去,還是會回到秦始皇時代。
問:看到突尼西亞、埃及這樣阿拉伯之春的發展,難道北京當局不擔心?
答:中共對這種運動非常驚心注意,對他的政權是一大威脅。但民主也不是是那麼容易到手的,要取決老百姓的教育與品質,要相對的教育、相當的傳統、相當的尊重反對派,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
我 不認為一下子就可以跳到民主。台灣因為教育好、幾十年的發展,加上日本殖民的關係,還有中國五四以來的科學民主東西,都是可以公開談論的。但是現在共產黨 不准談民主科學,像是最近所謂的「七不講」,還是毛澤東那一套,什麼能講,什麼不能講,或是鄧小平的「四個堅持」,這些都是中共不能動、不能談、不能討論 的。
◆回中國須否定自己 並不心安理得
問:您追求自由、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隨著中國崛起與您的年齡增長,中國想盡辦法勸您回去,雖然您常公開批評中共政策,但大部分作品已在中國出版。許多海外的中國知識人,年老時都有懷鄉與文化歸屬的情懷,您堅持不回中國嗎?
答:第一我不喜歡熱鬧,如果我回去,到處開座談會、演講,我受不了,我現在也不談政治。第二基本上是價值問題,這與六四無關。但要我否定自己所有一切才能回去,並不心安理得,我首先就看不起自己了。
我去不去大陸不重要 ,我不去還好,至少有一個人、而且我相信不止一人,讓人知道有人這麼做,而且這人還活著,不是非回大陸才能吃飯,這還是有意義的。
美國給我最大的自由,生活在一個自由的世界,我不要求別人跟我的看法一樣,別人跟我的看法一樣,我並不特別高興,每個人都應有自己的看法和觀點。
問:若中共放棄一黨專制,您會否考慮回大陸?
答:如果中共放棄一黨專制,我馬上去。
問:六四與文革是中共至今不願面對的難堪,也是不能動搖的統治基礎。但北京當局對這個歷史傷痕始終不願認真面對,您看六四能平反嗎?
答:我認為六四不存在「平反」的問題,只要中共政權存在的一天,他們永遠不會面對六四問題,否則他們就垮台了,而且六四也不應叫「平反」。
「六四」後很多人認為中共很快會垮台,但他的組織太厲害,這裡面也有個氣數問題。
問:您為什麼堅持反共?您對中國前途還樂觀嗎?
答: 我的看法從19歲就形成了,但我不是為了反共而反共。我對中國前途並不悲觀,中國傳統文化不會消失,中國有些東西是生了根的,如祭祖、同鄉會等「老東 西」,還有溫柔敦厚、人情味等,我相信慢慢還會回來。將來我們還要過正常生活,現在鬥爭太多,尤其共產黨一天到晚講階級門爭,但相信共產黨不會永遠存在, 將來總有一天會回歸文明的主流。
◆堅守民主價值 台灣保持軟實力
問:您也提到台灣經驗,是否可輸出到中國大陸,可是近年來台灣因經濟起不來,似乎也沒有自信再常提台灣經驗?
答: 這就是台灣的最大問題,台灣有很大的心理問題,包括國民黨在內,就是畏共怕共,怕得不得了。一是怕他打過來,好像完全不能抵抗,另外一種就是怕台獨,於是 就想用對岸來控制台獨。這種想法是很自私的想法,說老實話,如果繼續這樣子顧忌下去,那最後只有向共黨產投降。如果這樣子,那當初何必跑到台灣來,在南京 簽字投降不就完了嗎。
台灣政府跟共產黨打交道要有原則,民主自由這套價值觀要保持。像是盲人維權人士陳光誠去台灣,不但總統馬英九不敢見, 連文化部長龍應台都不出來,沒有出息到極點了,在我看來是很丟臉,不是什麼光彩的事,好像擔心共產黨會找你麻煩。老實坦白的說,對台灣目前的態度,我很失 望,甚至不客氣的說,我看不起了。我以前對台灣有一種期待,我也知道台灣有不盡如意之處,但對抗共產黨的決心不能沒有。
一個以反共為始的政 府,怎麼能搞到這個地步呢?跟共產黨不是不可以打交道,三通都可以,但在政治上是不能讓步的。我對馬英九不瞭解,在我認識中是個蠻好的一個人。但我想他在 黨內的壓力很大,就像大陸內部一樣,有想法也施展不出來。配合有錢的台商做生意,少數人生活很舒服,就不管下面的人了,現在拚命拿大陸的好處,這樣百姓會 離政府越來越遠。
問:您認為兩岸之間來往,台灣自信何在,有沒有外界普遍認知的「軟實力」?
答:照理說,台灣在文化上有實 力,是絕對高於大陸的,特別是那種有人情味的中華文化。而且台灣現有的社會是大家都接受的,沒有人說要把他推翻來重新再搞一個。這是一個很大的穩定力量, 台灣自己不覺得,你看中共花多大的力氣去維穩,如果每個人都覺得不推翻這個制度否則自己不能活,就是很危險的狀態。
問:各國與中共打交道時,似乎都擔心萬一中共垮台,中國不穩會帶來災難……
答: 對,但大家把維穩不成的後果看的很嚴重,我覺得中共所謂的維穩,目的是在共產黨不要失去政權。可是我覺得中國不會大亂,只是慢慢的不聽中央指揮的情況。現 在,不會讓中共得心應手地使用暴力統治。所以中共所謂的維穩是誇張的,認為沒有中共,中國就會亡了,就會亂了,但沒有這麼可怕。
◆余英時小檔案
余英時,著名歷史學家、漢學家。祖籍安徽潛山,1930年1月22日生於天津。
●學歷:
燕京大學肄業,香港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生,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先後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和當代漢學泰斗楊聯陞。
●經歷:
美國密西根大學助教授、哈佛大學教授、香港新亞學院校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美國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康乃爾大學首任胡適講座訪問教授(1991-1992)。2001年6月自普林斯頓大學教職退休。
●學術榮譽:
台灣中央研究院第10屆院士(1974)
香港中文大學榮譽法學博士(1977)
美國明德學院榮譽文學博士(1984)
香港大學榮譽博士(1992)
美國哲學會院士(2004)
美國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2006)
●主要著作:
出 版書籍30多部,重要著作包括: 「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史學與傳統」、「歷史與思想」、「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方以智晚節考」、 「論戴震與章學誠」、「紅樓夢的兩個世界」、「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兼論他的學術精神與晚年心境」「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朱熹的歷史世 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等。
*****
這本書常提到胡適錢穆......等等人物
不只是"胡適的學位與自由之精神"一節
處處有識見
余先生很用功讀經典 諸如
| ||||||||||||||||||||||||
| ||||||||||||||||||||||||
| ||||||||||||||||||||||||
|
余英時訪談錄北京 (3刷2萬本) /香港 中華書局 2012
我走過的路:余英時訪談錄
作者:陳致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2年
目錄
直入塔中,上尋相輪克魯格獎
政治、黨爭與宋明理學
清代考據學:內在理路與外部歷史條件
最後一位風雅之士:錢鍾書先生
以通馭專,由博返約:錢賓四先生
國學與現代學術
學問與性情,考據與義理
「直入塔中」與「史無定法」
「哲學的突破」與巫的傳統
「內向超越」
胡適的學位與自由之精神
民族主義與共產主義
人文邊緣化與社會擔當
西方漢學與中國學
宗教、哲學、國學與東西方知識系統儒家思想的宗教性與東西方學術分類
國學、「國學者」與《國學季刊》
哲學與思想:東西方知識系統
哲學與抽象的問題
文化熱與政治運動
知識人:專業與業餘
治學門徑與東西方學術哈佛讀書經驗
早歲啟蒙與文史基礎
先立其大,則小者不能奪
洪煨蓮(業)與楊聯陞
俞平伯與錢鍾書
學術與愛國主義
取法乎上
西方漢學與疑古問題
為了文化與社會的重建(劉夢溪訪談)關於錢穆與新儒家
學術不允許有特權
學術紀律不能違反
「天人合一」的局限
怎樣看「文化中國」的「三個意義世界」
學術立足和知識分子的文化承擔
「經世致用」的負面影響
中國學術的道德傳統和知性傳統
中國傳統社會的「公領域」和「私領域」
中國歷史上的商人地位和商人精神
如何看待歷史上的清朝
東西方史學觀念和研究方法的異同
最要不得的是影射史學
文化的問題在社會
社會的問題在民間
後記
余英時教授著作目錄
§內文1
政治、黨爭與宋明理學陳:這兩年我們知道先生的《朱熹的歷史世界》在學界影響很大。我前段時間也在看這本書,您在自序中說到本來是給《朱熹文集》寫序的,結果寫成了一部大著作,這是不是有點兒像梁任公(啟超)寫《清代學術概論》那樣?
余:那倒還不一樣。梁任公寫清代學術,他本來已經很熟悉有清一代的學術變遷,然後用十幾天的時間概括出來,寫成六七萬字的長序,最後獨立成書。他 並沒有再作新的研究。我是本想介紹一下朱熹的思想怎麽産生的背景的,但研究不斷展開後,就發現了許多問題。以至範圍越來越大,最後變成思想史和政治史雙管 齊下,不是專講朱熹一個人了。我特別注意他的歷史背景。隨著問題的不斷複雜化,我又發現了許多前人未注意的新史料。比如說周必大的全集,有二百多卷,裡面 有很多源文件,還有許多奏摺,都沒有人看過。看過的人也對很多前因後果沒太注意,其中可以瞭解到朱熹和當時的政治關係有多深,比如慶元黨禁。我現在把朱熹 在政治上的活動,和他在政治上成爲精神領袖的原原委委全部找出來。這中間他和政治直接牽涉至少有十幾年的時間,的確牽連到權力集團和權力鬥爭,是保守的官 僚集團和一個想有作爲的以理學家爲中心的集團之間的矛盾衝突。後者是有理想有抱負的,希望革除弊政,有徐圖規複的宏偉計劃。這與希望維持現狀的一群人形成 矛盾。這中間還牽涉到祖孫三代皇帝之間的矛盾,所以頭緒繁多到不可想像的程度。我是足足花了兩三年的時間才整理清楚的。
陳:這部書的角度我覺得比較特別。因為以前研究宋代理學,主要是從思想史的內部看,很少從政治生態和政治文化的角度來看。而您在以前研究清代思想,認為清代考据學的興起是由宋明以下理學發展的內在理路(innerlogic)給逼出來的,這與研究朱熹的角度好像正好相反。
余:情況不同,因爲對清代的研究,以前從外部聯繫比較多,如說滿洲人入關以後大家不敢講大問題,有些歷史上的忌諱,逼得大家去做考證工作。這個我 覺得是一個解釋。還有解釋就是清朝人反對理學。這些解釋並不是說不對,而是偏了,把思想內部的問題反而忘了。內部有兩個線索,一個是哲學上的爭論,朱、陸 和朱、王之爭,使理學把考據給逼出來了,非考證不能解決問題。像毛西河(奇齡)是王學的人物,閻百詩(若璩)是尊朱子的。在此之前更早有與王陽明同時的羅 欽順,他在《困知記》裡已經提出取證經書,分判經書裡哪些是假的哪些是真的,這就逼著你回到原典。而王陽明一定要講《古本大學》,這一點就是哲學的爭辯引 向經典的真假遲早的問題,其中是有內在變化的。我研究宋代思想是因爲幾百年來多講內部思想紛爭。傳統的說法集中在「理」與「心」之爭,大陸上說客觀唯心論 主觀唯心論什麽的,都不免只講內部,不問外緣關係。這和清代學術研究的取向相反,也不免陷於一偏。但那時候思想的爭論事實上和黨爭之間有關係,這是沒有人 解釋的。好像北宋王安石的理學、新學到南宋時候已經沒有了。二程與王安石之間的新學之爭,由此發生的政治之爭,似乎到南宋時整個不見了,其實不然。王安石 改變社會並不是爲了只是發明一條道理,或者說與佛教鬥爭。這對兩宋的學術來說是講不清楚的。
陳:所以您講原來的兩宋思想研究有抽離的問題。但後來也有一些爭論,您又寫了文章叫《「抽離」、「回轉」與「內聖外王」》,再申論這個問題。那些文章我也 都看了。您講抽離是說哲學史家在談兩宋理學發生發展的研究中,一是把道學從儒學中抽離出來;二是把道體又從道學中抽離出來。您能不能再解釋一下這個「抽 離」的概念,您是怎麼想的?
余:我所說的「抽離」是就思想史或哲學史上對於宋、明「道學」(或廣義的「理學」)的處理方式而言,其中包括三個層次。第一層是將全部宋、明儒學 從一般政治、社會、文化的歷史脈絡中抽離出來,當做一種純學術思想的動態來觀察。第二層是進一步將「道學」從全部儒學中抽離出來,建構出種種形上系統。第 三層則是將「道體」從道學中抽離出來作精微的分析,以確定其作爲儒家形上實體的性質。這是因爲宋明道學中本有程、朱「性即理」和陸、王「心即理」的兩大對 立系統,一直存在著誰得「道統」真傳的爭論。在現代中國哲學史研究中,這一爭論又以不同的面貌出現。我並不是反對「抽離」,甚至承認以哲學分析而言,「抽 離」是必要的。但是我在《朱熹的歷史世界》一書中,是從歷史觀點處理宋、明道學和政治文化的關係,採取了與「抽離」相異的方式;在歷史分析之外,更注重綜 合。我一向強調「史無定法」,研究方法往往因物件而異。所以我用「抽離」一詞僅僅是關於研究方法的一種描述,並不含絲毫貶斥之意。
陳:您所建構的關於理學的歷史面貌好像和一般的講法很不一樣?
余:這是因爲我的觀察角度不同,提出的問題不同,對於儒學性質的斷定也不相同。宋儒繼承了孟子與韓愈的「道統」說,一開始便提倡回向「二帝」 (堯、舜)「三王」(夏、商、周)之「道」,可見他們最關切的中心問題是重建一個合於「道」的人間秩序,而政治秩序(「治道」)尤其處於關鍵性的地位。所 以在道學興起以後,張載就明白地說「道學」和「政術」是一事的兩面;他的《西銘》則代表了道學家理想中的人間秩序,因此成爲二程教學的經典文本。程頤也說 過「道學輔人主」的話。道學承北宋儒學復興大運動而起,整體的規劃並無改變。這一整體規劃,用孔子的話說,便是怎樣變「天下無道」爲「天下有道」,但北宋 儒者追求「天下有道」的使命感更強烈了,也更具體了。在這一理解下,強調「心、性」修養的「道學」也必須看做是當時儒家整體規劃(the Confucian project)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我們似乎不宜將「心、性之學」單獨挑出來,當做道學的全部。道學在心、性問題上確和佛教有分歧,但北宋儒學復興也不 能簡單地理解爲韓愈辟佛運動的延續和擴大。這是因爲北宋的佛教轉變了,同樣有「入世」的一面。釋氏之徒也希望「天下有道」,並且把這一希望寄託在儒家身 上,從智圓到契嵩無不如此。
陳:所以您對王安石改革和道學之間的關係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您是否可以簡單地概括幾句?
余:王安石改革代表了北宋儒家整體規劃的行動或實踐階段。行動的要求在范仲淹慶歷時期短暫改革中已出現,不過時機仍未成熟。範提倡「士」以「天下 爲己任」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是宋代「士」的精神最扼要的概括,影響極大,見於石介、蘇軾、黃庭堅等人的文集之中。王安石也是在這一 精神之下成長起來的。他的「新學」以儒家經典(特別是《詩》《書》《周禮》)爲根據,加上佛教大乘精神的啓發,已具備道學家以來所發展的「內聖」、「外 王」互相支援的規模。所以在熙甯變法開始時,道學家程顥也參加了王的改革總部—「三司條例司」。儘管道學與「新學」在具體內容上存在著不少差異,但二者的 目的和思想結構是大致相似的,因此才有極短暫的合流。後來雙方鬧翻了,王安石的固執固然要負一部分責任,道學家的意氣過盛也未嘗沒有責任。程頤事後反思, 也承認「吾黨爭之有太過……亦須兩分其罪」。總之,王安石能爭取到神宗的全力支援,使儒家的整體規劃有實現的可能—即所謂「得君行道」—這是當時各派士大 夫都一致擁護的。不但程顥參與新法,劉摯(胡瑗的弟子)和蘇轍最早也同在「三司條例司」工作。朱熹說「新法之行,諸公實共謀之」,這是很中肯的歷史論斷。 王安石與道學的關係在南宋仍然餘波不斷,這可以分兩方面來看。第一,就王氏「新學」而言,通過科舉,它已成爲官學。高宗一朝執政的官僚仍多由「新學」出 身。雖有人提倡「程學」與「王學」相抗,想用二程的道學在科舉考試上取代「王學」,終不能敵。關於這一點,只要讀朱熹的《道命錄》,便可知其大概。道學在 南宋成爲顯學是張栻、朱熹等人出現以後的事。第二,王安石所樹立的「致君行道」的典範對南宋道學家繼續發揮啓示作用。這是因爲南宋道學仍然遵守北宋儒學變 「天下無道」爲「天下有道」的大綱領。朱熹、張栻、呂祖謙、陸九淵等人在政治上都非常積極,希望說服孝宗進行「大更改」。他們並不是「袖手談心性」的人, 而是要改變現狀,建立合乎「道」的新秩序,然後恢復失去的半壁山河。所以他們先後都捲入了權力世界的衝突,終於慶元黨禁。詳情這裡不能談了。
陳:讀您的著作,我有一個很強的印象,就是您特別強調當時士大夫要與君主「共治天下」的觀念。特別講到宋代理學的出現這些問題,讓人覺得與以前的常識不太 一樣。您是不是認爲傳統士大夫的政治使命感超過了他們的道德使命感?在對王陽明研究的時候,您說他有一個很重要的思想就是「覺民行道」。這是宋代士大夫與 君主「共治天下」和「致君行道」不成功之後的邏輯發展,還是主要是明代的政治現實造成的?
余:士大夫與皇帝「共治天下」是宋代儒家政治文化的一個最突出的特色,已預設在「士當以天下爲己任」這句綱領之中。用現代話說,宋代的「士」充分 發展了「政治主體」的意識:他們要直接對政治秩序負起責任。所以「共治天下」的觀念同時必然涵蘊了對於皇權的限制。「天下」不屬於「一人」或「一家」,而 是「天下人之天下」;「士」則自居爲代「天下人」參與政治、議論政治,因爲他們來自民間各階層。「致君行道」首先要求「君」的言行必須合乎「道」,這也是 對「君權」的限制。從王安石、程頤到朱熹、陸九淵等都曾公開地強調「道尊於勢」的理念,他們心目中的「君」,通過分析,則可見只是「無爲」的虛君,程頤所 謂「天下治亂系宰相」便說得很露骨,因爲宰相代表了「在位」的「士」。至於「不在位」而在野的「士」則有「議論(批評)政事」的責任,因此宋儒把「士」分 成兩類,前者是「天下之共治者」,後者則是「天下之論治者」。這並不是他們的政治使命感超過了道德使命感,而是政治與道德爲一事的兩面,互相支援,互相加 強。一方面,重建一個合乎「道」的政治秩序,使天下人人都能各得其所,便體現了最高的道德成就。另一方面,道學家特重心性修養,也是以治國精英爲主要物件 (從皇帝到士),而不是一般的「民」。所以朱熹對孝宗專說「正心誠意」四字;個人的道德修養爲政治秩序提供了精神保證。至於王陽明的「覺民行道」,明代的 政治生態當然是一個極重要的背景。明代君主獨攬大權,已不容許士大夫有「共治天下」的幻想。而且明太祖一開始便對士階層歧視,「廷杖」便是專爲淩辱士大夫 而設的獨特制度。洪武十三年(1380)索性廢除了宰相的職位,便使「天下治亂系宰相」失去了制度的根據。所以黃宗羲把這件大事看作「有明一代政治之壞」 的起點。此中曲折已見我的專書與論文,略去不談。這裡我要特別指出的是在王陽明的時代,「民」的一方面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這才使「覺民行道」新心態的 出現成爲可能。所謂「民」的變化,即指十五六世紀「棄儒就賈」大運動的興起。一方面,由於科舉已不能容納越來越多的士人,另一方面又適逢市場經濟的迅速擴 張,許多士人都「下海」,向商業世界求發展,因而造成了一個士商合流的社會。商業財富開拓了新的社會、文化空間,當時書院、印刷、鄉約、慈善事業、宗教活 動等無不有商人參與其間。具有儒生背景的商人階層也積極創建自己的精神領域,他們對於理學表現出深厚的興趣,無論是王陽明的「致良知」或湛若水的「到處體 認天理」都對他們有極大的吸引力。王陽明對這一新的社會變化十分敏感,因此一則說「四民異業而同道」,再則說「雖終日作買賣,不害其成聖成賢」。陽明早年 繼承了宋代道學傳統,仍有「致君行道」的抱負。但王受廷杖、貶龍場之後,此念已斷。他在龍場頓悟所發展出來的「致良知」教,仍然以「治天下」爲最後的歸 宿,不過他對皇帝與朝廷已不抱多大指望,轉而訴諸民間社會。明代已不存在「聖君賢相」的格局,他的眼光從由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轉向由下而上的社會革新運動。 因此「覺民行道」代替了「致君行道」。這個轉變過程很複雜,詳見《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第六章。我對於宋、明理學演變的研究,最初只是想恢復歷史的客觀面 貌,但最後得到的論斷則有「通古今之變」的意外收穫。
序
我走過的路
我求學所走過的路是很曲折 的。現在讓我從童年的記憶開始,一直講到讀完研究院為止,即從1937年到1962年。這是我的學生時代的全部過程,大致可以分成三個階 段:1937-1946 年,鄉村的生活;1946-1955年,大變動中的流浪;1955-1962年,美國學院中的進修。
我變成了一個鄉下孩子
我是1930年在天津出生的,從出生到1937年冬天,我住過北平、南京、開封、安慶等城市,但是時間都很短,記憶也很零碎。1937年7月7日,抗日 戰爭開始,我的生活忽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一年的初冬,大概是10月左右,我回到了祖先居住的故鄉──安徽潛山縣的官莊鄉。這是我童年記憶的開始,今天 回想起來,好像還是昨天的事一樣。
讓我先介紹一下我的故鄉──潛山縣官莊鄉。這是一個離安慶不遠的鄉村,今天乘公共汽車只用四小時便可 到達,但那時安慶和官莊之間還沒有公路,步行要三天。官莊是在群山環抱之中,既貧窮又閉塞,和外面的現代世界是完全隔絕的。官莊沒有任何現代的設備,如電 燈、自來水、汽車,人們過的仍然是原始的農村生活。對於幼年的我,這個變化太大也太快了,在短短的三天之內,我頓然從一個都市的孩子變成了一個鄉下的孩 子。也就從這時開始,我的記憶變得完整了,清楚了。
鄉居的記憶從第一天起便是愉快的。首先,我回到了大自然的懷抱。我的住屋前面有一道 清溪,那是村民洗衣、洗米、洗菜和汲水的所在,屋後和左右都是山岡,長滿了松和杉,夏天綠蔭密布,日光從樹葉中透射過來,暑氣全消。我從七八歲到十三四歲 時,曾在河邊和山上度過無數的下午和黃昏。有時候躺在濃綠覆罩下的後山草地之上,聽鳥語蟬鳴,渾然忘我,和天地萬物打成了一片。這大概便是古人所說的「天 人合一」的一種境界吧!這可以說是我童年所受的自然教育。
鄉居八九年的另一種教育可以稱之為社會教育。都市生活表面上很熱鬧,到處都是 人潮,然而每個人的感覺其實都是很孤獨的。家庭是唯一的避風港,但每一個家庭又像是一座孤島,即使是左鄰右舍也未必互相往來。現代社會學家形容都市生活是 「孤獨的人群」(lonely crowd),其實古代的都市又何嘗不然?蘇東坡詩「萬人如海一身藏」,正是說在都市的人海之中,每一個人都是孤獨的。但是在鄉村中,人與人之間、家與家 之間都是互相聯繫的,地緣和血緣把一鄉之人都織成了一個大網。幾百年、甚至千年聚居在一村的人群,如果不是同族,也都是親戚,這種關係超越了所謂階級的意 識。我的故鄉官莊,有餘和劉兩個大姓,但兩姓都沒有大地主,佃農如果不是本家,便是親戚,他們有時交不出田租,也只好算了。我從來沒有見過地主兇惡討租或 欺壓佃農的事。我們鄉間的秩序基本上是自治的,很少與政府發生關係。每一族都有族長、長老,他們負責維持本族的族規,偶爾有子弟犯了族規,如賭博、偷竊之 類,族長和長老們便在宗祠中聚會,商議懲罰的辦法,最嚴重的犯規可以打板子。但這樣的情形也不多見,我只記得我們餘姓宗祠中舉行過一次聚會,處罰了一個屢 次犯規的青年子弟。中國傳統社會大體上是靠儒家的規範維繫著的,道德的力量遠在法律之上。道理(或天理)和人情是兩個最重要的標準。這一切,我當時自然是 完全不懂的。但是由於我的故鄉和現代世界是隔絕的,我的八九年鄉居使我相當徹底地生活在中國傳統文化之中,而由生活體驗中得來的直覺瞭解對我以後研究中國 歷史與思想有很大的幫助。現代人類學家強調在地區文化研究上,研究者必須身臨其境(being there)和親自參與(participation),我的鄉居就是一個長期的參與過程。
現在我要談談我在鄉間所受的書本教育。我離 開安慶城時,已開始上小學了。但我的故鄉官莊根本沒有現代式的學校,我的現代教育因此便中斷了。在最初五六年中,我僅斷斷續續上過三四年的私塾;這是純傳 統式的教學,由一位教師帶領著十幾個年歲不同的學生讀書。因為學生的程度不同,所讀的書也不同。年紀大的可以讀《古文觀止》、四書、五經之類,年紀小而剛 剛啟蒙的則讀《三字經》、《百家姓》。我開始是屬於啟蒙的一組,但後來得到老師的許可,也旁聽一些歷史故事的講解,包括《左傳》、《戰國策》等。總之,我 早年的教育只限於中國古書,一切現代課程都沒有接觸過。但真正引起我讀書興趣的不是古文,而是小說。大概在十歲以前,我偶在家中找到了一部殘破的《羅通掃 北》的曆史演義,讀得津津有味,雖然小說中有許多字不認識,但讀下去便慢慢猜出了字的意義。從此發展下去,我讀遍了鄉間能找得到的古典小說,包括《三國演 義》、《水滸傳》、《蕩寇志》(這是反《水滸傳》的小說)、《西遊記》、《封神演義》等。我相信小說對我的幫助比經、史、古文還要大,使我終於能掌握了中 國文字的規則。
我早年學寫作也是從文言開始的,私塾的老師不會寫白話文,也不喜歡白話文。雖然現代提倡文學革命的胡適和陳獨秀都是我的 安徽同鄉,但我們鄉間似乎沒有人重視他們。十一二歲時,私塾的老師有一天忽然教我們寫古典詩,原來那時他正在和一位年輕的寡婦鬧戀愛,浪漫的情懷使他詩興 大發。我至今還記得他寫的兩句詩:「春花似有憐才意,故傍書台綻笑腮。」詩句表面上說的是庭園中的花,真正的意思是指這位少婦偶爾來到私塾門前向他微笑。 我便是這樣學會寫古典詩的。
在我十三四歲時,鄉間私塾的老師已不再教了。我只好隨著年紀大的同學到鄰縣——舒城和桐城去進中學。這些中 學都是戰爭期間臨時創立的,程度很低,我僅僅學會了二十六個英文字母和一點簡單的算術。但桐城是有名的桐城派古文的發源地,那裡流行的仍然是古典詩文。所 以我在這兩年中,對於中國古典的興趣更加深了,至於現代知識則依舊是一片空白。
我走過的路
我求學所走過的路是很曲折 的。現在讓我從童年的記憶開始,一直講到讀完研究院為止,即從1937年到1962年。這是我的學生時代的全部過程,大致可以分成三個階 段:1937-1946 年,鄉村的生活;1946-1955年,大變動中的流浪;1955-1962年,美國學院中的進修。
我變成了一個鄉下孩子
我是1930年在天津出生的,從出生到1937年冬天,我住過北平、南京、開封、安慶等城市,但是時間都很短,記憶也很零碎。1937年7月7日,抗日 戰爭開始,我的生活忽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一年的初冬,大概是10月左右,我回到了祖先居住的故鄉──安徽潛山縣的官莊鄉。這是我童年記憶的開始,今天 回想起來,好像還是昨天的事一樣。
讓我先介紹一下我的故鄉──潛山縣官莊鄉。這是一個離安慶不遠的鄉村,今天乘公共汽車只用四小時便可 到達,但那時安慶和官莊之間還沒有公路,步行要三天。官莊是在群山環抱之中,既貧窮又閉塞,和外面的現代世界是完全隔絕的。官莊沒有任何現代的設備,如電 燈、自來水、汽車,人們過的仍然是原始的農村生活。對於幼年的我,這個變化太大也太快了,在短短的三天之內,我頓然從一個都市的孩子變成了一個鄉下的孩 子。也就從這時開始,我的記憶變得完整了,清楚了。
鄉居的記憶從第一天起便是愉快的。首先,我回到了大自然的懷抱。我的住屋前面有一道 清溪,那是村民洗衣、洗米、洗菜和汲水的所在,屋後和左右都是山岡,長滿了松和杉,夏天綠蔭密布,日光從樹葉中透射過來,暑氣全消。我從七八歲到十三四歲 時,曾在河邊和山上度過無數的下午和黃昏。有時候躺在濃綠覆罩下的後山草地之上,聽鳥語蟬鳴,渾然忘我,和天地萬物打成了一片。這大概便是古人所說的「天 人合一」的一種境界吧!這可以說是我童年所受的自然教育。
鄉居八九年的另一種教育可以稱之為社會教育。都市生活表面上很熱鬧,到處都是 人潮,然而每個人的感覺其實都是很孤獨的。家庭是唯一的避風港,但每一個家庭又像是一座孤島,即使是左鄰右舍也未必互相往來。現代社會學家形容都市生活是 「孤獨的人群」(lonely crowd),其實古代的都市又何嘗不然?蘇東坡詩「萬人如海一身藏」,正是說在都市的人海之中,每一個人都是孤獨的。但是在鄉村中,人與人之間、家與家 之間都是互相聯繫的,地緣和血緣把一鄉之人都織成了一個大網。幾百年、甚至千年聚居在一村的人群,如果不是同族,也都是親戚,這種關係超越了所謂階級的意 識。我的故鄉官莊,有餘和劉兩個大姓,但兩姓都沒有大地主,佃農如果不是本家,便是親戚,他們有時交不出田租,也只好算了。我從來沒有見過地主兇惡討租或 欺壓佃農的事。我們鄉間的秩序基本上是自治的,很少與政府發生關係。每一族都有族長、長老,他們負責維持本族的族規,偶爾有子弟犯了族規,如賭博、偷竊之 類,族長和長老們便在宗祠中聚會,商議懲罰的辦法,最嚴重的犯規可以打板子。但這樣的情形也不多見,我只記得我們餘姓宗祠中舉行過一次聚會,處罰了一個屢 次犯規的青年子弟。中國傳統社會大體上是靠儒家的規範維繫著的,道德的力量遠在法律之上。道理(或天理)和人情是兩個最重要的標準。這一切,我當時自然是 完全不懂的。但是由於我的故鄉和現代世界是隔絕的,我的八九年鄉居使我相當徹底地生活在中國傳統文化之中,而由生活體驗中得來的直覺瞭解對我以後研究中國 歷史與思想有很大的幫助。現代人類學家強調在地區文化研究上,研究者必須身臨其境(being there)和親自參與(participation),我的鄉居就是一個長期的參與過程。
現在我要談談我在鄉間所受的書本教育。我離 開安慶城時,已開始上小學了。但我的故鄉官莊根本沒有現代式的學校,我的現代教育因此便中斷了。在最初五六年中,我僅斷斷續續上過三四年的私塾;這是純傳 統式的教學,由一位教師帶領著十幾個年歲不同的學生讀書。因為學生的程度不同,所讀的書也不同。年紀大的可以讀《古文觀止》、四書、五經之類,年紀小而剛 剛啟蒙的則讀《三字經》、《百家姓》。我開始是屬於啟蒙的一組,但後來得到老師的許可,也旁聽一些歷史故事的講解,包括《左傳》、《戰國策》等。總之,我 早年的教育只限於中國古書,一切現代課程都沒有接觸過。但真正引起我讀書興趣的不是古文,而是小說。大概在十歲以前,我偶在家中找到了一部殘破的《羅通掃 北》的曆史演義,讀得津津有味,雖然小說中有許多字不認識,但讀下去便慢慢猜出了字的意義。從此發展下去,我讀遍了鄉間能找得到的古典小說,包括《三國演 義》、《水滸傳》、《蕩寇志》(這是反《水滸傳》的小說)、《西遊記》、《封神演義》等。我相信小說對我的幫助比經、史、古文還要大,使我終於能掌握了中 國文字的規則。
我早年學寫作也是從文言開始的,私塾的老師不會寫白話文,也不喜歡白話文。雖然現代提倡文學革命的胡適和陳獨秀都是我的 安徽同鄉,但我們鄉間似乎沒有人重視他們。十一二歲時,私塾的老師有一天忽然教我們寫古典詩,原來那時他正在和一位年輕的寡婦鬧戀愛,浪漫的情懷使他詩興 大發。我至今還記得他寫的兩句詩:「春花似有憐才意,故傍書台綻笑腮。」詩句表面上說的是庭園中的花,真正的意思是指這位少婦偶爾來到私塾門前向他微笑。 我便是這樣學會寫古典詩的。
在我十三四歲時,鄉間私塾的老師已不再教了。我只好隨著年紀大的同學到鄰縣——舒城和桐城去進中學。這些中 學都是戰爭期間臨時創立的,程度很低,我僅僅學會了二十六個英文字母和一點簡單的算術。但桐城是有名的桐城派古文的發源地,那裡流行的仍然是古典詩文。所 以我在這兩年中,對於中國古典的興趣更加深了,至於現代知識則依舊是一片空白。
余英時
↧
↧
齊邦媛《巨流河》/《時與潮》雜誌(1959-1967)
《时与潮》半月刊,1938年4月在汉口创刊,主编为齐世英,是一份政治性的综合刊物。1938年第一卷第5期起迁重庆出版,1946年出24卷第6期后曾停刊,1946年12月在上海复刊。1949年2月终刊。共出版33卷。
臺灣大學 慶祝創校83年校慶大會頒授齊邦媛名譽博士學位
11月15日(星期二)上午9時,在校總區綜合體育館舉行創校83年校慶慶祝大會,
李校長以提升格局、邁向頂尖,祝福臺大由追隨者躍昇為領航者;齊邦媛名譽
博士以「尋求永恆價值」為目標,慶祝臺大生日快樂。慶祝大會同時表揚6位傑
出校友。慶典除邀請本校歷任校長、各地校友及國內外各界貴賓與會,典禮後
隨即於國際會議廳舉行校慶茶會及晚間舉辦的1971年及1976年校友重聚會餐會
等多項慶祝活動。
今年獲頒名譽博士學位的學者是齊邦媛女士。齊女士對國內國語文與英語教學
之開創革新,引領一個世代的心智往活潑化、自由化發展,潛移默化之功甚
偉。尤其對臺灣文學的整理、研究與介紹,成功把臺灣文學推介至國際舞臺,
也開啟了國際對臺灣文學研究的興趣,終於蔚成一受重視之獨立學術領域,志
行崇高,影響深遠。其學問事功,足以表率群倫,為「敦品勵學,愛國愛人」
之最佳典範,本校授予博士學位,即在表彰渠卓越的成就與貢獻。
***
我白髮蒼蒼站在這裡接受一生最高榮譽,百感交集。回想1947年第一次看到臺
大校門跟椰林大道,當時我黑髮披肩,剛從大學畢業,不知道天高地厚,孤獨
寂寞,還是勇敢地來到臺灣。手裡拿著「毛筆寫在宣紙上的臺大助教臨時證
書」,以為此後自己就走上了學術之路,但這條路卻非常地漫長、崎嶇。
在臺64年,我在臺大擁有從基層做到退休的完整資歷。期間看到臺灣最大的改
變,是從一個文化到另一個文化到更多的文化。我所有的課都在教中西交流,
包括:英國文學史、高級英文、研究所英文、翻譯…。我覺得很幸運,在最好
的時候看見了臺灣的生機,看見了臺灣的可能,也幫忙創造了臺灣文學盛世,
從1970年到1999年。
1972年臺大中文系跟外文系合辦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協會進軍國際。我代表參加
所有國際會議為臺灣發言。1949年政治大斷裂後,臺灣保持中國純正的文化,
我們有最好的學術環境、著作,所以我和外文系、中文系許多同事共創比較文
學會向國外發聲。從1960一直到1985年臺灣文學是國外漢學研究唯一的教材;
我所編的《臺灣中國文學選集》是唯一的教材。
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做?我兩次參加Fulbright exchange program,我們能夠教
別人聽到,一定要有實際的東西。至今我仍鼓勵自己要有拿得出去的東西。所
以我們有《筆會季刊》,至今已發行40年未曾拖期。因為我們相信,文化在文
學上凝聚所有的心力應該持久不變。
1949年我為了婚姻第一次離開臺大,走入一個女子一生最困難的路:家庭與事
業兼顧的路。其中的困難,如果你未曾經歷很難瞭解,我的兒女也很難原諒。
剛才校長說我是齊邦媛女士。「女士」二字,可不容易,我寧可作老師、教
授,但女士就有很多複雜的身分、複雜的角色、複雜的快樂、複雜的痛苦。
1949年傅斯年校長在臺大校慶說:「我們現在要辦一所真正的大學。為什麼要
辦真正的大學?因為我們現在臺灣,退此一步便無死所。我們要貢獻這所大學
宇宙精神。」政治大斷裂時,幾百萬人回不了家,幾千萬人在尋求未來的目
標,這個宇宙精神是鼓勵也是自信,我們希望有這個能力。許多人渡海而來,
將1949以前所珍貴的、所學習的帶來,所以臺大自從1949以後日漸壯大,成就
今天的臺大。
我到臺大的時候只有1000多個學生。外文系僅有20個學生左右。我是唯一從大
陸受聘來臺的一個小小助教,心裡想的「宇宙精神」代表了很多的希望、很多
努力的目標,所以自從有機會以來,我就不斷地投入教育。希望把一代又一代
的年輕人帶出來看到我們必須要做的事。
我們能做什麼?我們能夠把臺 灣做成什麼樣子?這麼多年我們看到,今天臺灣
在世界上,以這麼小的地位,創造出的文化地位,實在不是我們自己在這裡誇
口。
在這個瞬息萬變的社會,我們還有不變的東西。今天,似乎所有的人都在談論
科技的進步,都在談論那些優秀的人的成就。那些優秀的人都說:「我要改變
世界。」可是我們自從來到臺灣以後一直在改變世界,一直在改變臺灣,一直
使得臺灣進步;我們一直在做,沒有一天不做。我和那些朋友推動的,都是奠
定臺灣文化真正的基礎。
最近大家都在談論賈伯斯,而我因為想要真正了解一個時代,所以也看了他的
傳記,我看的非常有興趣。他跟他同時代的人一樣有夢想,可是他的夢想是從
中間出來的,而我們當年的夢想是從基層出來的,兩者相當的不同。他們追求
的是超越別人,超越一切的成功,這種超越的力量是一種熱狂,也是一種快
樂,能得到如此的成功是非常高的境界,但最後他也會覺得:這樣大的星空,
這樣大的宇宙,要如何才能夠得到最後的勝利?當他知道自己生病不久人世
時,堅持找可靠的人寫傳記。作者問他:「你不是一個很重視隱私的人嗎?為
什麼要把你的傳記寫得如此詳細?我會寫下你的許多優點和缺點,難道你不在
乎嗎?」他說:「這就是我,我奮鬥的經過、我的夢想,我希望我的孩子將來
能夠知道我為什麼常常不在家?我希望他們知道我做了什麼,希望他們了解我
是怎樣的人。」看到這裡,我已經把書看完了。
我想,原來他那輝煌的,21世紀的成功,跟20世紀我的父親、我的祖父那一代
的成功其實完全一樣。他想要告訴後代:我們做什麼,我們怎樣做;我們努力
地做,我們用所能做的方式做了。我從他的傳記裡看到世世代代開創世界,做
一個文化的成就時,就像賈伯斯所做的,將人文與科學結合,缺一不可;因此
你不可能再回到原始洪荒的世界。
我直到跟朋友討論時才了解,人生瞬息萬變只是表面,瞬息萬變之後得到的是
不變的東西,是永恆的價值。人間的情、愛、了解,實在是永遠、永恆不變的
關懷。我真的很感謝臺灣大學對我有整體的評估,知道我所做的在這個校園,
在牆裡牆外,都是為了尋求永恆的價值。我這一生用種種方式推行文學教育,
一直用文學教育和永恆的價值跟青年朋友、後代苦口婆心地說:「我們必須這
樣活下去,才有未來;無論臺灣多小,世界多大,我們有真正的宇宙精神。」
這個宇宙精神並不是空言。對於年輕的學生跟朋友,我希望你們在進步的科學
設備之下,能有時抬起頭,不要只專注在機器上;看看比你更小的學生、朋
友,跟他們講講文學之美。你們一定要看看大的、厚的、專注的、有焦點的
書;才夠思考大的、厚的、專注的、有焦點的問題;才能對世界做出大的、厚
重的、有貢獻的事情,這也是我對還在教書的朋友最大的期待。
我很感謝當年臺大給我機會,讓我們(外文系)跟中文系可以合辦文學教育,用
中文推銷西方文化,用西方文學來推銷臺灣的文化。我們變成了一個被人看
見、被人了解的地方。希望年輕的老師們、未來的老師們能夠多多了解:無論
機器有多進步、能做多流暢的溝通、擁有多新穎的形貌,人性的溝通還是最重
要的。現在人都活得太久了,賈伯斯56歲去世,大家都很驚訝:怎麼他會在56
歲就死去了?他還有30年的時間啊!但是當人能活得長久,我們要怎樣活著,
卻是一門大學問。我們應該要好好地利用這些時間,我也希望未來的人性能和
從前一樣,追尋更好的世界。
我一生所留戀的美好的事情已經過去了,譬如文學題材裡的等待。我們那時迷
路的感覺、悲傷的感覺已經不在,連郵票都已經沒有人用了,將來想看到郵票
可能只在郵票百年大展能看見。這些美好的東西,在形式上或抽象的看法漸漸
都要過去,可是一環接著一環,這世界有不同時代的美好串成整個人類永恆的
價值;瞬息萬變是必然,但永恆的價值也是必然。
感謝謝立沛老師贈書2010/2
忘不了的人和事
才是真生命
--- 齊邦媛《巨流河》p. 433
![巨流河]()
www.books.com.tw/activity/2009/07/htm/page06_8.html - 頁庫存檔 -
***
此書精彩 譬如說 許多人物軼事 包括胡適之先生與作者談文學之深度和品味等
有一些 缺點
最大的是無索引
少數人物上的資訊小錯或小誤 例如
Hippolyte-Adolphe Taine
(born April 21, 1828, Vouziers, Ardennes, France — died March 5, 1893, Paris) French thinker,非德國人( p.450)
譬如說 Hayek 來台時還沒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p.358 ) CZ 列車 California Zephyr
![]()
7.3創辦中興大學外文系
我有一個夢
第一次交換教員進修回來,回到台中一中教書滿兩年後,一九五八年秋天,轉任台中的台灣省立農學院教大一英文。事實是學術研究生涯的開始。
台灣省立農學院在一九六一年改為省立中興大學,而後才又改為國立中興大學。英文是共同科,除此之外還有國文、歷史、三民主義、體育等。在共同科的教員休息 室聽多了「雜拌」的言談,下定決心一定要推動中興大學外文系,可以有切磋琢磨的文學同道。
一九六○年左右,學校開設兩班大二英文選課,請我教一班,教材自定。
這一年正好是約翰‧甘迺迪當選美國總統,他的就職演說以及一九六二年去世的胡適先生最後的演講稿,加上美國黑人民權領袖金恩博士一九六三年的著名演說「I have a dream」,我在台中美國新聞處取得這三篇稿子,我大約讀遍了那裡的文學書。當時台中圖書館、學校圖書館的英文資料少得可憐。
我拿這些篇章再加上讀書時讀過的一些好散文,還有狄金蓀(Emily Dickinson)、惠特曼(Walt Whitman)與佛洛斯特(Robert Frost)的詩作教材,並且比較中西文化的差異。學生對我講的都覺得很新鮮。尤其在甘迺迪總統和金恩博士被暗殺後的國際氛圍中,大學畢業去美國的留學潮已經開始,有關美國文化的,較有深度的新文章非常受歡迎。
這門課是選修的,約有七、八十個學生選,但上課時擠了一百多人。教室大約只有七、八十個位置,學生因為座位不夠,就把隔壁教室的椅子搬來坐,常起糾紛。
那時的校長是林致平和後來的湯惠蓀,劉道元校長時期我開始向校長要求設立外文系。他們也常常在重要場合請我出席。
一九六五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海耶克博士(Prof. Friedrich A. Hayek)到台中各校演講,我受命擔任現場翻譯。他對我說:「待會兒我講一段,你就幫我翻譯一段。」我心裡忐忑不安,因為我大一雖然修過經濟學概論,但並不懂,所以很緊張。到了會場,看到台北還有好多人陪他來,包括台大名教授施建生、華嚴等,整個會場都坐滿了人,我有些心慌。
海耶克先生沒有給我演講稿,而且他講的英文帶有德國腔,不容易聽懂;他往往一說就是五、六分鐘才讓我翻譯,這真是很大的挑戰。還好,他偶爾會在黑板上寫幾個字。那是我第一次聽到「Closed Society」跟「Open Society」這兩個詞,我想「Closed」是封閉,「Open」是開放,所以就翻成「封閉的社會」與「開放的社會」,應該不會錯吧。後來大家果然繼續這麼用,這給我很大的鼓勵。
台大法學院長施建生後來對我說:「我帶他們走了這麼一大圈,你是當中翻譯得最好的。」而且也對別人這麼說。
後來,很多重要人士來台中,我曾為浸信會主教翻譯,這種翻譯我還能勝任。六○年代左右,蔣總統邀請《讀者文摘》總編輯來台,因為他曾寫過一篇關於台灣是個 新寶島的文章,到台中來也曾請我幫他翻譯,這些經驗給我很大的鼓勵。當然,緊張的心情是免不了的,每次站在台上,我都像是戰士披著盔甲上戰場,總想怎麼樣 能生還才好。文學作品的翻譯必須到達精深的層次,日後我推動中書外譯的一些計畫,因為那是更高的挑戰。
(詳見第七章)
文學播種——國文教科書改革
我到國立編譯館之前,對自己的工作已做了一些研 究。台中的教育界朋友很多,那才是真正的「民間」。國民中學的各科編審委員會全是新設,可聘請切合時代精神的專家學者,而不似過去只以聲望地位作考慮。在 這方面,王館長和我在大學校園多年,應已有足夠的認識和判斷能力。我的工作之一就是掌理人文社會各科的編寫計畫,既被迫兼掌教科書組,又須負責計畫的執 行,包括各科編審委員會的組成、編書內容的審訂。在一九七二年,那並不只是「學術判斷」的工作,也是「政治判斷」的工作。
我第一件事是仔細研究,分析暫定本國文的內容編排。每學期一冊,各選二十篇課文。翻開暫定本第一冊篇目表,前面兩課是蔣中正〈國民中學聯合開學典禮訓詞〉 和孫文〈立志做大事〉,接續就是〈孔子與弟子言志〉、〈孔子與教師節〉、〈民元的雙十節〉、〈辛亥武昌起義的軼聞〉、〈示荷蘭守將書〉、〈慶祝台灣光復 節〉、〈國父的幼年時代〉、〈革命運動之開始〉。政治色彩之濃厚令我幾乎喘不過氣來,更何況十二、三歲的初一學生!
是什麼樣的一群「學者」,用什麼樣「政治正確」的心理編出這樣的國文教科書?這時我明白,我所面臨的革新挑戰是多麼強烈巨大了。但是走到這一步,已無路可退,只有向前迎戰。
第一件事是組成一個全新的編審委員會,最重要的是聘請一位資望深、有骨氣、有擔當的學者擔任主任委員。不僅要導正教科書的應有水準,還需擋得住舊勢力可能 的種種攻擊,編出符合義務教育理想的國文。我心目中的第一人選是台大中文系主任屈萬里先生。
屈先生字翼鵬,是國際知名的漢學家,從普林斯頓大學講學返台,擔任中央圖書館長,其後轉任台大中文系系主任,不久又兼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而後膺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學術聲望很高。
柯慶明對我在國立編譯館要做的事很有興趣,也深深了解其重要性,所以他以接續編輯《現代文學》的心情,提供許多幫助,助我建立了第一批台灣文學作品的書 單,開始公正而不遺漏的選文作業。譬如他最早告訴我,司馬中原早期作品如《黎明列車》等,由高雄大業出版社印行,已近絕版,我寫信去才買到他們尚稱齊全的 存書。因他的協助,我們建立與作者的聯絡與認識,日後選稿能站住國家編書的立場。對於國民中學國文教科書的改進和定編,他有更真摯的關懷。他深感民間普及 教育的重要,願意幫我說動屈先生領導這艱巨的工作。終於有一天,屈先生同意我到中文系辦公室一談。
在那次相當長的面談中,我詳談舊版的缺點和民間輿論的批評與期望,這原也是王館長和我在台中淳樸校園未曾深入了解的。現在,不僅是基於職責而編書,更是為 國家文化的前途,為陶冶年輕世代的性靈,必須用超越政治的態度。當然,這樣一套新書是與舊制為敵的,雖無關學術立場,但將來不免會為主持者引來一些政治立 場的敵人。但是 不論付出什麼代價,為了未來國民教育每年每冊三十萬本的教科書,是義不容辭的。我清晰地記得,屈先生坐在那間陳舊的辦公室,深深地吸他的煙斗,然後嘆了口 氣,說:「好罷!我答應你!這下子我也等於跳進了苦海,上了賊船。」他語氣中有一種不得不然的複雜情緒(resignation)。我覺得其中有種一諾不 悔的豪情和悲壯,從潔淨超然的學術天地,走進政治、文化立場的是非之地,應是也經過許多內心交戰的思量決定。
屈先生主持「國民中學國文教科用書編審委員會」,由台大、師大、政大各三至五位教授和幾位中學老師組成。主編執筆者是台大中文系張亨教授、師大應裕康教 授、政大戴璉璋教授,他們都是中文系普受肯定四十歲左右的年輕學者。
為了一年後即須使用正式部編本教科書,第一、二冊必須編出定稿,在次年八月前出版。國立編譯館所有會議室,日日排滿會程,有些委員會晚上也開會。國文科委 員開會經常延長至黃昏後,當時還沒有便當簡餐,編譯館就請屈先生、執編小組和編審委員到隔壁僑光堂吃很晚的晚飯。屈先生有時主動邀往會賓樓,杯酒在手,長 者妙語如珠。
一九七三年以後,數代的國民中學學生至少是讀了真正的國文教科書,而不是政治的宣傳品。想來屈先生未必悔此一諾,他當年付出的心力和時間是值得的。可惜屈先生逝世後的追思文章,甚少言及他在這方面的貢獻。
三位主編初擬國文課本第一、二冊目錄之後,我們的編審委員會才算真正開始運作,屈先生掌舵的船才開始它的苦海之旅。在那政治氛圍仍然幽暗的海上,他不禁要 掌穩方向,注意礁岩,還要顧及全船的平穩航行。開會第一件事是由主編就所選二十課的文體比例及各課內容、教育價值加以說明,然後逐課投票,未過半數者,討 論後再投票。如我們預料,這個過程是對屈先生最大的挑戰。有兩位委員嚴詞責問:為什麼原來課本中培育學生國家民族思想的十課課文全不見了,現擬的目錄中只 有兩篇,由二分之一變成十分之一,其他的都是些趣味多於教誨的文章。楊喚的新詩〈夜〉怎麼能和古典詩並列?《西遊記》〈美猴王〉、沈復〈兒時記趣〉和翻譯 的〈火箭發射記〉都沒有教學生敦品勵學……。解釋再解釋,投票再投票,冗長的討論,爭辯,說服,幾乎每次都令人精疲力竭。
舊版大多選取含有政治歷史節慶、民族英雄色彩的文章,即使選了一些白話文,也都偏屬議論文;屬文學性質者,篇數略少。新版只保留孫文〈立志做大事〉,並將 舊版第二冊蔣中正〈我們的校訓〉挪移到第一課,其餘古典現代小說、散文、詩歌,全是新增;此外,更選入翻譯文章〈人類的祖先〉和〈火箭發射記〉,讓國中生 有人類文化史觀與尖端科技的世界觀。
想不到我當初萬般委屈接下兼任教科書組,被屈先生稱為苦海「賊船」的挑戰,是我付出最多心力感情的工作,也是我在國立編譯館最有意義的工作成果之一。為達 到改編的理想,恢復國文課本應有的尊嚴,讓每一個正在成長學生的心靈得到陶冶與啟發,在那個年代,我的工作是沉重的,不僅要步步穩妥,還需要各階層的支 持。
在政治高階層,我們必須尋求一些保護。我曾以晚輩的身份,拿著新舊國文課本目錄拜望早年教育部長陳立夫、黃季陸;也以學生身份去看望武漢大學第一任校長王 世杰,希望他們在輿論風暴之前,能對我們的改革具有同理心,因為他們自己是文人從政,對文學教育和學術尊嚴也有理想。我尤其記得黃季陸先生,對我侃侃而談 民國以來,國民教育的種種利弊得失,他很贊成政治退出語文教材,一談竟是兩小時,還說歡迎我以後再去談談我們編寫的進展。可惜不久他即病逝,我未能再聆聽 教益。老國民黨有不少被歷史定位為政治人物的文人,很希望在穩定社會中以書生報國之心從政,卻生不逢辰,生在政爭的中國。
在編審委員會中,我最需要資深委員的支持,當時代表編譯館最資深的編審者是洪為溥先生。我初到館時,他對這個外文系的女子敢來作人文社會組主任頗感懷疑, 甚至反感。經過幾次懇談後,對我漸漸轉為支持。討論第三冊篇目時,我大力推薦黃春明〈魚〉。沒想到首次投票,未能通過,我和屈先生商量:「下次開會,能不 能讓這個案子復活,再討論一次?」屈先生說:「還討論什麼呢?投票也通不過。」我說:「我為它跑票。」我第一個去跑的就是反對最激烈的洪為溥先生。他的辦 公室和我的相隔一間,窗外都對著舟山路台大校牆外一棵高大豐茂的台灣欒樹,太陽照在它黃花落後初結的一簇簇粉紅色果子上,美麗中充滿自信。他說:「這篇文 章講小孩子騎腳踏車,在山路上將買給爺爺的魚掉了,回到家反反覆覆不斷地喊,我真的買魚回來了!相當無聊,怎麼講呢?」
我想起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一本語文教學書,讀到一位中學老師寫他教初中課本選了莎士比亞《馬克白》(Shakespeare's Macbeth)一段:
這位中學老師問學生:「為什麼連用三次『明天』?」學生的回答形形色色,但是多半抓住一點:活得很長,會有許多明天。老師聽完後說:「你們想著,那麼多明 天可以去騎馬、打獵、釣魚,馬克白因為今天和昨天做了太多惡事,所以他的許多『明天』是漫長難捱。」用一個簡單的字,一再重複,它所創造的意境,老師大有 可講之處。就像〈魚〉,小孩不斷重複「我真的買魚回來了」,也有令人玩味低迴之處。
下一次開會時,屈先生果然將上次未通過的幾課提出再討論,洪先生突然站起來說:「我們的學生百分之八十在鄉鎮,對〈魚〉中祖父和孫子之間的感情應是很熟 悉,這樣樸實的情景會讓他們感到親切。」第二次投票通過,我記得自己感動得熱淚盈眶……。
譯介台灣文學的橋樑——中華民國筆會
我既是作學術交流的人,必須先站穩台灣文學的立足點。自一九八五年柏林經驗之後,我得以從美國以外的大框架歐洲,思索台灣文學已有的格局和未來的發展。對 我啟發最深的是一九八六年在德國漢堡舉行的筆會年會上,西德著名作家葛拉斯(Gunter Grass)對支持俄共威權的東德作家,咆哮責問:「文學良心何在」?一九九二年在巴塞隆那的筆會年會,幾乎是該城向西班牙爭取獨立的一個論壇,我們收到的文件一半是使用該城的加泰隆尼亞語(Catalan),以示他們古老語文的存在意義。而最強烈的啟發則是一九九四年,在捷克布拉格的筆會年會,主題是「國家、種族、宗教、社會的容忍與文學」,由捷克作家總統哈維爾(Havel)主持,其中有一場座談會題目是「小語言與偉大文學(Small Languages, Great Literature),小語言寫作者的難題」。另一場是「我們自知幾許?」(How Much do We Know about Ourselves?)第 一次看到語言有大小之分,第一次聽到蘇俄解體後,五十多位作家各自回到獨立的國家,不用俄語陳述,而是重用小語言的母語創作,陷入另一種困境。我曾根據他 們的話寫了一篇〈我的聲音只有寒風聽見〉,文中並未明言我的憂慮,世界的漢學界已將注意轉移至中國大陸,台灣重要的作家多已停筆,本土化的聲浪日益高漲, 當年大家用中文寫作的熱情不再,會不會有一天,我們也面臨小語言,小文學的處境?
從此,我對台灣文學的關懷,就不再只是單純地鼓勵與評介,而是它在未來的發展和定位。一九九二年正式接任中華民國筆會英文季刊總編輯的工作,將近十年,得 以深耕台灣土地的文學創作,對這個大問題有切身的領悟。
這本英文季刊自一九七二年創辦以來,我一直是個實質的顧問。主編選集後,我對台灣文學的發展,以不遺漏的閱讀,保持真正的了解。因為「台大哲學系事件」 (1973年)而離開的趙天儀被教育部安排到國立編譯館任人文組編審,以及接辦《現代文學》的柯慶明,都助我深入認識本土作家。當時台灣詩社如雨後春筍, 我一直是訂戶讀者,日後主編筆會英文季刊選稿來源仍是維持公平的態度,尤其沒有「政治正確」的立場。
在自由世界,文學作者原不必有會,寫作是個單打獨鬥的行業,文壇原本無壇,只是有時文人相聚也有可談之事。一九二一年由英國和一些歐洲作家在倫敦成立了國際筆會(The International PEN),PEN是Poet, Essayist, Novelist的縮寫。一九二四年,中華民國筆會成立於上海加入總會,發起人有林語堂、胡適、徐志摩等人,第一任會長是蔡元培,開始做各種文化交流,作品互譯,作家互訪等拓荒工作。我自幼逢書便讀,讀後常有難忘之事,他們邀請印度詩人泰戈爾訪華的事,啟發我多年的想像。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筆會會員國參加戰爭,立場對立,文學交流停止,直到一九四六年,在中立的瑞典重開。中華民國筆會一九五三年在台灣復會,第一、二屆的會 長是張道藩和羅家倫。一九五九年首次回歸國際總會,參加每年一度的年會。一九七○年林語堂當選會長,在台北召開第三屆亞洲作家大會,邀請川端康成、張大千 等及韓國、泰國、菲律賓等國重要作家前來,台灣作家將近百人參加盛會。王藍、彭歌(姚朋)和殷張蘭熙三人負責辦事,在剛剛落成的圓山飯店將大會辦得有聲有 色,大大地提高了台灣的聲譽。林語堂說,台灣應該有一份發表作品的英文刊物,讓我們在東方與西方之間搭一座橋。
一九七二年秋天,中華民國筆會季刊(The Chinese PEN)創 刊號出版,由母語是英文的殷張蘭熙擔任總編輯,王藍和彭歌是編輯顧問。從創刊到一九九二年,殷張蘭熙獨撐二十年,我繼編九年,彭鏡禧、張惠娟、高天恩和現 任的梁欣榮都是我台大外文系的年輕同事,以拔刀相助之情前來兼任總編輯,助理編輯兼秘書只有一人,前十五年是劉克端女士,近十五年是項人慧,大出版社很難 想像那種「孤寂」。發書時增一工讀學生。三十六年來,春、夏、秋、冬四季運行,和大地運行一樣,中華民國筆會季刊至今發行一百四十四期,從無一季脫期,是 國際筆會最穩定最持久的刊物。在一百多個會員國的文學界,台灣是個有信譽的地方。
殷張蘭熙是最早作台灣文學英譯的人。一九六一年美國新聞處資助Heritage Press出版社英譯小說和新詩,殷張蘭熙就是《新聲》(New Voices)的主編,選入者白先勇、敻虹、王文興、陳若曦、葉珊(後改筆名為楊牧)等作品。因此執編筆會季刊之前,殷張蘭熙已有數年孤軍奮戰的經驗了。
殷張蘭熙(Nancy Ing)的名字和季刊幾乎是不可分的,她選稿,翻譯每期的詩,尋找高水準譯者,讀譯稿、校對、發排。創刊後三年開始用台灣藝術作品作封面,刊內介紹,她又增加了另一個領域的挑戰,在這方面協助最多的是王藍,我接編後是林文月、丁貞婉等好友。
殷張蘭熙金髮碧眼的美麗母親,一九一七年嫁給中國同學張承槱先生(來台後曾任審計長),由美國維吉尼亞州到中國湖北縣城成家,生兒育女。十多年後蘭熙長 大,畢業於成都華西大學外文系,一九四九年隨夫婿殷之浩先生來台灣,創立大陸工程公司,因為出國開會而冠夫姓,文壇好友都只稱Nancy。她愛文學,有時 也寫詩,一九七一年曾出版 One Leaf Falls 詩集。
一九七二年我從台中搬到台北,恰巧與蘭熙住在鄰巷,街頭蹓狗又常遇到。各自主編筆會季刊和《中國現代文學選集》,總有說不完的話題。最基本的話題是值得譯 介的書稿,英譯的人才,字字句句斟酌譯文,整體的安排,呈現的效果,國際讀者的反應等等,好似長河流水,永不厭倦。
蘭熙是個坦誠溫暖的人,忙碌中熱情洋溢。每年在各地召開的年會前,催集論文,安排演講和討論議題,準備禮物,到會場結交天下士,握住那麼多伸出的友誼之 手。大陸的「中國筆會」文革後參加總會,多次在會場排擠我們,蘭熙收起她自然溫婉的笑容,登台發言憤慨迎擊,保衛自由民主的台灣代表權。直到一九八九年天 安門事件後,他們不再出席年會。在今日政局情勢下,會籍立場仍會被提出,但是蘭熙與當年代表所建立的國際友誼,以及我們的季刊三十多年穩定的出刊,豐富的 專業形象,已讓中華民國筆會立於不易撼動的地位。中美斷交後,蘭熙受邀在美國十家地方電視台上「談台灣」(“Talk about Taiwan”)節 目,侃侃而談,以條理的分析,清晰的言辭,呈現台灣在文化、經濟、社會各方面的進步,英文的筆會季刊更幫助增加了解。那些年,在西方世界為台灣發聲的事, 蘭熙做了很多,但是在台灣反而少有人知。最可貴的是,這些奉獻和她主編筆會季刊二十年的投入都受到丈夫殷之浩先生全心全力的支持。季刊收入僅有外交部和新 聞局所付國際贈送的那數百冊書款,國內在誠品等地出售則不及百冊,主要的支出如稿費、印刷、發行及人事費用,皆由殷先生資助。筆會會址原也設在大陸公司所 在地,殷先生去世後,一九九六年開始租屋在溫州街,即將面臨斷炊時,殷氏「浩然基金會」開始資助,得以編印發行至今。
(詳見第十章)
| 篇名: | 齊世英與逆勢而為的《時與潮》雜誌(1959-1967) |
| 作者: | 邱家宜 |
| 中文摘要: | 本文專注於齊世英先生在1959年到1967年間在台灣所創辦的《時與潮》雜誌內容,以及創辦者齊世英先生在台灣的政治活動,並指出其表裡呼應的關係。一 方面有系統地整理《時與潮》雜誌在各個階段言論的主要重點,對照於當時台灣的政治社會狀況,凸顯《時與潮》鼓吹民主法治、言論自由的一貫調性;一方面則從 其生命史追溯,探討曾是國民黨中間幹部的齊世英,為什麼在當時會投入與國民黨對抗的組黨運動,並且成為後來的黨外運動最早期的一批外省籍支持者。做為報人 的齊世英,與其所辦的《時與潮》雜誌的內容,與創辦《自由中國》的雷震及這兩個刊物的讀者,共享一特定的「感知結構」,雖一度沉潛,卻即將在二十年後再度 浮現成為主流。 |
| 中文關鍵詞: | 時與潮、齊世英、感知結構、新黨、雷震案、黨外 |
| 發表日期: | 2013/7/14 |
| 授權狀況: | 已授權 |
| 全文下載: | 3-1D_邱家宜_齊世英與逆勢而為的《時與潮》雜誌(1959-1967).pdf |
臺灣大學 慶祝創校83年校慶大會頒授齊邦媛名譽博士學位
11月15日(星期二)上午9時,在校總區綜合體育館舉行創校83年校慶慶祝大會,
李校長以提升格局、邁向頂尖,祝福臺大由追隨者躍昇為領航者;齊邦媛名譽
博士以「尋求永恆價值」為目標,慶祝臺大生日快樂。慶祝大會同時表揚6位傑
出校友。慶典除邀請本校歷任校長、各地校友及國內外各界貴賓與會,典禮後
隨即於國際會議廳舉行校慶茶會及晚間舉辦的1971年及1976年校友重聚會餐會
等多項慶祝活動。
今年獲頒名譽博士學位的學者是齊邦媛女士。齊女士對國內國語文與英語教學
之開創革新,引領一個世代的心智往活潑化、自由化發展,潛移默化之功甚
偉。尤其對臺灣文學的整理、研究與介紹,成功把臺灣文學推介至國際舞臺,
也開啟了國際對臺灣文學研究的興趣,終於蔚成一受重視之獨立學術領域,志
行崇高,影響深遠。其學問事功,足以表率群倫,為「敦品勵學,愛國愛人」
之最佳典範,本校授予博士學位,即在表彰渠卓越的成就與貢獻。
***
諸位貴賓,感謝你們來看我回到一生工作、居住的臺灣大學拿最高榮譽。今天名譽博士齊邦媛述懷:尋求永恆價值
我白髮蒼蒼站在這裡接受一生最高榮譽,百感交集。回想1947年第一次看到臺
大校門跟椰林大道,當時我黑髮披肩,剛從大學畢業,不知道天高地厚,孤獨
寂寞,還是勇敢地來到臺灣。手裡拿著「毛筆寫在宣紙上的臺大助教臨時證
書」,以為此後自己就走上了學術之路,但這條路卻非常地漫長、崎嶇。
在臺64年,我在臺大擁有從基層做到退休的完整資歷。期間看到臺灣最大的改
變,是從一個文化到另一個文化到更多的文化。我所有的課都在教中西交流,
包括:英國文學史、高級英文、研究所英文、翻譯…。我覺得很幸運,在最好
的時候看見了臺灣的生機,看見了臺灣的可能,也幫忙創造了臺灣文學盛世,
從1970年到1999年。
1972年臺大中文系跟外文系合辦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協會進軍國際。我代表參加
所有國際會議為臺灣發言。1949年政治大斷裂後,臺灣保持中國純正的文化,
我們有最好的學術環境、著作,所以我和外文系、中文系許多同事共創比較文
學會向國外發聲。從1960一直到1985年臺灣文學是國外漢學研究唯一的教材;
我所編的《臺灣中國文學選集》是唯一的教材。
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做?我兩次參加Fulbright exchange program,我們能夠教
別人聽到,一定要有實際的東西。至今我仍鼓勵自己要有拿得出去的東西。所
以我們有《筆會季刊》,至今已發行40年未曾拖期。因為我們相信,文化在文
學上凝聚所有的心力應該持久不變。
1949年我為了婚姻第一次離開臺大,走入一個女子一生最困難的路:家庭與事
業兼顧的路。其中的困難,如果你未曾經歷很難瞭解,我的兒女也很難原諒。
剛才校長說我是齊邦媛女士。「女士」二字,可不容易,我寧可作老師、教
授,但女士就有很多複雜的身分、複雜的角色、複雜的快樂、複雜的痛苦。
1949年傅斯年校長在臺大校慶說:「我們現在要辦一所真正的大學。為什麼要
辦真正的大學?因為我們現在臺灣,退此一步便無死所。我們要貢獻這所大學
宇宙精神。」政治大斷裂時,幾百萬人回不了家,幾千萬人在尋求未來的目
標,這個宇宙精神是鼓勵也是自信,我們希望有這個能力。許多人渡海而來,
將1949以前所珍貴的、所學習的帶來,所以臺大自從1949以後日漸壯大,成就
今天的臺大。
我到臺大的時候只有1000多個學生。外文系僅有20個學生左右。我是唯一從大
陸受聘來臺的一個小小助教,心裡想的「宇宙精神」代表了很多的希望、很多
努力的目標,所以自從有機會以來,我就不斷地投入教育。希望把一代又一代
的年輕人帶出來看到我們必須要做的事。
我們能做什麼?我們能夠把臺 灣做成什麼樣子?這麼多年我們看到,今天臺灣
在世界上,以這麼小的地位,創造出的文化地位,實在不是我們自己在這裡誇
口。
在這個瞬息萬變的社會,我們還有不變的東西。今天,似乎所有的人都在談論
科技的進步,都在談論那些優秀的人的成就。那些優秀的人都說:「我要改變
世界。」可是我們自從來到臺灣以後一直在改變世界,一直在改變臺灣,一直
使得臺灣進步;我們一直在做,沒有一天不做。我和那些朋友推動的,都是奠
定臺灣文化真正的基礎。
最近大家都在談論賈伯斯,而我因為想要真正了解一個時代,所以也看了他的
傳記,我看的非常有興趣。他跟他同時代的人一樣有夢想,可是他的夢想是從
中間出來的,而我們當年的夢想是從基層出來的,兩者相當的不同。他們追求
的是超越別人,超越一切的成功,這種超越的力量是一種熱狂,也是一種快
樂,能得到如此的成功是非常高的境界,但最後他也會覺得:這樣大的星空,
這樣大的宇宙,要如何才能夠得到最後的勝利?當他知道自己生病不久人世
時,堅持找可靠的人寫傳記。作者問他:「你不是一個很重視隱私的人嗎?為
什麼要把你的傳記寫得如此詳細?我會寫下你的許多優點和缺點,難道你不在
乎嗎?」他說:「這就是我,我奮鬥的經過、我的夢想,我希望我的孩子將來
能夠知道我為什麼常常不在家?我希望他們知道我做了什麼,希望他們了解我
是怎樣的人。」看到這裡,我已經把書看完了。
我想,原來他那輝煌的,21世紀的成功,跟20世紀我的父親、我的祖父那一代
的成功其實完全一樣。他想要告訴後代:我們做什麼,我們怎樣做;我們努力
地做,我們用所能做的方式做了。我從他的傳記裡看到世世代代開創世界,做
一個文化的成就時,就像賈伯斯所做的,將人文與科學結合,缺一不可;因此
你不可能再回到原始洪荒的世界。
我直到跟朋友討論時才了解,人生瞬息萬變只是表面,瞬息萬變之後得到的是
不變的東西,是永恆的價值。人間的情、愛、了解,實在是永遠、永恆不變的
關懷。我真的很感謝臺灣大學對我有整體的評估,知道我所做的在這個校園,
在牆裡牆外,都是為了尋求永恆的價值。我這一生用種種方式推行文學教育,
一直用文學教育和永恆的價值跟青年朋友、後代苦口婆心地說:「我們必須這
樣活下去,才有未來;無論臺灣多小,世界多大,我們有真正的宇宙精神。」
這個宇宙精神並不是空言。對於年輕的學生跟朋友,我希望你們在進步的科學
設備之下,能有時抬起頭,不要只專注在機器上;看看比你更小的學生、朋
友,跟他們講講文學之美。你們一定要看看大的、厚的、專注的、有焦點的
書;才夠思考大的、厚的、專注的、有焦點的問題;才能對世界做出大的、厚
重的、有貢獻的事情,這也是我對還在教書的朋友最大的期待。
我很感謝當年臺大給我機會,讓我們(外文系)跟中文系可以合辦文學教育,用
中文推銷西方文化,用西方文學來推銷臺灣的文化。我們變成了一個被人看
見、被人了解的地方。希望年輕的老師們、未來的老師們能夠多多了解:無論
機器有多進步、能做多流暢的溝通、擁有多新穎的形貌,人性的溝通還是最重
要的。現在人都活得太久了,賈伯斯56歲去世,大家都很驚訝:怎麼他會在56
歲就死去了?他還有30年的時間啊!但是當人能活得長久,我們要怎樣活著,
卻是一門大學問。我們應該要好好地利用這些時間,我也希望未來的人性能和
從前一樣,追尋更好的世界。
我一生所留戀的美好的事情已經過去了,譬如文學題材裡的等待。我們那時迷
路的感覺、悲傷的感覺已經不在,連郵票都已經沒有人用了,將來想看到郵票
可能只在郵票百年大展能看見。這些美好的東西,在形式上或抽象的看法漸漸
都要過去,可是一環接著一環,這世界有不同時代的美好串成整個人類永恆的
價值;瞬息萬變是必然,但永恆的價值也是必然。
感謝謝立沛老師贈書2010/2
忘不了的人和事
才是真生命
--- 齊邦媛《巨流河》p. 433

巨流河
- 作者:齊邦媛
- 原文作者:Chi,Pang-yuan
- 出版社:天下文化
- 出版日期:2009年07月16日
齊邦媛《巨流河》-媒體報導
祖父母漢滿結合、外祖父母漢蒙聯姻,族群融合造就了有「鐵漢」之稱的資深立委齊世英,www.books.com.tw/activity/2009/07/htm/page06_8.html - 頁庫存檔 -
***
此書精彩 譬如說 許多人物軼事 包括胡適之先生與作者談文學之深度和品味等
有一些 缺點
最大的是無索引
少數人物上的資訊小錯或小誤 例如
Hippolyte-Adolphe Taine
譬如說 Hayek 來台時還沒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p.358 ) CZ 列車 California Zephyr

|
7.3創辦中興大學外文系
我有一個夢
第一次交換教員進修回來,回到台中一中教書滿兩年後,一九五八年秋天,轉任台中的台灣省立農學院教大一英文。事實是學術研究生涯的開始。
台灣省立農學院在一九六一年改為省立中興大學,而後才又改為國立中興大學。英文是共同科,除此之外還有國文、歷史、三民主義、體育等。在共同科的教員休息 室聽多了「雜拌」的言談,下定決心一定要推動中興大學外文系,可以有切磋琢磨的文學同道。
一九六○年左右,學校開設兩班大二英文選課,請我教一班,教材自定。
這一年正好是約翰‧甘迺迪當選美國總統,他的就職演說以及一九六二年去世的胡適先生最後的演講稿,加上美國黑人民權領袖金恩博士一九六三年的著名演說「I have a dream」,我在台中美國新聞處取得這三篇稿子,我大約讀遍了那裡的文學書。當時台中圖書館、學校圖書館的英文資料少得可憐。
我拿這些篇章再加上讀書時讀過的一些好散文,還有狄金蓀(Emily Dickinson)、惠特曼(Walt Whitman)與佛洛斯特(Robert Frost)的詩作教材,並且比較中西文化的差異。學生對我講的都覺得很新鮮。尤其在甘迺迪總統和金恩博士被暗殺後的國際氛圍中,大學畢業去美國的留學潮已經開始,有關美國文化的,較有深度的新文章非常受歡迎。
這門課是選修的,約有七、八十個學生選,但上課時擠了一百多人。教室大約只有七、八十個位置,學生因為座位不夠,就把隔壁教室的椅子搬來坐,常起糾紛。
那時的校長是林致平和後來的湯惠蓀,劉道元校長時期我開始向校長要求設立外文系。他們也常常在重要場合請我出席。
一九六五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海耶克博士(Prof. Friedrich A. Hayek)到台中各校演講,我受命擔任現場翻譯。他對我說:「待會兒我講一段,你就幫我翻譯一段。」我心裡忐忑不安,因為我大一雖然修過經濟學概論,但並不懂,所以很緊張。到了會場,看到台北還有好多人陪他來,包括台大名教授施建生、華嚴等,整個會場都坐滿了人,我有些心慌。
海耶克先生沒有給我演講稿,而且他講的英文帶有德國腔,不容易聽懂;他往往一說就是五、六分鐘才讓我翻譯,這真是很大的挑戰。還好,他偶爾會在黑板上寫幾個字。那是我第一次聽到「Closed Society」跟「Open Society」這兩個詞,我想「Closed」是封閉,「Open」是開放,所以就翻成「封閉的社會」與「開放的社會」,應該不會錯吧。後來大家果然繼續這麼用,這給我很大的鼓勵。
台大法學院長施建生後來對我說:「我帶他們走了這麼一大圈,你是當中翻譯得最好的。」而且也對別人這麼說。
後來,很多重要人士來台中,我曾為浸信會主教翻譯,這種翻譯我還能勝任。六○年代左右,蔣總統邀請《讀者文摘》總編輯來台,因為他曾寫過一篇關於台灣是個 新寶島的文章,到台中來也曾請我幫他翻譯,這些經驗給我很大的鼓勵。當然,緊張的心情是免不了的,每次站在台上,我都像是戰士披著盔甲上戰場,總想怎麼樣 能生還才好。文學作品的翻譯必須到達精深的層次,日後我推動中書外譯的一些計畫,因為那是更高的挑戰。
(詳見第七章)
| |||||||
|
文學播種——國文教科書改革
我到國立編譯館之前,對自己的工作已做了一些研 究。台中的教育界朋友很多,那才是真正的「民間」。國民中學的各科編審委員會全是新設,可聘請切合時代精神的專家學者,而不似過去只以聲望地位作考慮。在 這方面,王館長和我在大學校園多年,應已有足夠的認識和判斷能力。我的工作之一就是掌理人文社會各科的編寫計畫,既被迫兼掌教科書組,又須負責計畫的執 行,包括各科編審委員會的組成、編書內容的審訂。在一九七二年,那並不只是「學術判斷」的工作,也是「政治判斷」的工作。
我第一件事是仔細研究,分析暫定本國文的內容編排。每學期一冊,各選二十篇課文。翻開暫定本第一冊篇目表,前面兩課是蔣中正〈國民中學聯合開學典禮訓詞〉 和孫文〈立志做大事〉,接續就是〈孔子與弟子言志〉、〈孔子與教師節〉、〈民元的雙十節〉、〈辛亥武昌起義的軼聞〉、〈示荷蘭守將書〉、〈慶祝台灣光復 節〉、〈國父的幼年時代〉、〈革命運動之開始〉。政治色彩之濃厚令我幾乎喘不過氣來,更何況十二、三歲的初一學生!
是什麼樣的一群「學者」,用什麼樣「政治正確」的心理編出這樣的國文教科書?這時我明白,我所面臨的革新挑戰是多麼強烈巨大了。但是走到這一步,已無路可退,只有向前迎戰。
第一件事是組成一個全新的編審委員會,最重要的是聘請一位資望深、有骨氣、有擔當的學者擔任主任委員。不僅要導正教科書的應有水準,還需擋得住舊勢力可能 的種種攻擊,編出符合義務教育理想的國文。我心目中的第一人選是台大中文系主任屈萬里先生。
屈先生字翼鵬,是國際知名的漢學家,從普林斯頓大學講學返台,擔任中央圖書館長,其後轉任台大中文系系主任,不久又兼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而後膺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學術聲望很高。
柯慶明對我在國立編譯館要做的事很有興趣,也深深了解其重要性,所以他以接續編輯《現代文學》的心情,提供許多幫助,助我建立了第一批台灣文學作品的書 單,開始公正而不遺漏的選文作業。譬如他最早告訴我,司馬中原早期作品如《黎明列車》等,由高雄大業出版社印行,已近絕版,我寫信去才買到他們尚稱齊全的 存書。因他的協助,我們建立與作者的聯絡與認識,日後選稿能站住國家編書的立場。對於國民中學國文教科書的改進和定編,他有更真摯的關懷。他深感民間普及 教育的重要,願意幫我說動屈先生領導這艱巨的工作。終於有一天,屈先生同意我到中文系辦公室一談。
在那次相當長的面談中,我詳談舊版的缺點和民間輿論的批評與期望,這原也是王館長和我在台中淳樸校園未曾深入了解的。現在,不僅是基於職責而編書,更是為 國家文化的前途,為陶冶年輕世代的性靈,必須用超越政治的態度。當然,這樣一套新書是與舊制為敵的,雖無關學術立場,但將來不免會為主持者引來一些政治立 場的敵人。但是 不論付出什麼代價,為了未來國民教育每年每冊三十萬本的教科書,是義不容辭的。我清晰地記得,屈先生坐在那間陳舊的辦公室,深深地吸他的煙斗,然後嘆了口 氣,說:「好罷!我答應你!這下子我也等於跳進了苦海,上了賊船。」他語氣中有一種不得不然的複雜情緒(resignation)。我覺得其中有種一諾不 悔的豪情和悲壯,從潔淨超然的學術天地,走進政治、文化立場的是非之地,應是也經過許多內心交戰的思量決定。
屈先生主持「國民中學國文教科用書編審委員會」,由台大、師大、政大各三至五位教授和幾位中學老師組成。主編執筆者是台大中文系張亨教授、師大應裕康教 授、政大戴璉璋教授,他們都是中文系普受肯定四十歲左右的年輕學者。
為了一年後即須使用正式部編本教科書,第一、二冊必須編出定稿,在次年八月前出版。國立編譯館所有會議室,日日排滿會程,有些委員會晚上也開會。國文科委 員開會經常延長至黃昏後,當時還沒有便當簡餐,編譯館就請屈先生、執編小組和編審委員到隔壁僑光堂吃很晚的晚飯。屈先生有時主動邀往會賓樓,杯酒在手,長 者妙語如珠。
一九七三年以後,數代的國民中學學生至少是讀了真正的國文教科書,而不是政治的宣傳品。想來屈先生未必悔此一諾,他當年付出的心力和時間是值得的。可惜屈先生逝世後的追思文章,甚少言及他在這方面的貢獻。
三位主編初擬國文課本第一、二冊目錄之後,我們的編審委員會才算真正開始運作,屈先生掌舵的船才開始它的苦海之旅。在那政治氛圍仍然幽暗的海上,他不禁要 掌穩方向,注意礁岩,還要顧及全船的平穩航行。開會第一件事是由主編就所選二十課的文體比例及各課內容、教育價值加以說明,然後逐課投票,未過半數者,討 論後再投票。如我們預料,這個過程是對屈先生最大的挑戰。有兩位委員嚴詞責問:為什麼原來課本中培育學生國家民族思想的十課課文全不見了,現擬的目錄中只 有兩篇,由二分之一變成十分之一,其他的都是些趣味多於教誨的文章。楊喚的新詩〈夜〉怎麼能和古典詩並列?《西遊記》〈美猴王〉、沈復〈兒時記趣〉和翻譯 的〈火箭發射記〉都沒有教學生敦品勵學……。解釋再解釋,投票再投票,冗長的討論,爭辯,說服,幾乎每次都令人精疲力竭。
舊版大多選取含有政治歷史節慶、民族英雄色彩的文章,即使選了一些白話文,也都偏屬議論文;屬文學性質者,篇數略少。新版只保留孫文〈立志做大事〉,並將 舊版第二冊蔣中正〈我們的校訓〉挪移到第一課,其餘古典現代小說、散文、詩歌,全是新增;此外,更選入翻譯文章〈人類的祖先〉和〈火箭發射記〉,讓國中生 有人類文化史觀與尖端科技的世界觀。
想不到我當初萬般委屈接下兼任教科書組,被屈先生稱為苦海「賊船」的挑戰,是我付出最多心力感情的工作,也是我在國立編譯館最有意義的工作成果之一。為達 到改編的理想,恢復國文課本應有的尊嚴,讓每一個正在成長學生的心靈得到陶冶與啟發,在那個年代,我的工作是沉重的,不僅要步步穩妥,還需要各階層的支 持。
在政治高階層,我們必須尋求一些保護。我曾以晚輩的身份,拿著新舊國文課本目錄拜望早年教育部長陳立夫、黃季陸;也以學生身份去看望武漢大學第一任校長王 世杰,希望他們在輿論風暴之前,能對我們的改革具有同理心,因為他們自己是文人從政,對文學教育和學術尊嚴也有理想。我尤其記得黃季陸先生,對我侃侃而談 民國以來,國民教育的種種利弊得失,他很贊成政治退出語文教材,一談竟是兩小時,還說歡迎我以後再去談談我們編寫的進展。可惜不久他即病逝,我未能再聆聽 教益。老國民黨有不少被歷史定位為政治人物的文人,很希望在穩定社會中以書生報國之心從政,卻生不逢辰,生在政爭的中國。
在編審委員會中,我最需要資深委員的支持,當時代表編譯館最資深的編審者是洪為溥先生。我初到館時,他對這個外文系的女子敢來作人文社會組主任頗感懷疑, 甚至反感。經過幾次懇談後,對我漸漸轉為支持。討論第三冊篇目時,我大力推薦黃春明〈魚〉。沒想到首次投票,未能通過,我和屈先生商量:「下次開會,能不 能讓這個案子復活,再討論一次?」屈先生說:「還討論什麼呢?投票也通不過。」我說:「我為它跑票。」我第一個去跑的就是反對最激烈的洪為溥先生。他的辦 公室和我的相隔一間,窗外都對著舟山路台大校牆外一棵高大豐茂的台灣欒樹,太陽照在它黃花落後初結的一簇簇粉紅色果子上,美麗中充滿自信。他說:「這篇文 章講小孩子騎腳踏車,在山路上將買給爺爺的魚掉了,回到家反反覆覆不斷地喊,我真的買魚回來了!相當無聊,怎麼講呢?」
我想起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一本語文教學書,讀到一位中學老師寫他教初中課本選了莎士比亞《馬克白》(Shakespeare's Macbeth)一段:
| Tomorrow, and tomorrow, and tomorrow, Creeps on its petty pace from day to day , To the last syllable of recorded time. |
| (明天,又明天,又明天。 一天又一天在這碎步中爬行, 直到註定時刻的最後一秒。)(註1) |
下一次開會時,屈先生果然將上次未通過的幾課提出再討論,洪先生突然站起來說:「我們的學生百分之八十在鄉鎮,對〈魚〉中祖父和孫子之間的感情應是很熟 悉,這樣樸實的情景會讓他們感到親切。」第二次投票通過,我記得自己感動得熱淚盈眶……。
註1:採用胡耀恆翻譯:《中央日報》「全民英語專刊」(91年4月15日)。
(詳見第八章)
讓世界看見台灣文學 | 筆會時期
譯介台灣文學的橋樑——中華民國筆會
我既是作學術交流的人,必須先站穩台灣文學的立足點。自一九八五年柏林經驗之後,我得以從美國以外的大框架歐洲,思索台灣文學已有的格局和未來的發展。對 我啟發最深的是一九八六年在德國漢堡舉行的筆會年會上,西德著名作家葛拉斯(Gunter Grass)對支持俄共威權的東德作家,咆哮責問:「文學良心何在」?一九九二年在巴塞隆那的筆會年會,幾乎是該城向西班牙爭取獨立的一個論壇,我們收到的文件一半是使用該城的加泰隆尼亞語(Catalan),以示他們古老語文的存在意義。而最強烈的啟發則是一九九四年,在捷克布拉格的筆會年會,主題是「國家、種族、宗教、社會的容忍與文學」,由捷克作家總統哈維爾(Havel)主持,其中有一場座談會題目是「小語言與偉大文學(Small Languages, Great Literature),小語言寫作者的難題」。另一場是「我們自知幾許?」(How Much do We Know about Ourselves?)第 一次看到語言有大小之分,第一次聽到蘇俄解體後,五十多位作家各自回到獨立的國家,不用俄語陳述,而是重用小語言的母語創作,陷入另一種困境。我曾根據他 們的話寫了一篇〈我的聲音只有寒風聽見〉,文中並未明言我的憂慮,世界的漢學界已將注意轉移至中國大陸,台灣重要的作家多已停筆,本土化的聲浪日益高漲, 當年大家用中文寫作的熱情不再,會不會有一天,我們也面臨小語言,小文學的處境?
從此,我對台灣文學的關懷,就不再只是單純地鼓勵與評介,而是它在未來的發展和定位。一九九二年正式接任中華民國筆會英文季刊總編輯的工作,將近十年,得 以深耕台灣土地的文學創作,對這個大問題有切身的領悟。
這本英文季刊自一九七二年創辦以來,我一直是個實質的顧問。主編選集後,我對台灣文學的發展,以不遺漏的閱讀,保持真正的了解。因為「台大哲學系事件」 (1973年)而離開的趙天儀被教育部安排到國立編譯館任人文組編審,以及接辦《現代文學》的柯慶明,都助我深入認識本土作家。當時台灣詩社如雨後春筍, 我一直是訂戶讀者,日後主編筆會英文季刊選稿來源仍是維持公平的態度,尤其沒有「政治正確」的立場。
在自由世界,文學作者原不必有會,寫作是個單打獨鬥的行業,文壇原本無壇,只是有時文人相聚也有可談之事。一九二一年由英國和一些歐洲作家在倫敦成立了國際筆會(The International PEN),PEN是Poet, Essayist, Novelist的縮寫。一九二四年,中華民國筆會成立於上海加入總會,發起人有林語堂、胡適、徐志摩等人,第一任會長是蔡元培,開始做各種文化交流,作品互譯,作家互訪等拓荒工作。我自幼逢書便讀,讀後常有難忘之事,他們邀請印度詩人泰戈爾訪華的事,啟發我多年的想像。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筆會會員國參加戰爭,立場對立,文學交流停止,直到一九四六年,在中立的瑞典重開。中華民國筆會一九五三年在台灣復會,第一、二屆的會 長是張道藩和羅家倫。一九五九年首次回歸國際總會,參加每年一度的年會。一九七○年林語堂當選會長,在台北召開第三屆亞洲作家大會,邀請川端康成、張大千 等及韓國、泰國、菲律賓等國重要作家前來,台灣作家將近百人參加盛會。王藍、彭歌(姚朋)和殷張蘭熙三人負責辦事,在剛剛落成的圓山飯店將大會辦得有聲有 色,大大地提高了台灣的聲譽。林語堂說,台灣應該有一份發表作品的英文刊物,讓我們在東方與西方之間搭一座橋。
一九七二年秋天,中華民國筆會季刊(The Chinese PEN)創 刊號出版,由母語是英文的殷張蘭熙擔任總編輯,王藍和彭歌是編輯顧問。從創刊到一九九二年,殷張蘭熙獨撐二十年,我繼編九年,彭鏡禧、張惠娟、高天恩和現 任的梁欣榮都是我台大外文系的年輕同事,以拔刀相助之情前來兼任總編輯,助理編輯兼秘書只有一人,前十五年是劉克端女士,近十五年是項人慧,大出版社很難 想像那種「孤寂」。發書時增一工讀學生。三十六年來,春、夏、秋、冬四季運行,和大地運行一樣,中華民國筆會季刊至今發行一百四十四期,從無一季脫期,是 國際筆會最穩定最持久的刊物。在一百多個會員國的文學界,台灣是個有信譽的地方。
殷張蘭熙是最早作台灣文學英譯的人。一九六一年美國新聞處資助Heritage Press出版社英譯小說和新詩,殷張蘭熙就是《新聲》(New Voices)的主編,選入者白先勇、敻虹、王文興、陳若曦、葉珊(後改筆名為楊牧)等作品。因此執編筆會季刊之前,殷張蘭熙已有數年孤軍奮戰的經驗了。
殷張蘭熙(Nancy Ing)的名字和季刊幾乎是不可分的,她選稿,翻譯每期的詩,尋找高水準譯者,讀譯稿、校對、發排。創刊後三年開始用台灣藝術作品作封面,刊內介紹,她又增加了另一個領域的挑戰,在這方面協助最多的是王藍,我接編後是林文月、丁貞婉等好友。
殷張蘭熙金髮碧眼的美麗母親,一九一七年嫁給中國同學張承槱先生(來台後曾任審計長),由美國維吉尼亞州到中國湖北縣城成家,生兒育女。十多年後蘭熙長 大,畢業於成都華西大學外文系,一九四九年隨夫婿殷之浩先生來台灣,創立大陸工程公司,因為出國開會而冠夫姓,文壇好友都只稱Nancy。她愛文學,有時 也寫詩,一九七一年曾出版 One Leaf Falls 詩集。
一九七二年我從台中搬到台北,恰巧與蘭熙住在鄰巷,街頭蹓狗又常遇到。各自主編筆會季刊和《中國現代文學選集》,總有說不完的話題。最基本的話題是值得譯 介的書稿,英譯的人才,字字句句斟酌譯文,整體的安排,呈現的效果,國際讀者的反應等等,好似長河流水,永不厭倦。
蘭熙是個坦誠溫暖的人,忙碌中熱情洋溢。每年在各地召開的年會前,催集論文,安排演講和討論議題,準備禮物,到會場結交天下士,握住那麼多伸出的友誼之 手。大陸的「中國筆會」文革後參加總會,多次在會場排擠我們,蘭熙收起她自然溫婉的笑容,登台發言憤慨迎擊,保衛自由民主的台灣代表權。直到一九八九年天 安門事件後,他們不再出席年會。在今日政局情勢下,會籍立場仍會被提出,但是蘭熙與當年代表所建立的國際友誼,以及我們的季刊三十多年穩定的出刊,豐富的 專業形象,已讓中華民國筆會立於不易撼動的地位。中美斷交後,蘭熙受邀在美國十家地方電視台上「談台灣」(“Talk about Taiwan”)節 目,侃侃而談,以條理的分析,清晰的言辭,呈現台灣在文化、經濟、社會各方面的進步,英文的筆會季刊更幫助增加了解。那些年,在西方世界為台灣發聲的事, 蘭熙做了很多,但是在台灣反而少有人知。最可貴的是,這些奉獻和她主編筆會季刊二十年的投入都受到丈夫殷之浩先生全心全力的支持。季刊收入僅有外交部和新 聞局所付國際贈送的那數百冊書款,國內在誠品等地出售則不及百冊,主要的支出如稿費、印刷、發行及人事費用,皆由殷先生資助。筆會會址原也設在大陸公司所 在地,殷先生去世後,一九九六年開始租屋在溫州街,即將面臨斷炊時,殷氏「浩然基金會」開始資助,得以編印發行至今。
(詳見第十章)
↧
大洋洲的逍遙列島
大洋洲的逍遙列島(上/下) The happy isles of Oceania : paddling the Pacific
- 作者:保羅.索魯/著
- 原文作者:Paul Theroux
- 譯者:吳美真
- 出版社:天下文化
- 出版日期:2000年
上 冊:踩著泥水走過紐西蘭、在白人的澳洲胡扯、在烏普烏普漫遊、在絕地之北、擱淺於不安的特洛布里安、沙弗島的孵蛋場、萬那杜的食人族和傳教士……。
下冊: 王室之島東加、髒亂的礁湖、愛之島的迎風岸大溪地、庫克群島、復活島、在那帕里海岸追隨海豚前進、在天恩眷顧中划船……。
-----
我先翻末章.
可以談點譯注的微改善:
注1: 吉夫斯式的廢話
P. G. Wodehouse (-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小說中的人物指理想僕人
此君英文名字值得一記: Jeeves -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Reginald Jeeves is a fictional character in the short stories and novels of P. G. Wodehouse (1881–1975), being the valet of Bertie Wooster (Bertram Wilberforce
注5 內文談達賴團隊所用Om:應也說明此為佛教/印度教共用:根據吠陀經的傳統,「唵」這個音節在印度教裡非常神聖,它認為「唵」是宇宙中所出現的第一個音,也是嬰兒出生後所發出的第一個音。佛教受印度教影響,也認為這是一個聖潔音節,不少密宗咒語都以「唵」字作開首,如著名的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
-----
頁585 Herman Melville 1819-91 作品Omoo 最好附原文.
原作者引用的是下句黑體字 (紅字未翻譯)
CHAPTER LVII.
THE SECOND HUNT IN THE MOUNTAINS
FAIR dawned, over the hills of Martair, the jocund morning of our
hunt.
頁7 漢譯完全
But does not Alfred Wallace relate in his famous book on the Malay Archipelago
how, amongst the Aru Islanders, he discovered in an old and naked savage
with a sooty skin a peculiar resemblance to a dear friend at home?
不過發現本書的地名有的和地圖不一致. 所附地圖也不夠精確.
↧
詩探索 2002第3-4輯/.《浮世巴哈》也斯(梁秉鈞)2013
詩探索 2002第3-4輯 總47-48輯 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371頁 18元
(此書要感謝臺大文學院某善心人士拋書給我撿到......)
本书是一本探讨诗各个方面问题的书。全书分十三部分,内容包括:诗学研究,字思维与中国现代诗学,歌词与新诗,新诗文本细读等。
詩探索(2002年. 第3~4輯)
- 作者:謝冕,楊匡漢,吳思敬主編
- 出版社: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 出版日期:2002年12月01日
內容很雜. 我有興趣的部分:
梁秉鈞(也斯)研究
梁秉鈞:與城市對話. 王光明198
一種食事的倫理觀. 周蕾原著. 207
詩‧食物‧城市 梁秉鈞 215-224
(.《書與城市》香港:香江1985 /台北:東大1987年出版他的《城市筆記》後來還有許多相關著作如.......
-----
詩探索,每年4輯,每輯兩冊,分為理論卷和作品卷。此為2012年第3輯。主要收錄了各類風格的詩歌以及相關評論。
詩探索2012第3輯(理論卷+作品卷)
诗探索
诗探索,是以诗歌探索为主旨的诗歌网站,它由山东诗人金小麦、云南诗人马丽芳于2007年2月27日创建,网址是www.shitansuo.com
诗探索的愿望:涤荡诗坛风气,重塑诗人形象,诗歌再逢盛唐!
诗探索站长金小麦的诗歌随谈:
1、诗人行为:诗人,属于艺术个体的称谓,那么,对于一群诗人如何称谓,往往会冠之以派、社,这说明,个体行为的影 响远不及群体行为的影响的,所以,团结至关重要,诗人间的坦诚非常必须。如果说我们把诗歌看成一个行走的巨人,那么他的每一步都会体现时代足音。我们现在 所处的时代是国家正在回归超级大国,民族日渐强盛,以此为背景,对诗歌产生的影响,再逢盛唐不是不可能,当然阻力是有(简文,以后再论);重塑诗人形象, 我想大家应该知道目前社会上对诗人的评价,那么,我们诗人的最应具备形象是什么样的,他应该是丰满的、健康的、向上的;涤荡诗坛风气,目前的诗坛还是非常 萎靡,当然其中不乏充满信仰、追求、真实的好诗歌、诗人,是要涤荡,如果不涤荡,诗的形象重塑和诗歌再逢盛唐就是空谈。
2、关于创作:意象是 为诗歌服务的,而非诗歌为意象服务,意象是一种语言。如果不用崇高的心去读爱情,那么这首诗歌和你是相互陌生的。你不能因这种陌生而去用不解来品读诗歌。 诗歌永远是属于心灵的,诗歌也是心灵上空的琴弦,它是因感动而发出声响的。诗歌可以悲悯、愤怒、大知、大哀……,唯独一味发泄是低级的。诗歌是普通的艺 术,但却是语言里最高级别的表达哲学。诗歌不能放大自己,却可以放大眼睛,不关心爱情、他人、生命、人类、世界的诗人是不具备良知的,虽然并不妨碍他的技 巧和别人对他的喜爱。在茫茫的黑夜里,怕的是有路可走或走前人的路。文学和艺术帮闲到无耻,包括诗歌为“统战”服务都是我所鄙视的。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 神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最可贵的。
3、探索什么:诗歌探索也是生活的探索、社会的探索、人性的探索……,总其要,归其底,诗人的内心要善良,人心惟有善,诗歌才会好。
4、诗人和诗人之间:诗人之间需要团结,协作。诗人不是羸弱的形象,他们应该无比丰满、健康向上,深谙生活、亲近民众。
比如说我现在很穷,我不能只沉浸在诗歌的海洋里,我还要肩负起责任,使自己和家庭变得富有,又不能完全放弃诗歌,我 认为诗人在改变自己的过程中反过来又能影响诗歌、丰富诗歌。诗人和诗人之间相互尊重,对于诗歌中流露出属人类高尚情操的旨义我们就要推崇,还要坚决摒弃文 人相轻,甚至相诋的恶习。诗人之间的团结、协作至关重要,互相帮助不仅是在诗歌中,还有要在生活上、工作上、前途上、认知上等等,还要相互批评、相互鼓 励、相互欣赏、相互理解。诗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首先要理解这个社会,既不要将社会孤立于自己的身外,也不要被社会所孤立,当然,溶入社会,要有所溶,有 所不溶。用切身体会它,用眼睛观察它……
5、从侧面看诗歌的价值:一个诗人一生能写出几篇好的作品,又有几篇能传诵?或许有的诗人写了一辈子,在若干年之后,没有人能记住他的一个句子,想想如此,着实的悲哀。作为一个诗人,你的诗句能经常被别人引用,说明它是有价值的,作为一个诗人,你也是成功的。
6、诗人的素养:诗人首先应该具有良知,其次是责任感,再其次是使命感;诗人的眼睛应该既能看到光明,也能看到黑暗,推崇真善,抨击丑恶;
诗人应该有一定的社会功能性,不能空喊,不能只抒发自己,不妨作一作正当利益的代言人,这是在建立诗人的基础。…………
- 相关文献
- 千年变与守:中国诗歌,乡关何处-云梦学刊-2013年 第1期 (9)
- 胡先骕佚文《蜀雅序》考释——兼论胡先骕词学观念的文化守成主义倾向-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 第4期 (8)
- 审视,然后突围——“我们”散文诗群的引领者之一林美茂访谈录-梧州学院学报-2011年 第2期 (9)
↧
臺大:傑出教師 /校友雙月刊/意識報/ 臺大學生報/火花時代/ 臺大電影節/藝文年鑑
目錄
<校長開講>
<學院動態~院長面對面>
<研究發展>
<臺大學術資產>
<李弘祺專欄>
臺大校友第88期雙月刊目錄
http://www.alum.ntu.edu.tw/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2013/07/no88-e887bae5a4a7e99b99e69c88e5888a-e69d8ee5bc98e7a5bae69599e68e88.pdf
2013.4.30很妙
我今晚參加半場劉克襄的近來台灣蔬果的省思 (大意) 現在找不到當時的資料
2013年4月30日(週二)19:00不知怎的我記得演講8點開始...
講座:「晚近新種蔬果對我的提示」/講者:作家 劉克襄
臺大文學獎
http://literatureawardntu.blogspot.tw/
活動總覽
http://arts.ntu.edu.tw/activity/list/menu_sn/2
《展覽》 「紙上花園──臺大文學獎閱讀展」
2013-04-11 (四) 10:00 ~ 2013-05-31 (五) 17:00 雅頌坊 The Odeum
願生活是本詩集的目錄輕巧動人的語句
開啟花園的入口
下一個逗點之前
讓葉子接住你 向前
飛
我們將以文學獎歷屆得獎作品為策展文本,結合雅頌坊廣場中我們親自種植、照料的植栽地景,打造一間文學花園。在這裡你可以打開一本書,也可以認識一株香草,漫步在獨特的閱讀空間。這是一場展覽,更是一次種植計畫。
歡迎你,在晴朗的四月,一起來閱讀‧種花
 | 2013.5.15(週三) 「紙上花園-臺大文學獎閱讀展」講座 花亦芬老師主講:歐洲修道院的香草花園
|
2010年出版《不同的人生風景: 臺大教師傑出服務的故事》(社會服務;校內服務),包括2007 (社會服務3人;校內服務3人)、2008 (社會服務5;校內服務5)、2009 (社會服務5;校內服務4)
《臺大教學傑出教師的故事》
也許從2017年起,每年一本: 2010年表揚21位。約6-7年前我跟畢業於台大電機的王晃三教授說,他的母系教師有百位…..這本2010年的書說,是120位老師才對。
火花時代創刊號 2011.12.23
台灣大學學生會創的新刊物 首期32頁全彩 印510份
它的網站有問題 會讓你電腦出狀況
https://www.facebook.com/ntusparks?ref=ts&fref=ts
國立臺灣大學藝文年鑑 2008-2011
2007- 2010 都是約270頁全彩2011年換主管比較務實編輯 減半還有介紹現有的公共藝術專題
材
----
領學誌01這是領導學程前三屆的內部刊物 (2011)
-----
(島影)
臺大電影節電影論壇
-----
北京
中国知名导演谢飞发表公开信呼吁以分级制度代替电影审查制度。70岁的导演谢飞曾执导影片《香魂女》、《黑骏马》、《本命年》等,并获得过多项国际和国内大奖。在这封12月15日发表的公开信中,谢飞列举了诸多知名导演作品在送审过程中受到侵害的事例,其中包括姜文、田壮壮、贾樟柯。谢飞认为,国家对电影作品的管制和审查传统已经失去了实际的社会、经济、意识形态和文化意义,成为制约艺术文化市场的繁荣、扼杀艺术思想探索、浪费行政管理资源的成规陋习。此公开信发表之后,得到了包括业内人士、学者以及不少网民的支持。
*****
韓國媒體早已妥協 不敢批判大企業/台大韓生看反壟斷 羨慕多元台灣
 |
| 韓國首爾大學學生金俊植到台大交換就學半年後做出建言,台灣還沒真正了解什麼是「壟斷」,如果台灣一直往韓國方向跑,可能以後就來不及轉型了。(取自台大意識報網頁) |
若學韓國 恐來不及轉型
台大學生社團創辦的台大意識報,近日刊出一篇對台大中文系交換生、韓國首爾大學三年級學生金俊植的「泡菜與蕃薯,Life is good?」訪問。
金 俊植在文中直言,多數韓國學生及民眾對台灣不了解,幾乎都是透過中國大陸的視角在看台灣;更對於台灣近期甚關注的「壟斷」議題提出警語,台灣其實還不真正 了解壟斷是什麼,直到「反旺中」運動後才有一些模糊概念,韓國則早已長期被大企業壟斷,政經環境是政府、企業和媒體形成的三角架構,他們互相合作、聯姻。 韓國媒體雖沒被政府直接控制,但報導早已跟執政當局妥協,也沒敢批判三星等大企業,因廣告會被抽掉,敢批判的媒體越來越薄弱。
大企業壟斷四、五十年
韓國被大企業壟斷有四、五十年,依賴程度太大了,來不及轉型。就像韓國核電比例三十三%,轉型太難,但台灣核電比例只佔十六%,還可想到節能、替代電力等方案。
金俊植昨日接受本報記者訪問更指出,台灣與韓國的媒體環境目前還有點不同,韓國的政府、媒體與企業早有很緊密關係,年輕人很少自由發聲空間,在韓國,若出現類似「反旺中」的活動,年輕人恐不太敢站出來嗆聲,怕影響日後的就業機會。
怕影響就業 年輕人噤聲
金俊植指出,在台灣所有的一切都可以被懷疑,但韓國不是這樣,這種懷疑的精神可以讓社會很多元。台灣媒體環境,目前要面對的是大企業要直接買下媒體問題,要避免被壟斷、被洗腦,跟韓國比起來還算有希望,應該繼續加油、努力下去。
金 俊植的友人、世新社發所碩一的陳廷豪表示,金俊植對台韓差異有許多觀察,談到韓國經濟特別有意思,「台灣輿論對韓國的經濟、企業等方面,一直是一面倒的叫 好,但沒有深刻反省其中的好與壞。」就如過去台灣人會認為,三星等大企業對經濟有很大幫助,但金俊植卻看到不同現象,「韓國大企業、大媒體壟斷市場,年輕 人不能批評企業,批評就會沒工作,言論也受到限制,並不如表面看來的好。」
韓國觀點 引發網友討論
韓國學生的論點也在網路引起討論。有網友指出,從韓國角度看台灣,是不一樣的文化體驗;還有南韓網友表示,金同學所說「南韓現象」是真的,至於他所說的「台灣現象」,台灣人應該自己最清楚。
****
臺大校友雙月刊
http://www.alum.ntu.edu.tw/wordpress/
【記者馮天昱、王泓琦/報導】
臺大校友雙月刊
http://www.alum.ntu.edu.tw/wordpress/
- NTUSNews
1988創刊,2009開新頁
以平易近人的校園新聞作為本報社的基調。 報導分為五個面向「即時」、「現象」、 「社團」、「休閒」與「專題系列報導」。 紮實的新聞採編、生動的基礎課程、精彩的社內講座,本學期的學生報社歡迎你的加入。
BLOG:http://ntusnews.blogspot.com/
[134][藝文]夢想的起點 臺大學生的創業之路
夢想的起點 臺大學生的創業之路
------------------------------【記者馮天昱、王泓琦/報導】
「如果一個國家最優秀的青年都只以考取公職為目標,就是一個國家競爭力下降的開始。」十二月十六日由生傳系三年級林昆彥、歷史系三年級胡秩瑋所舉辦的『夢想的起點』,是來自不同系所但有著網路創業夢的臺大學生們,在此時分享彼此的經驗,朝著夢想前進。
此次活動參與的團體有在臺大批踢踢轉錄功能上提供更方便管道的Credarp,他們獲利的方式是以活動相關之器材設備廠商為廣告主進行廣告。另外一個發表團體為眾多住宿生們所熟知的i-food,他們提到,是為了集合住宿生的晚餐以及宵夜需求而有此概念。此外,由臺大法律系同學所設立的Bios是一個提供城市生活資訊的網站。
Buyble國際代購公司的創辦人呂元鐘也來分享創業經驗,同時是臺大的校友的他提到,自己和其他公司不一樣的是懂得如果創造「不一樣」。除此之外,Shotwill提供愛好攝影的業餘玩家一個平台,在這個平台上,人人都能將自己的攝影作品上傳,創造出一個全新的分享互動,且同時具有營利效果的形式。
談 到為何想要舉辦這個活動,林昆彥解釋,由於在過去能夠使人成功的方法早已與現在不同,現代著重的是創新與創造力。此外,自己本身的興趣所在,以及許多臺大 同學也有創業的想法,也是舉辦此活動的原因。他認為,過去大家嘴巴說說的想法階段若一直無法轉化成實際行動力,何不給自己一個機會闖闖看。
至 於在網路創業過程中遇到的困難,林昆彥提到,最大的困難點在於與創業夥伴的溝通和協調,夥伴之間意見不合的衝突是必然的,他們也直接對彼此說出心中想法來 化解。此外,林昆彥也談到,系上所學的行銷更能應用在宣傳、接洽以及公關的工作上。至於未來是否還有舉辦此活動的機會,林昆彥表示,希望未來一個學期會有 一次的聚會,讓更多對於網路創業的臺大同學能夠有個彼此交流、分享的機會。
[134期][資訊]產學合作新體驗 臺大生助劇團管理行銷
產學合作新體驗 臺大生助劇團管理行銷
------------------------------
【記者李承軒/報導】
------------------------------
【記者李承軒/報導】
「管理學」不僅能提升企業的營收與績效,還能讓人們走進戲院,讓藝術走進人們心中。本學期,有一群管理學課程的修課同學,與國內知名劇團「創作社」進行合作,藉由課堂實作計畫CMP(改革管理專案),提供劇團不同以往的管理及行銷方式,期望藉此提升觀眾人數、推廣劇場藝術。
「創 作社」是國內知名劇團,成立迄今已有十五年的歷史,其作品風格獨特,美學面向豐富。本劇團最初由八位藝術工作者集結成立,其中包含紀蔚然、周慧玲、王孟 超、魏瑛娟、林靜芸五位編劇家。劇團成立初期,由於每一位編劇的創作風格都不盡相同,「創作社」這個「劇團」在觀眾心中並沒有留下清楚鮮明的印象。然而, 隨著作品一次、一次的獲獎,劇團的知名度也越來越高,戲劇作品的「原創性」成為劇團最大的特色,也吸引了一批劇場愛好者成為固定客群。除了固定客群之外, 劇團行政人員也努力進行劇場藝術推廣,希望能以不同的方式吸引年輕人走進戲院。
本 學期,在戲劇系三年級張祐寧的提議之下,有一組管理學的修課同學與創作社進行合作,提供劇團更多元的管理及行銷方式。劇團行政總監李慧娜表示,這群同學讓 她看見了年輕人的思考方式與創意。舉例而言,劇團過去對於臉書的經營一直沒有跳脫「業者-顧客」的思維,只會在作品的宣傳期間提供票價及演出時間的資訊。 同學卻提醒她,應該要把臉書上的每一個人都當成創作社的「朋友」。在平時就要發佈一些劇團的動態,也許只是一張簡單的照片、簡短的一句話,都能拉近劇團和 觀眾的距離。此外,也能在臉書上提供一些「劇團小知識」,藉由網友的轉貼分享,達到藝術推廣與劇團行銷。李慧娜說,這些同學還提醒她,對於不同的客群應該 給予適當的「差別待遇」。過去,上網註冊的會員「創作社之友」只能定時收到劇團的演出資訊,未來她將規劃劇團的「早鳥票」由會員限購,藉此鼓勵觀眾上網註 冊,也強化了劇團行政人員對於顧客資訊的掌握。
國 企二楊任翔表示,他們也建議劇團從不同的基金會尋求贊助,減輕高中生的購票負擔,提供高中生低於五折的優惠購票,讓年輕人有動力走進戲院、享受藝術所帶來 的感動。李慧娜說,希望藉由這些同學提供的改革管理計畫,能讓網路時代的學生族群嘗試走入劇場,給藝術家一個機會,也給自己一個機會。
創作社將在今年重演去年極為賣座的療傷喜劇<我為你押韻-情歌>,一月二日開始開放購票,詳情請洽兩廳院購票系統。
[134期][要聞]校馬開跑 成績計時混亂惹議
校馬開跑 成績計時混亂惹議
------------------------------
【記者馮天昱、王泓琦/報導】
一年一度的臺大校園馬拉松在一百年十二月三日圓滿落幕,雖然比賽進行得十分順利,但在賽後有不少參賽者對於名次卡的發放順序有所疑慮,在臉書上的一百年台大新生臉書聯合交流版及批踢踢的臺大版討論。
------------------------------
【記者馮天昱、王泓琦/報導】
一年一度的臺大校園馬拉松在一百年十二月三日圓滿落幕,雖然比賽進行得十分順利,但在賽後有不少參賽者對於名次卡的發放順序有所疑慮,在臉書上的一百年台大新生臉書聯合交流版及批踢踢的臺大版討論。
校 園馬拉松舉行當天,有參賽者表示,在現場問了工作人員關於成績的排序,工作人員說明只有第一道的前一百名有準確的排序。換言之,其他跑道與一百名之後的名 次記錄較為草率。對此,幾位參賽者在比對後發現,確實有秒數較多而名次卻較為前面的情形發生。此外,更有參賽者提到,不知道自己完成賽程的時間,只能以大 略估算,許多同學對於臺大處理這個重要程序的態度感到不滿。
面對種種質疑,體育組解釋,本 次活動參賽人數高達四千五百零七人,賽會為讓所有參賽選手都可查詢到自己的成績,第一次實施公布所有參賽選手的計時成績。但當日入場人數眾多,在男學生組 部分,雖分為三個入口道,在一百名以後,由於同時湧入過多選手進入終點,在領取名次順序卡的過程中出現了失誤,有些同學可能從第一道或第三道開跑,卻跑入 第二道領取名次順序卡的情形,導致許多名次與計時成績無法對上的狀況。
針對同學抱怨的狀況,體育組回應,今年馬拉松賽為了使活動進行更為順利以及讓參賽者有更好的參賽經驗,而在活動規劃上做了一些調整。其中許多措施都是賽會首次實施,包含了網路報名、紀念衫、公告所有參賽人員的計時成績等機制。體育組也期望未來在此部分將會做更完善的安排,並使明年賽會能更圓滿。
[133期][校園]藥學系水森館建物落成 內部設計進行中
藥學系水森館建物落成 內部設計進行中
------------------------------
【記者周紫陵、呂一萱/報導】
------------------------------
【記者周紫陵、呂一萱/報導】
藥學系新系館水森館已於民國一百年一月舉行落成典禮,但因內部設計尚未規劃完成且經費仍在籌措中,至今仍未遷入。水森館預計作為教學研究大樓,主要供研究之用,同時保留學生活動的空間。
藥 學系目前和醫學院共用基礎醫學大樓,面臨空間不足的困擾。不僅學生活動範圍狹小,不敷使用,且由於每位教師都需要實驗室及研究空間,導致藥學系現任教師額 雖然尚未達到聘用上限,但限於研究室的缺乏,無法聘任更多教師。藥學系系學會總務長高廷宇表示,十分期盼在新大樓中能有屬於學生的活動空間,增加同學對系 上的歸屬感,也能促進彼此的情誼。
水 森館規劃的核心單位為藥學系空間規劃委員會,由於招標程序冗長,加上高規格的環保要求,目前水森館的空調設備、消防排氣管線以及內部配置多未定案。不過藥 學系系主任顧記華表示,系上絕對傾聽並且尊重學生的聲音,除了實驗室、研究室、會議室外,也承諾有經常性活動地點供學生使用。水森館內部裝潢的完工日期還 無法確定,但顧記華提到,新聘教師將於民國一百零一年八月上任,意即在此之前,水森館應邁入基本可進駐階段,為新聘教師準備好部份研究空間。
2012年3月6日星期二
[133期][校園]管院新進教師六年英文授課 部分學生反應成效不佳
管院新進教師六年英文授課 部分學生反應成效不佳
------------------------------
【記者游任博/報導】
------------------------------
【記者游任博/報導】
管理學院規定新進教師前六年需使用英文授課,本學期扣除大一英文外,管院開設了最多的英文課程,因此有許多同學抱怨英文授課會降低學習成效。管院副院長李吉仁認為,這是為了國際化的要求,因此無法避免,但是時候該做通盤檢討。
李吉仁表示,為了提供本國學生能有更多機會到國外交換,臺大也需要提供大量的英文課程給外籍生,換句話說,開設許多英文課程等於是提供同學更多機換到國外交換。此外由於管院有Global MBA program,因此需要提供更多英文課程給外籍生。
由於商管領域相較於其他學科,有地域以及文化的差異,因而更加多元,此外也比較沒有銜接的問題,因此管院學生交換比例是全校最高,近年更高達四成至五成,所以交換來管院的外籍生人數較多,也需提供更多英文課程。
除 了提供誘因讓老師自願開設英文課外,自上一任院長洪茂蔚任內,規定新進教師前六年需使用英文授課。李吉仁表示,已經經過四、五年英文授課的陣痛期,是時候 該做通盤的總檢討,他認為應該協助並輔導教師使用英文授課,並且是循序漸進,而非沒有英文教學經驗就直接授課,這樣才能降低英文授課的問題。
李吉仁表示,同學若對英文授課感到不適應,要在期中、期末教學意見反應。他認為英文的邏輯性教中文好,若同學聽不懂,則很有可能是老師表達上的問題,若是英文授課專注力較低的話,則是同學自身的問題。
這學期開設兩門使用英文授課的國企系副教授王之彥認為,用英文授課多少會影響師生之間的互動,但學習成效主要取決時學生是否盡力學習,跟使用哪種語言授課沒有太大的關係。另外他認為英文授課有好處,由於管院對英文特別要求,英文授課對學生而言也是種練習。
訂閱: 文章 (Atom)
意識報051刊目錄(04/08/2012)
意識社論
戳破依法行政的謊言
議事專題
從殘存的時代悲劇談起 ◎人類二 陳瀅
吹入校園的風暴──省工委與五零年代白色恐怖 ◎生傳三 廖翊筌 人類二 陳瀅
白色校園的美麗與哀愁──專訪張則周老師 ◎大氣三 陳梁政
發掘歷史的先行者:藍博洲──追尋那已然消逝的精神 ◎歷史三 李盈佳
發掘歷史的先行者:林樹枝──良心犯的血淚史 ◎法律四 吳俊志
發掘歷史的先行者:陳銘城──為受難人權發聲的記者 ◎人類二 陳瀅
汪洋中的一盞明燈──談轉型正義在當代的意義 ◎法律四 吳俊志
重返白色的記憶之門──重訪臺大與師大策展者 ◎社工三 孫文駿
校園意語
那些強拆士林王家之後的事 ◎中文三 王立柔
總編的話
各位支持意識報的朋友們大家好,我是意識報新任總編輯曾稚驊。意識報至今已四年多了,我們持續的在校園議題中耕耘,期望能成為台大最具代表性的校園刊物。我們還在這條路途上,感謝所有支持的朋友,我們會繼續努力向前行。
本學期意識報與台大學生會合作籌辦了台大1950年代白色恐怖檔案及影像展, 因此我們有更多機會對這段過去作深入的探訪,並帶來了此期刊物。從當代殘存的六張犁公墓開始,我們將時空拉回了過去,這股白色的風暴究竟是如何吹入校園之 中?而當時校園中的受難者張則周老師的經驗又是甚麼?在時代洪流中不斷努力發掘歷史的幾位先行者,又有甚麼經驗可以分享呢?而回到當代,轉型正義的意義何 在?我們又可以做些甚麼呢?本次意識報與各位一同重返這道白色的記憶之門。
最後,在閱讀本次意識報之餘,也希望各位朋友能撥空前往博雅教學館一樓參觀展覽,感謝各位的支持!
有空再研讀東海的學生刊物
昨天向台大的《意識報》敬禮 !!!!
《意識報》網址:
http://cpaper-blog.blogspot.com/
這一期045批判力道很弱 (想平衡報導)
意識報045刊目錄(16/10/2011)竹北特刊II
主編的話
再一次的,我們來到了竹北 ◎社工三 董 昱
說不完的故事:東海故事集
細說竹北──童言童語話故鄉 ◎外文三 陳莉容 會計三 翁栢垚
面對區段徵收的另類反抗 ◎生傳五 黃怡安 社工三 孫文駿
人類二 陳 瀅 藥學二 張雲翔
農村之於布爾喬亞的再詮釋 ◎政治三 謝佳榮 社工三 施郡珩
夢想還是幻想:竹北璞玉計畫
一些關於璞玉計畫的小夢想
──完整規劃,美麗未來 ◎化工三 曾稚驊
一些關於璞玉計畫的小幻想
──專訪東海國小林老師 ◎化工三 曾稚驊 外文五 劉時君
北教大 陳廷豪
總編輯的話:
再一次的,我們來到了竹北。這片位於竹北東側的土地,在景觀上仍呈現平靜、安詳的樣貌。然而,平靜的外貌下,我們不能忽略的是,土地徵收的議題仍然冰冷的撕裂著人與土地的情感聯繫。
今年暑假,意識報在校內開設「服務學習課程」,並且與當地的「東海國小」合作,舉辦「影像說故事營」。不論大小朋友,都一起在有限的時間內,蒐集最大量的素材,寫下最直接的故事。本期意識報延續第39「竹北特刊」的內容,繼續在竹北的「璞玉計畫預定地」上,記錄著說不完的故事。
一些璞玉計畫的小幻想:專訪東海國小林老師
標籤: 045竹北特刊II, 夢想還是幻想:竹北璞玉計畫
璞玉計畫從2000年宣布開始,至今已經超過十年,由於地方對於計畫的態度有著很大的分歧,計畫至今仍未落實;即使計劃不斷的拖延,龐大的開發利益仍然讓當地的農地喊價至一坪七萬多元。隨著土地的價格水漲船高,開發的呼聲也就越來越大。
當地居民面對這項龐大的開發案的觀感可以普遍分為兩派:以璞玉計畫促進會為首的「贊成徵收派」與以璞玉計畫自救會為首的「反對徵收派」。這場辯論不只是相 互不認識的觀眾之間的意見發表與切磋,而是真實地在切割當地居民的感情,並隨著時間越拖越久而切得越深。
在此,我們訪問了於東海國小任教的林伯殷老師。林老師從小就在竹北東海成長,對於這塊土地有著敏銳的觀察;懷著對故鄉的濃厚情感,林老師試圖從「贊成」與「反對」的切割中,找出第三條路的可能性。
感情?錢?天平的二端
竹北當地的居住者多數為客家人,過去居民之間關係相當密切,在祭祀與宗教上,從當地為數眾多大大小小的土地公廟,與定期的祭典時各家奔相走告並出席參與的盛況,便可略知端倪。但是這種感情上的聯繫,在近年來土地不斷徵收開發之下,慢慢的變了樣。
「在 地的土地糾紛實在很多,就拿電線桿上的廣告來說就好,別的地方會有尋人啟事和宗教信仰的條子,但是在竹北這邊,更多的是會看到電線桿會貼上販賣土地或不動 產公司的廣告,而且非常多。另外,我甚至看過有人在電線桿上公開地在詛咒他的兄弟啊。」林老師口氣透露著些許的感慨:「一點也不誇張,這是真實在當地發生 的事情。當一定要被徵收時就會面臨到財產分家的問題,初期一坪地可能是幾千元,後來經過炒作後,現在一坪可以賣到7萬元。在這樣龐大的利益之下,我們的情 感也就隨之消失了。」
「這 裡就是我從小來玩的地方,當然是希望她保留原有的景觀。」林老師用這一句話,明白地說出他的心聲。「為什麼凡事要用經濟效益、金錢來做計算呢?農地這樣留 了下來,不但風景宜人,且這樣的生活方式對我們健康來說也比較好吧?而且,我們東海里這邊當地有非常多的客家文化,也有許多的民間伯公信仰,若不再多替台 灣保存一些人文素養,之後我們台灣人見面就只剩下比誰的錢多了。」誠如林老師所說,土地是人們居住之處,如何使用土地,決定了人們的生活品質;但是透過居 住與生活,土地更是讓居住其上的人們,不論血緣是否親近、年紀是否相仿,彼此之間關係聯繫的最重要根基,而這絕對是無法用錢去評估、去彌補的。
盲目的發展邏輯
許多支持璞玉計畫的人高舉開發的旗幟吶喊:「都市發展計畫可以帶動當地產業發展,進而增加當地工作機會。土地徵收利用是一種社會進步必然發展的趨勢。台灣的經濟要起飛,不可能永遠停留在務農社會。」
「工 業」發展被視為是璞玉計畫的目的。這些論述都指向農業是「落後的」、難以維生的。但事實上,如璞玉計畫這樣的工業發展,是人民所需要的嗎?在交通大學與新 竹縣政府介紹璞玉計畫的網頁中,皆有提到璞玉計畫將與IC產業與生物技術產業,如半導體、影像顯示......等「兩兆雙星」計畫相關連;但以半導體產業 為例,國際大型公司多委外代工,因此台積電等台灣的大型公司雖然訂單充足,但幾乎都為代工,而代工早已被指出相較於技術專業與品牌形象,是個利潤最為短缺 的分工。
並且,代工的產業結構關係帶來的只是短視近利的經濟,委外國與代工國之間,各自需承擔的風險是不平等的。以半導體產業為例,在製程上從製作晶圓所需 的砷、鎵等致癌的過渡金屬,或是清洗、蝕刻時需要的鹽酸、硫酸、硝酸或氨水等強酸或刺激性物質,或其他使用作清洗的有機溶劑,與其他如砷化氫、磷化氫等毒 性特殊的廢氣等,姑且不論廢棄物與毒性物質的回收流程設計,光是以近年來桃竹苗地區十大死因中,肺、肝癌幾乎都高占一二名,便可對於這些汙染的嚴重性略知 一二;另外這些產業對於水與電的需求都相當龐大,反思政府單位言猶在耳的節能減碳政策,彷彿就像是一場笑話。
許多人認為,台灣的耕地過於破碎,使得農產品無法與外國進口的糧食競爭,因此不適合農業發展;還有些人認為,稻作農業由於灌溉的需要,浪費了許多珍貴的水 資源。因此,在水與土地方面,工業對於自然資源的利用可以更有效率;因此,我們不需要浪費資源的農業,需要技術密集的工業;因此,最好我們還需要大學來幫 助我們研發工業的技術;因此,我們可以擺脫貧窮,擁有更高的社會地位;因此璞玉計畫勢必要執行。
與其說人們期待的是發展,不如說人們是對工業化有很高的期待。事實上,上述這些都是今天台灣農業必須面對的困境,但是為什麼人們不是選擇改革農業,而是選 擇將農業完完全全的拋棄呢?農業難道不可以「技術密集」,而成為土地利用的專業嗎?為什麼不質疑工業可能帶來的汙染,而是將焦點集中在農業的利潤不足?改 革農業所需要付出的代價,難道真的比剷平稻田去豎起工廠來得高嗎?
「這是自信的問題」,林老師快速地說:「例如今天班上有五十個人,其中四十九個同學去留學了,你沒有去留學,這個時候你怎麼辦?就盲目地去和他們一樣去留 學嗎?有沒有認真想過為什麼我要去留學呢?會說這個是趨勢、潮流的,其實自己心裡就設限了,認為這是一種不可違逆的真相!」
為什麼他們反對璞玉計畫
璞玉計畫挑戰的是人們對於農業的認同感;根本來說,食物作為農產品的本質,這項事實在市場場域的交換關係之中不斷的被忽略。人們之所以嚮往工業,是因為工 業商品帶來許多經濟利益,而經濟利益的衡量是靠貨幣、是數字,是那些在現實中無法讓人「吃飽」的幻象。工業商品之所以能讓人感到飽足,是因為它所交換而來 的金錢,有辦法讓我們購買到食物。
但是,一旦交換的網絡無法形成,任何工業商品也就無法餵飽今天的人群。隨著石油等化石燃料的價格不斷上漲,「交換」這項動作的成本也不斷在提高;再加上, 台灣在工業上仍處在「代工」的分工流程之中,交換更是其中的利潤來源。難道,我們真的只為了彌補交換本身的成本,而犧牲農地來生產更多工業商品嗎?如果我 們貿易的目的就是為了要吃到豐盛又精緻的食物,為什麼還要犧牲那些食物的來源──農地呢?
當人們用金錢購買其他國家的食物時,卻仍以為這些食物這是自己生產的。台灣目前的糧食自給率約為32%,換句話說,我們平常吃到的食物中,有32%是「生 於台灣又長於台灣」的,有其他68%是來自於其他國家生產的農產品。只要來自於外國的食物越多,交易的成本也就越高。同樣的,如果交易的成本高到人們實在 無法進行交易了,那麼,誰來補足這個將近七成的食物短缺漏洞?
為什麼反對璞玉計畫?因為土地的價值不是在於炒作出來的誇張價格,而是其所乘載的種植、培養的功能;土地的意義在於生產食物本身。更不論那些農民在農業勞 動中所獲得的成就感,抑或乘載於農村中的文化元素,以及這些元素所帶來的優良生態環境、教育資源、孩童的童年回憶……等。
台灣的農業固然仍面對許多挑戰,但是不代表沒有解決的方法。目前已經有許多人和組織開始投入相關的工作,例如:培育更優良的品種、研發更有效的耕作技術、 生產環境友善的食物、發展社區支持型農業(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等。這些都不失為改良傳統農業的方式,有許多都已經開始實施並頗具成效。對於竹北而言,問題不是改善農村的具體方法是否存 在,而在於「選擇哪些方法?」、「如何執行?誰來執行?」。而關於這些問題的討論,已經是另外的故事了。
這時,讓我們再回頭想想那將農地全部徵收,作為產業、商業用地的璞玉計畫,無奈之情,溢於言表。
後記
在訪談後的一陣子,開始了全國各鄉鎮的地區稻米競賽,東海里即拿下了竹北區的第一名。再次令人感受到,在工業發展與農業改革之間,無限的複雜情緒。
特別參考各國立大學逐錄竹北的報導: 039刊目錄(3/14/2011)竹北特刊
它的一缺點是”放過”清華大學…..
---敬禮 !!!!
關於意識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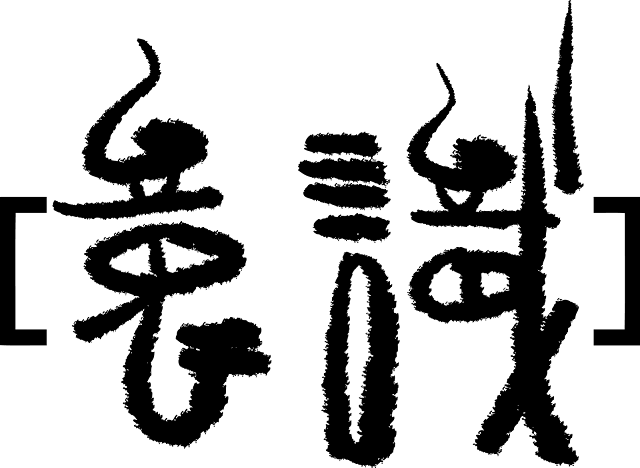
- 台大意識報,議事在台大
- 意識報(The NTU Consciousness)是一份台大的校園刊物,每期20頁、雙週出刊、發行量2000。於台大活大、總圖、誠品、唐山書店等報點外供人免費取閱。內 容包括校園議題、校園政策評論、社會議題、教育議題、台大校史、人物專訪等。稟持著批判反省的精神,懷抱著服務校園的熱忱,意識報從周遭的生活關心起,進 而思考台大學生參與公共事務的各種可能性。
封面繪圖:黃韻玲
大學的圈地運動:瓜分竹北
主編的話◎社工二 董昱
關於竹北:不可不知的幾件事
竹北徵收大事回顧◎ 台大意識報社整理
相關地點的照片與簡介◎ 台大意識報社整理
區段徵收的創始者 ──竹北的開發◎ 陳冠宇(台大大陸社)
實際走訪、深入報導
定位不明的台大竹北分部◎ 政治三 李芃萱、化工二 曾稚驊
沒有結果的生醫園區◎ 外文二 賴昱安
不見人影的台科大竹北校區◎ 政治二 謝佳榮
交大的投資與擴張:竹北璞玉計畫◎ 人類四 李問
透視大學、政府、與財團發展的原貌
區段徵收之後 被犧牲的小農與客家文化◎社工二 董昱
瓜分竹北:大學作為土地徵收的幫兇◎ 人類四 李問
設立分校,真的划算嗎◎ 政治三 李芃萱
將農業與整體發展還給人民◎ 化工二 曾稚驊
當地居民投稿:璞玉究竟是誰的玉?◎ 謝明豪(東海里住戶,清大原子科學院院學士班學生)
本刊意識報是竹北特刊,我們帶著數不清的疑問,探尋台大竹北校區 的發展。
台大為何選擇竹北?為何要選擇一個距離總區那麼遠的地方建設新校區?
竹北校區要開什麼課?新竹縣政府與台大的關係究竟又如何?
新聞說的內容到底是真是假?在響噹噹的名稱和口號背後,是否隱藏著不可 告人的祕密?
除了台大之外,我們同時也遇上了交大和台科大的「擴充計畫」;各個大學分別在
竹北劃分自己的勢力地盤,宛如歐洲列強切割非洲一樣,使得原本的客家農村景觀,
變成一格格的大學「殖民地」。
意識報竹北特刊,揭開大學瓜分竹北的殘酷面紗。
↧
↧
市廛集 鹿橋歌未央
<李弘祺專欄>
臺大校友第88期雙月刊目錄
http://www.alum.ntu.edu.tw/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2013/07/no88-e887bae5a4a7e99b99e69c88e5888a-e69d8ee5bc98e7a5bae69599e68e88.pdf
Nelson I. Wu,吳訥孫 2008
.....對於美好東西的形容,似乎只剩下美不勝收和多采多姿兩句陳腐的濫調.....(鹿橋歌未央 臺北:臺灣商務2006 頁108)
鹿橋歌未央一書還有不少缺點 譬如說到21世紀了還不知道梁宗岱的消息(頁107) 不過它保持了一些還未成書的資訊
2009.3.8
我景仰的作家 鹿橋 晚年寫市廛集(台北:時報)
我只記得他也在哈佛大學之鎮置屋 必須到這文化匯聚處大隱
「市廛而不徵,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ㄔㄢˊ 解釋 古代城市中可供平民居住的宅地。說文解字:廛,二畝半也,
店鋪。禮記˙王制:市廛而不稅。鄭玄˙注:廛,市物邸舍,
2008
Nelson I. Wu,吳訥孫
樸月(編著)鹿橋歌未央,台灣:商務印書館,2006該書有第一手資料鹿橋,原名吳訥孫,英文名Nelson Ikon Wu(Ikon是他的小名音譯)。1919年6月9日生于北京,先後就學于燕京大學、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耶魯大學,1954年在耶魯大學取得美術史博士學 位;又先後在舊金山大學、耶魯大學、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執教。 鹿橋是一位“左手寫詩篇右手寫論文”的學者,集學術理性與文學感性于一身的作家;他不僅對中國藝術史的研究頗有建樹,還著有《未央歌》、《人子》、《懺情 書》《市廛集》等暢銷作品。 2002年3月19日鹿橋病逝于波士頓,享每83歲。
香港文學史家司馬長風先生在他的《中國新文學史》中 把鹿橋的《未央歌》看作抗日戰爭和戰後期間長篇小說的“四大巨峰”之一。另外三部是:巴金的《人間三部曲》、沈從文的《長河》、無名氏的《無名書》。而 《未央歌》“尤使人神往”,“讀來幾乎無一字不悅目、無一句不賞心”。當年,鹿橋是靠朋友找紙張,連鋼筆墨水都得加水調稀。為了躲警報,他的寫作多半是在 防空洞裏完成的。自1945年完成之後,由于戰爭等原因,這部作品分別于1959年和1967年才在香港自印千冊留百冊、臺灣版由商務印書館印行。
Chinese and Indian architecture: The city of man, the mountain of God, and the realm of the immortals (Great ages of world architecture)
by Nelson Ikon Wu (Author)
- Unknown Binding: 128 pages
- Publisher: Studio Vista (1968)
record.wustl.edu/2002/03-29-02/obit.html
Nelson I. Wu, professor emeritus, 82

By Liam Otten

Nelson Ikon Wu, Ph.D., an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scholar of Asian art and architecture, died Tuesday, March 19, 2002, of cancer at the Beth Israel Deaconess Medical Center in Brookline, Mass. He was 82.Wu, the Edward Mallinckrodt Distinguished University Professor Emeritus of the History of Art and Chinese Culture in Arts & Sciences, came to the University in 1965, becoming a key figure for the promotion of Asian art in St. Louis and, in 1971, a founder of the Asian Art Society. He was named professor emeritus in 1984.
Additionally, Wu was a best-selling author in China and Taiwan, writing under the pen name Lu Ch'iao. His novel Song Never to End (1958), about the friendships between four young people during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has sold more than 500,000 copies and in 1991 was voted most influential book of the 1950s by readers of the Taiwan-based newspaper China Times, the nation's largest daily.
"Nelson was an extremely charismatic figure with a large following on campus and in St. Louis," said Mark S. Weil, Ph.D., the E. Desmond Lee Professor for Collaboration in the Arts and director the Gallery of Art. "Every year around Christmas, he would give a lecture celebrating Pan-Asian spirituality that filled Steinberg Auditorium."
Born June 9, 1919, in Peking, Wu earned a bachelor's degree from the 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in Kunming in 1942 and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45. He attended 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in New York before earning both a master's and doctorate in art history from Yale University, in 1949 and 1954, respectively.
While at Yale, Wu met the former Mu-lien Hsueh, a Wellesley College graduate also born in Peking. The couple wed in 1951.
Wu taught at Yale, San Francisco State College and Koyoto University in Japan before coming to St. Louis.
His many honors include a Guggenheim Fellowship and a Fulbright Research Scholarship. In 1998, Washington University and the Saint Louis Art Museum inaugurated the annual Nelson I. Wu Lecture on Asian Art and Culture.
Wu is survived by Mu-lien and four children -- daughter Chao-ting and sons Chao-ming, Chao-ping and Chao-ying.
A small family service was held March 22. Memorial contributions may be made to the Washington University East Asian Library Nelson I. Wu Memorial Book Fund, Campus Box 1061.
看一下紀念他的第6屆講座之簡介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delivers Washington University's Nelson Wu Lecture
UCLA Art Historian speaks on "The Musical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A Presentation of Art and Music"
By Clayton DubeLothar von Falkenhausen, professor of art history, delivered the Sixth Annual Nelson I. Wu Memorial Lecture on Asian Art and Culture at Washington University on October 23, 2003. Prof. Von Falkenhausen's presentation focused on bronze bells and music making in China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Music was a critical part of state rituals in China. Different Chinese states had their own tonal systems and inscriptions on bells include markers indicating the tones they were capable of. This is a technological marvel, according to Prof. von Falkenhausen, as modern bell makers cannot be sure of a bell's tone prior to its completion. Among the most stunning of the surviving bells are those excavated in 1978 from the 4th century BCE tomb of Marquis Yi. It appears that musicians could use these bells to replicate the tonal systems of other states to honor visiting dignitaries. These bells were capable of two tones each, a capability that bell-makers seem to have lost in the ensuing century.
Prof. von Falkenhausen joined the UCLA faculty in 1993 after teaching at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UC Riverside. He earned his bachelor's degree at Bonn University and took his master's degree and doctora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Editor of the 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 Prof. von Falkenhausen's many publications include his 1993 book Suspended Music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nd articles and book chapters, including "The Waning of the Bronze Age: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Developments, 770-481 BC"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Since 1999, Prof. von Falkenhausen has served as the co-director of a UCLA-Beijing University archaeological project examining Yangzi River Basin salt works. During his visit to Washington University he made a seperate presentation on the current excavation underway along the Ganjing River, a Yangzi tributary.
Nelson Ikon Wu was a Washington University professor of art and architecture, known for his extensive work promoting interest in and understanding of Asian art. He's was a widely published writer of fiction under his Chinese pen name Lu Chiao. His novel Song Never to End was published in 1958 and sold more than half a million copies. Prof. Wu passed away in March, 2002 at age 82. The talk was co-sponsored by the St. Louis Art Museum.
This report draws upon information from Jenny Bazzetta's report in the spring 2004 newsletter of the East Asian Studies program at Washington University (distributed Nov. 2004) and the Washington University Record.
Asia Institute
Date Posted: 11/16/2004
↧
Against depression (Peter D. Kramer)
About the author (2005)
Peter D. Kramer, called "America's best-known psychiatrist" by the "New York Times", is the bestselling author of "Listening to Prozac", "Should You Leave?", "Spectacular Happiness", "Moments of Engagement", and, most recently, "Against Depression". He has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and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the "Washington Post", the "London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and "U.S. News & World Report", among other publications. Dr. Kramer lives and practices in Providence, Rhode Island, where he is a professor at Brown University.
Bibliographic information
Title Against depression
Author Peter D. Kramer
Publisher Viking, 2005
A decade ago, with his breakaway bestseller, Listening to Prozac, Peter Kramer revolutionized the way we think about antidepressants and the culture in which they are so widely used. Now, he returns with a profound and original look at the condition those medications treat ;depression. He asks: If we could eradicate depression so that no human being ever suffered it again, would we? Depression, linked in our culture to a long tradition of ;heroic melancholy, ; is often understood as ennobling ;a source of soulfulness and creativity. Tracing this belief from Aristotle to the Romantics to Picasso, and to present-day memoirs of mood disorder, Kramer suggests that the pervasiveness of the illness has distorted our sense of what it is to be human. There is nothing heroic about depression, Kramer argues, and he presents the latest scientific findings to support the fact that depression is a disease ;one that can have far-reaching health effects on its sufferers. Frank and unflinching, Against Depressionis a deeply felt, deeply moving book, grounded in time spent with the depressed. As his argument unfolds, Kramer becomes a crusader, the author of a compassionate polemic that is fiercely against depression and the devastation it causes. Like Listening to Prozac, Against Depressionwill offer hope to millions who suffer from depression ;and radically alter the debate on its treatment.
中文本取名如果梵谷不憂鬱 台北:張老師 2006
諸如第9章的章名都是"亂翻譯".....
Tate (Modern)美術館等都翻譯成"畫廊" 所以有"畫廊主人"等的翻譯.....
In Defense of Antidepressants
By PETERD. KRAMER
It's all the rage to question their effectiveness. But critics don't understand the research.
↧
夏目漱石《草枕》The Three-Cornered World : 茶文化講演会
夏目漱石《草枕》The Three-Cornered World : 茶文化講演会
2005.8.2
hc補充:夏目漱石(1867~1916)的作品《草枕》
在「康健月刊」中吳迎春談過夏目的吃之美學如:《草枕》
「烤魚中點綴了些許綠意,掀開碗蓋,
『你不喜歡嗎?』女侍問。 『不是,我會吃。』」
Simon U 有過這樣的介紹:「夏目漱石(Natsume Soseki 1867~1916).先生的書最有意思,《草枕》(
-----2013.8.25
《茶況》 夏目漱石の草枕題材 茶文化講演会
夏目漱石の「草枕」を題材に茶文化を語る小川教授=県立美術館で |
 |
県立美術館(静岡市駿河区)で24日、開催中の企画展「夏目漱石の美術世界」に合わせた茶文化講演会があった。夏目漱石の小説「草枕」を題材に、小川流煎茶家元の小川後楽京都造形芸術大教授が話した。
草枕には、青年がヒロインの父親をお茶で接待する場面がある。小川教授は、お茶を楽しむ空間のつくり方や道具、入れ方などが小川流煎茶に通じると指摘。漱石の漢詩などにもお茶が取り入れられていることを紹介し、漱石が茶の歴史、文化に詳しかったと説いた。
聴講した女性(67)は「漱石を茶の分野から見る貴重な機会で、本を読み返したくなった」と振り返った。
講演会は同大同窓会静岡支部が主催。海野正彦支部長は「静岡は茶生産が盛ん。文化面をもっともり立てたい」と話した。
企画展は25日まで開かれ、漱石の文学作品に登場する美術家の作品などを紹介している。
(松本利幸)
袋井・森 茶商は秋需要に向け消費地との情報交換を進めている。
掛川・小笠 産地問屋は秋需要をにらみ情報収集に力を入れている。
島田・金谷 茶商は秋需をにらみ情報収集を進めている。
川根 農家は天候を見ながら防除など茶園管理に努めている。
牧之原 農家は天候を見ながら防除など管理作業を進めている。
藤枝 産地問屋は蔵出し茶の販売準備をしている。
↧
牛津兒童文學百科/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Children's Literature/ Memories of a Bedtime Book Club/‘This Is Our House’ and ‘Once Upon a Northern Night’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Revised Edition
List price: $625.00
Sale price: $218.75
Save 65%
Children’s Books
A Sense of Place
‘This Is Our House’ and ‘Once Upon a Northern Night’

From "This Is Our House"
By SARAH HARRISON SMITH
Published: July 31, 2013
“What would it be like to stay in one place — to have your own bed, to ride your own bicycle?” a little girl named Anna wonders in Maxine Trottier’s 2011 picture book, “Migrant.” “Now that would be something.” Anna’s parents, who are migrant workers, move from one temporary home to another, and Anna imagines herself as a rabbit, living in abandoned burrows, or a bee, flitting from flower to flower. She is effectively homeless, and longs to live a settled life, “like a tree with roots sunk deeply into the earth.”
THIS IS OUR HOUSE
Written and illustrated by Hyewon Yum
40 pp. Frances Foster Books/Farrar, Straus & Giroux. $16.99. (Picture book; ages 3 to 8)
ONCE UPON A NORTHERN NIGHT
By Jean E. Pendziwol
Illustrated by Isabelle Arsenault
32 pp. Groundwood Books. $17.95. (Picture book; ages 4 to 7)
Related
Times Topic: Children's Books Reviews
From "Once Upon a Northern Night"
Home is also at the heart of two new picture books, “This Is Our House,” written and illustrated by Hyewon Yum, and “Once Upon a Northern Night,” written by Jean E. Pendziwol and illustrated by Isabelle Arsenault (whose artwork for Trottier’s “Migrant” earned a New York Times Best Illustrated award). Yum, originally from South Korea but now living in Brooklyn, sets her story in a city that could very well be New York, among a family of recent immigrants whose country of origin is never specified; Pendziwol and Arsenault, both Canadian, describe a cozy home in a wintry rural landscape.
On the title page of “This Is Our House,” a watercolor illustration shows a photograph of a little girl peeking her head around a front door, as if to welcome the reader inside. On the next, a framed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 again painted in watercolor — shows the house as it looked when her grandparents “arrived from far away with just two suitcases in hand.” In a pattern Yum continues throughout the book, the photo of the house is faced by a full-page scene. Here, the girl’s grandparents talk to each other as they stand outside their new home for the first time. The grandmother looks as if she is either shyly pleased, or hesitant. What is certain is her husband’s encouraging smile.
The photos reveal the public story, Yum seems to suggest, but there’s more to be told. And sure enough, the full-page scenes are intimate rather than posed: moments of action, and sometimes of crossness and tears; a little quarrel over the painting of the baby’s room on one side of the spread, a photo of the delighted expectant mother posing in a fully decorated room on the other. Mostly, the three generations who come to live in the house together display smiles and kind concern for one another.
Yum uses a springlike palette of yellow, pinks and greens, even when there’s snow on the sidewalk, and the little girl’s dark braids perfectly set off the fresh, happy colors. With time, the once-bare facade of the house comes to life with window boxes, flowering hedges and potted plants of the front stoop. The seasons cycle though the pictures as the family grows, including, at the end, a baby brother for the little narrator. She gives a slight twist to the book’s title in her final summary: “This is our home where my family lives.”
If family is central to Yum’s sense of home, Pendziwol and Arsenault enlarge that sense of a precious place to encompass a natural setting. “Once Upon a Northern Night” is spoken in a voice that could be that of an artist, a parent or even a deity. While a fair-haired boy sleeps “wrapped in a downy blanket,” the voice describes a scene in which wild animals roam across snowy fields as the northern lights play across the sky. Of the lights, the narrator says, “I tried to capture them but they were much too nimble, and only their rhythm reached you, deep in slumber, rising and falling with each sweet peaceful breath.”
Arsenault’s nighttime landscapes, created with gouache, ink, pencil and watercolor, add dramatic emphasis to the text; the wings of an owl with bright yellow and black eyes can scarcely fit on two pages; the russet tail and hind legs of a fox are lit by the moon while the rest of his body can be seen only faintly, in the shadows. Black and white dominate with occasional flashes of color — red apples on the bare branches of a tree, spiky green pine needles. The boy’s house appears only twice, but the overwhelming sense of the home is as a secure haven from which to view, or imagine, a mysterious and beautiful world. Older children may resist the slight sentimentality of Pendziwol’s text, but on a dark night a younger child is likely to revel in this book’s mixture of magic, wildlife and deep comfort.
Children's Books
The Children's Books Special Section features new books about grandparents, New York City traditions and books about holiday songs. Don't miss these features, the best illustrated books of 2011 and much more on nytimes.com/books.
1958年即由 Peter Opie 建議編寫此百科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Children's Literature
Description
Dig into almost 2,000 entries in this bulging resource, where Anne of Green Gables rubs elbows with the Lord of the Rings, Mother Goose with Punch and Judy,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with Christina Rossetti, and Maurice Sendak with Kate Greenaway. It's thorough -- and indispensable for teachers, librarians, and parents.Product Details
608 pages; 134 b/w drawings, & halftones;About the Author
Humphrey Carpenter's books include biographies of J. R. R. Tolkien, W. H. Auden, C. S. Lewis, Ezra Pound, and Benjamin Britten. He is the author of the popular Mr Majeika series of stories for children. Mari Prichard has worked as a broadcaster and teacher, and is now a local government education officer. She and Humphrey Carpenter were married in 1973 and have two daughters.Table of Contents
Preface, Acknowledgements, Note to the Reader, A-Z text.
![]()
閱讀
值得代代相傳的兒童讀物
2013年07月23日

Ed Koren
我把紅酒箱子和不透明膠帶取了出來,因為我要開始打包孩子們珍藏的最好的圖畫書了。
我早就該打包了。他們現在一個13歲,另一個15歲,我們已經很多年沒給他們大聲朗誦圖書了。出於濃郁的懷舊情結,我們還保留着這最後一堆書。把它們挪到閣樓上應該不算什麼大事。但又的確是件大事。
過去,當我必須把自己的藏書打包起來時,感覺那些書就像我的護身符,具有強烈而私人的體驗。圖畫書不是這樣的。當你把這些四四方方、皺皺巴巴、沾着爆米花和黃油污漬的圖書收起來時,你面對的是整個家庭的集體記憶。
因為我和妻子曾給孩子們反覆朗讀過這些心愛的圖畫書——滑稽地念,筋疲力盡地念,偶爾是醉醺醺地念。故事裡的對白和畫面已經印到了我們腦子裡。在家庭共有的記憶里,它們和暑假、去醫院以及照顧硬紙箱里受傷的小鳥一樣不可磨滅。
我們每個人都記得這些優美、古怪、離奇的詩,難以忘懷。它們能讓人想起生活中最美好的一些事情——潮濕的頭髮,乾淨的睡衣,下班後的時光。這些書很有可能是我們四個人在同一時間一起閱讀的最後一批書了。我們美妙的晚間讀書俱樂部已經走完了它的歷程。
幸運的是,我們的讀書俱樂部有一位明星主持人。她的名字叫伊登·羅斯·利普森(Eden Ross Lipson)。
伊登是《紐約時報》書評欄目的一位資深童書編輯,她是這個領域的傳奇人物,2009年去世。我的孩子們還小的時候,我在書評欄目做編輯,我的辦公桌就在她旁邊,我真是太幸運了。
她有偉大的人格(記者Cokie Roberts在她的葬禮上致辭時這樣說)和偉大的觀點。她不會輕易給你的孩子們推薦圖書,除非她非常了解他們,並且非常了解你,後者幾乎和前者同樣重要。她需要質詢你,以此了解你的性格。
伊登在她編輯的《紐約時報最佳童書指南》(The New York Times Parent』s Guide to the Best Books for Children, 1988)中描述了這種即興詢問。她會用一長串的問題轟炸你:「多大的孩子?男孩女孩?住在哪兒?有兄弟姐妹嗎?是單親家庭嗎?有什麼特殊愛好嗎?是想要 一本可供朗讀的書 ,還是讓孩子自己看的書?」
這些只是開場白。這種詢問的強度就像心理治療。之後,你得坐下來。那時候,我還沒戒煙,所以我會到其中一間可以抽煙的休息室里緩緩神,那是在《紐約時報》位於西43大街的舊樓里。
伊登的名言之一是,只有經過一兩代人的考驗,才能判斷一本童書是否是經典之作。問題不在於你是否會給孩子們讀這本書,而在於他們是否會給自己的孩子們讀這同一本書,並一直傳承下去。
我和妻子克里(Cree)都有孩提時代非常喜歡的童書,我們迫不及待地想把這些書念給孩子們聽。但是伊登經常會塞給我一兩本新書。「瞧,」她說,「這位作者真的有一手。」或者:「德懷特(Dwight),我覺得你女兒終於可以讀這本書了。」其中有些書成了我們的珍藏圖書。
其中一本是《巨大的線球》(The Giant Ball of String, 2002),文圖作者是阿瑟·蓋澤特(Arthur Geisert)。我們差不多把這本書都翻破了。它是個俏皮的道德寓言故事,講述了關於愛、偷竊、欺詐與正義。它可以被拍成一部嚴肅的兒童復仇惡作劇,可以讓韋斯·安德森(Wes Anderson)來導演。
另一本叫《嬰兒們爬走的那一天》(The Day the Babies Crawled Away, 2003),作者是佩姬·拉特曼(Peggy Rathmann)。天知道為什麼某些圖畫書能像魚鉤一樣緊緊地抓住你的心。對我們來說,這本書就是這樣的。它的故事情節很簡單——一群嬰兒在集市上從父 母的身邊爬走,一個小男孩跟隨並搭救了他們。
可是這本書很漂亮,而且給人一種身臨其境的感覺。一切都很 明快,背景是傍晚霓虹初上的天空。其中有一些有趣的亮點,比如有一個嬰兒,你幾乎在每一幅畫里都能找到他在什麼地方倒掛着。孩子們喜歡仔細查看內容豐富的 圖畫,尋找意想不到的細節。我們的孩子們給這個古怪的小孩起了個綽號,叫「蝙蝠寶貝」。
伊登還給了我一本《愛潑薩蒙達》(Epossumondas, 2002),故事作者是科林·薩莉(Coleen Salley),插圖作者是珍妮特·史蒂文斯(Janet Stevens)。它是根據一個南方民間故事改編的,十分有趣。
我通常最後會把這個故事大聲念出來。我會用米克·賈格爾(Mick Jagger)演唱《眼神空靈》(Far Away Eyes)時模仿的南方口音來朗誦——我希望南方的朋友們不要介意我這麼做。這本書講的是一隻負鼠,「他是媽媽和阿姨眼中的小心肝」。
我們最喜愛的圖畫書中,也有些是我們自己發現的。
比如漢斯·德·比爾(Hans de Beer)的《小北極熊》(Little Polar Bear, 1987)。這本書詼諧而哀傷,我的孩子們快不用穿紙尿褲時,特別喜歡這本書。
還有尼爾·蓋曼(Neil Gaiman)和戴夫·麥基恩(Dave McKean)的《牆中狼》(The Wolves in the Walls, 2003)。這些狼特別喜歡玩鬧,就像拉夫·斯特德曼(Ralph Steadman)畫里或沃倫·澤馮(Warren Zevon)歌中的那些卑鄙、骯髒的毛毛怪。
看着他們嬉鬧或者遭到報應,能獲得極大的樂趣。小女孩的父母從來不相信她說的話,總是說:「要是狼從牆裡出來,那就全完了。」
馬克·艾倫·斯達馬提(Mark Alan Stamaty)1973年出版的精彩而超現實的圖畫書《誰需要甜甜圈》(Who Needs Donuts?)是我準備打包的另一本書。斯達馬提把書中所有空白的地方都畫上了超現實的、詼諧的細節圖。這本書在2003年由Alfred A. Knopf出版社再次出版,堪稱經典。
這本書我給孩子們至少讀了500遍。直到今天,我們每次開車經過「唐恩都樂」(Dunkin』 Donuts)甜甜圈店時,后座總有人會哀怨或者諷刺地念叨書中的那句話:「有了愛,誰還需要甜甜圈呢?」
然後就是《名叫新奧爾良的火車》(The Train They Call the City of New Orleans, 2003)。這本書的內容跟1970年史蒂夫·古德曼(Steve Goodman)創作的同名經典歌詞差不多,由邁克爾·麥柯迪 (Michael McCurdy)配上插圖。多好的主意啊。你肯定樂意向孩子們低聲吟唱。
孩子們還小的時候,我們不是只在睡覺前讀圖畫書。克里的最佳創意之一是「爆米花讀書派對」。它的操作步驟是這樣的:1) 把爆米花做上。2) 把你最喜歡的童書都拿出來。3) 大喊「爆米花讀書派對!」4) 盡量保證童書讀完的時候,爆米花正好做好。
我們給孩子們讀了很多經典作品。但是我有意跳過了《伊索寓言》、《格林童話》和《蘇斯博士》(Doctor Seuss)等經典作品。因為這些書不需要我的協助孩子們也能讀。
這些不那麼知名的圖書肯定能通過伊登的考驗。能使它們傳承下去,真是件令人開心的事。有一天我的孩子們將打開這些箱子,滿心歡喜,熱切地將這些書讀給自己的孩子們。
家庭最愛的圖畫書:
(按字母順序排序):
漢斯·德·比爾:《小北極熊》
湯米·狄波拉(Tomie De Paola):《騎士和火龍》(The Knight and the Dragon)
朱爾斯·菲弗(Jules Feiffer):《汪汪喬治》(Bark, George)
朱爾斯·菲弗:《我丟了我的熊》(I Lost My Bear)
尼爾·蓋曼和戴夫·麥基恩:《牆中狼》
阿瑟·蓋澤特:《巨大的線球》
史蒂夫·古德曼和邁克爾·麥柯迪:《名叫新奧爾良的火車》
羅素·霍本(Russell Hoban和莉蓮·霍本(Lillian Hoban):《弗朗西絲的麵包和果醬》(Bread and Jam for Frances)
蒙羅·利夫(Munro Leaf)和羅伯特·勞森(Robert Lawson):《費迪南德的故事》(The Story of Ferdinand)
阿斯特麗德·林德格倫(Astrid Lindgren)和哈拉爾德·維貝格(Harld Wiberg):《湯姆登和狐狸》(The Tomten and the Fox)
佩姬·拉特曼:《嬰兒們爬走的那一天》
科林·薩莉和珍妮特·史蒂文斯:《愛潑薩蒙達》
莫里斯·森達克(MAURICE SENDAK):《夜晚的廚房》(In the Night Kitchen)
馬克·艾倫·斯達馬提:《誰需要甜甜圈》
桑德拉·斯蒂恩(Sandra Steen),蘇珊·斯蒂恩(Susan Steen)和G·布萊恩·卡拉斯(G. Brian Karas):《洗車》(Car Wash)
Critic’s Notebook
Memories of a Bedtime Book Club
July 23, 2013
The wine boxes and masking tape are out, because I’ve begun to pack up the last, best books in my children’s picture book library.
This is an overdue task. They’re 13 and 15 now and we haven’t read aloud to them in years. We’ve kept this final stack at hand out of undiluted nostalgia. Moving it into the attic shouldn’t be a big deal. But it is.
In the past, when I’ve had to pack my personal library, what I’ve boxed are talismans of intense yet essentially private experience. Picture books aren’t like this. When you’re putting away these square, dog-eared, popcorn-butter-stained things, you’re confronting an entire cosmos of collective memory.
Because my wife and I so repeatedly read these favorite picture books aloud — comically, exhaustedly, occasionally inebriatedly — to our children, their words and images have worn grooves into our minds. They occupy places in our family’s shared consciousness as indelibly as do summer vacations, trips to the hospital or injured birds cared for in cardboard boxes.
They’re the fine, weird, uncanny poems we’ve each memorized and carry around in our heads. They’re evocative of some of life’s best things — wet hair, clean pajamas, the end of working days. They’re the last books the four of us are likely ever to read again at anything like the same moment. Our splendid nightly book club has ended its run.
Happily for us, our book club had its Oprah. Her name was Eden Ross Lipson.
Eden was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s longtime children’s book editor, a legend in her field, who died in 2009. When my kids were little, I worked as an editor at the Book Review, and I had the crazy good fortune to possess the desk next to hers.
She had a jumbo-size personality (the journalist Cokie Roberts spoke at her funeral service) and jumbo-size opinions. She wouldn’t recommend a book for your children until she knew everything about them and, almost as importantly, everything about you. She’d need to grill you. Her interrogations were tests of character.
Eden described these improvised interviews in “The New York Times Parent’s Guide to the Best Books for Children,” (1988) a book she edited. She would bear down on you like this: “How old a child? A boy or a girl? Where does he or she live? Siblings? Intact family? Special interests? A book to read aloud, or a book for a child to read to herself?”
These were merely the opening salvos. It was as intense as psychotherapy. Afterward, you had to go and sit down. At the time, I still smoked, so I’d recuperate in one of the smoking lounges in the Times’s old building on West 43rd Street.
One of Eden’s dictums was that there was no way to tell if a new children’s classic had arrived until a generation or two had passed. The question isn’t whether you’ll read a book to your kids. It’s whether they will read the same book to their kids, and so on down the line.
My wife, Cree, and I both had favorite kids’ books from when we were young, books we couldn’t wait to read aloud to our children. But Eden was always there to slip me a new thing or two. “Here,” she’d say, “this writer has really got something.” Or: “Dwight, I think your daughter is finally ready for this.” Some of these became dearly prized.
One was “The Giant Ball of String” (2002), with text and art by Arthur Geisert. We’ve read this book until it’s nearly come apart. It’s a sly moral fable about love and theft and guile and justice. You can imagine it directed, as a kind of poker-faced kid’s revenge caper, by Wes Anderson.
Another was “The Day the Babies Crawled Away” (2003) by Peggy Rathmann. Who knows why certain picture books catch like fishhooks in your mind. For us, this was one of them. It’s barely got a story — it’s about a gaggle of babies who crawl away from their parents at a fair, and the young boy who follows and rescues them.
But it’s beautiful and enveloping. Everything is in crisp shadow against a neon late afternoon sky. There are funny grace notes, like the one baby who can be found hanging upside down somewhere in almost every drawing. Kids love to scan busy drawings for unpredictable detail. Ours nicknamed this weird kid “bat baby.”
Eden also gave me “Epossumondas” (2002), by Coleen Salley with illustrations by Janet Stevens. It’s based on a Southern folktale, and it’s hilarious.
I usually ended up reading this story aloud — I hope my Southern friends will forgive me for this — in the kind of faux-backwoods accent Mick Jagger employed in the song “Far Away Eyes.” The book’s about a possum who is “his mama’s and his auntie’s sweet little patootie.”
Other books, in our pile of favorites, we discovered on our own.
Hans de Beer’s “Little Polar Bear” (1987), for example, a witty, plaintive book my children adored when they were barely out of diapers.
And Neil Gaiman and Dave McKean’s “The Wolves in the Walls” (2003). These wolves are party animals, mean scuzzy fuzzballs out of a Ralph Steadman drawing or a Warren Zevon song.
It’s hideous joy to watch them frolic, and to witness them getting their comeuppance. The book’s refrain, uttered by a girl’s disbelieving mother and father, is this: “If the wolves come out of the walls, then it’s all over.”
Mark Alan Stamaty’s brilliant and surreal 1973 picture book, “Who Needs Donuts?”, is another I’m about to pack up. Mr. Stamaty tattoos every available surface in his books with surreal and witty detail. This book, reissued by Alfred A. Knopf in 2003, deserves to become a classic.
It’s one I’ve read to my children at least 500 times. To this day we can’t drive past a Dunkin’ Donuts without someone in the back seat plaintively or sarcastically mewling the book’s central question: “Who needs doughnuts, when you’ve got love?”
Then there’s “The Train They Call the City of New Orleans” (2003), which is little more than the lyrics to Steve Goodman’s classic 1970 song, illustrated by Michael McCurdy. What a good idea. You’ve got to be willing to whisper-sing to your kids to put this over.
We didn’t, when our kids were young, only read picture books at bedtime. One of Cree’s best inventions was the “popcorn reading party.” Here’s how you have a popcorn reading party: a) You make popcorn. b) You gather a pile of your best kids’ books. c) You yell, “popcorn reading party!” d) You try to work it out so that the kids books end at about the same time the popcorn does.
We read plenty of classics to our kids. But I’ve intentionally omitted Aesop, the Brothers Grimm, Doctor Seuss or other classic practitioners here. They don’t need my assistance.
It’s a treat to be able to pass along news of a few lesser-known books that I’m certain will pass the Eden Test. Someday my kids will open these boxes, gasp with delight, and eagerly read them to their own.
FAMILY FAVORITES
The list, in alphabetical order:
HANS DE BEER“Little Polar Bear”
TOMIE DE PAOLA“The Knight and the Dragon”
JULES FEIFFER“Bark, George”
JULES FEIFFER“I Lost My Bear”
NEIL GAIMAN AND DAVE MCKEAN“The Wolves in the Walls”
ARTHUR GEISERT“The Giant Ball of String”
STEVE GOODMAN AND MICHAEL MCCURDY“The Train They Call the City of New Orleans”
RUSSELL HOBAN AND LILLIAN HOBAN“Bread and Jam for Frances”
MUNRO LEAF AND ROBERT LAWSON“The Story of Ferdinand”
ASTRID LINDGREN AND HARALD WIBERG“The Tomten and the Fox”
PEGGY RATHMANN“The Day the Babies Crawled Away”
COLEEN SALLEY AND JANET STEVENS“Epossumondas”
MAURICE SENDAK“In the Night Kitchen”
MARK ALAN STAMATY“Who Needs Donuts?”
SANDRA STEEN, SUSAN STEEN AND G. BRIAN KARAS“Car Wash”
↧
↧
花園:談人之為人 Gardens: An Essay on the Human Condition by Robert Pogue Harrison / A Philosophy of Gardens 花園的哲理
Gardens: An Essay on the Human Condition by Robert Pogue Harrison 蘇薇星譯 北京三聯 2011 花園:談人之為人 不簡單的作者與譯者
人之為人,為什麼與花園息息相關?花園能否告訴我們為何“死亡是美的母親”,如詩人史蒂文斯所言?為什麼說我們其實生活在一個沒有花園的時代?為什麼說我 們正竭力創建一座史無前例的碩大伊甸園,與此同時卻將大地迅速變為荒原?《花園——談人之為人》作者羅伯特‧波格‧哈里森以其詩性的哲思引導讀者尋訪神話 傳說、宗教聖典、文學作品以及現實生活中的一座座花園,諸如荷馬史詩中的仙島樂園、伊壁鳩魯的弟子們深耕細作的菜園、《十日談》里的男女青年講故事的鄉村 花園、《瘋狂的羅蘭》中的幻景花園、樸質極簡的禪寺石庭、工致安詳的伊斯蘭園林、令園丁“走火入魔 ”、整日撥泥弄土的平凡的家庭小花園,還有無家可歸者在紐約街頭組建的臨時花園……《花園——談人之為人》邀請我們漫步這座座花園,體悟花園與園藝的內 蘊,由此在我們的心田和大地上重新開始耕種伏爾泰所說的“我們的花園”。
序
致謝
第一章 憂思乃天職
第二章 夏娃
第三章 人——奉獻于土地的園丁
第四章 無家而園
第五章 “我自己的花園”
第六章 柏拉圖的學園
第七章 伊壁鳩魯的花園學校
第八章 薄伽丘的花園故事
第九章 隱修之園、共和之園與王公之園
第十章 凡爾賽宮園林短評
第十一章 觀看——一門失落的藝術
第十二章 奇跡般的諧和
第十三章 兩種天堂︰伊斯蘭教與基督教之比較
第十四章 人,而不是破壞之徒
第十五章 時代的悖論
跋
附錄
一 《十日談》選摘喬瓦尼‧薄伽丘
二 《帕洛馬爾》選摘伊塔洛‧卡爾維諾
三 花園安德魯馬韋爾
四 伊斯蘭地毯花園簡介
注釋
文獻目錄
索引
譯後記
致謝
第一章 憂思乃天職
第二章 夏娃
第三章 人——奉獻于土地的園丁
第四章 無家而園
第五章 “我自己的花園”
第六章 柏拉圖的學園
第七章 伊壁鳩魯的花園學校
第八章 薄伽丘的花園故事
第九章 隱修之園、共和之園與王公之園
第十章 凡爾賽宮園林短評
第十一章 觀看——一門失落的藝術
第十二章 奇跡般的諧和
第十三章 兩種天堂︰伊斯蘭教與基督教之比較
第十四章 人,而不是破壞之徒
第十五章 時代的悖論
跋
附錄
一 《十日談》選摘喬瓦尼‧薄伽丘
二 《帕洛馬爾》選摘伊塔洛‧卡爾維諾
三 花園安德魯馬韋爾
四 伊斯蘭地毯花園簡介
注釋
文獻目錄
索引
譯後記
序
人類生來就無法凝視歷史的面龐,這一美杜莎之首遍布著瘋狂、死亡和無盡的苦難。這可不是我們的缺陷;恰恰相反,正因為不願听任歷史現實一展美杜莎的魔法, 將我們變成石塊,我們才有了得以承受人生的這一切︰我們的宗教熱忱、詩意想象、對理想之邦的夢幻;我們的道義追求、玄思冥想、對現實的審美幻化;我們對故 事的迷戀、對游戲競技的熱衷、徜徉大自然的歡欣。阿爾貝.加繆曾回憶道︰“苦難讓我無法相信陽光普照下、漫漫歷史中一切都那麼美好,陽光卻教我懂得歷史並 非一切。”(加繆,Lyrical and Critical Essays,第7頁)不妨補充一句,倘若歷史意味著一切,那我們只能癲狂而終。
在加繆看來,是陽光帶來了慰藉,而更普遍地說,在西方文化傳統中,供人躲避歷史的喧囂與狂躁的庇護聖所,當屬花園——無論實在的還是虛構的花園。本書的讀 者會發現,這一座座花園可能與我們相距迢遙,比如吉爾伽美什一度涉足的神仙之園,希臘傳說中的極樂之島,但丁筆下煉獄山巔的伊甸園;或許,這些園林就坐落 在凡俗城邦的邊緣,譬如柏拉圖的學園,伊壁鳩魯的花園學校,薄伽丘《十日談》里的別墅花園;也許,這些園圃竟展現于都會鬧市,一如巴黎的盧森堡公園,羅馬 的博爾蓋塞別墅園林,還有散布紐約街頭的“無家之園”。殊途同歸︰不論作為一種構想,還是作為由人所創的環境,花園即便不是天堂,也是一種理想的憩園。
盡管如此,由人所創的花園不論多麼封閉自足,也始終立足于歷史,哪怕只為抗拒驅動歷史的種種侵蝕生命的力量。伏爾泰,在《老實人》的結尾處寫道︰“我們應 當耕種我們的花園”(n faut cultiver notre jardin),要理解這句名言中花園的涵義,就不能將它孤立于小說背景中連綿不斷的戰亂、瘟疫和災荒。此處對“耕種”的強調至關重要。正因為我們生來就 被拋入歷史,才須耕種我們的花園。不朽的伊甸園無需栽培養育,它為上蒼所賜,本已盡善盡美。在我們眼中,人間座座花園仿佛在伊甸園後的世界里開啟了一扇扇 通往天堂的門戶,然而,這些園圃必須由我們自己來創建、維護和關照;這一事實足以證明,它們起源于人類失去樂園之後。沒有花園的歷史是一片不毛之地。脫離 了歷史的花園必然淪為多余。
曾給我們所在的這座凡生的伊甸園增色添彩的處處園林,最有力地體現了人類棲居大地的理由。每當歷史一展其破壞與毀滅之能,與之對抗是我們惟一的選擇,為的 是維持我們健全的神志,且不談健全的人性。我們不得不尋求治愈創傷、救贖生命的種種力量,讓它們在我們心中、在我們中間生長。“耕種我們的花園”意義就在 于此。伏爾泰的選詞——“我們的”——指向我們同屬共享的世界,這個紛繁世界借助人類的行動方才氣象萬千。“我們的花園”絕非一方逃避真實、純屬個人的私 密空間;“我們的花園”是大地上、內心深處或社群集體之中的那一塊土壤,在那里,救贖現實、使它不致自毀的文化精髓、倫理美德、公民道德正得到培養。這些 德性始終是我們的。
漫步此書,讀者將會穿行于多種不同的花園——有的來自歷史,有的立足現實生活,有的屬于神話傳說或文學創意——但本書探討的每一處園林多多少少都是“我們 的花園”這一故事的一個篇章。假如歷史終究在于破壞和培養這兩種力量之間驚人的、不間斷的、無止境的抗衡,那麼本書行將加入後者的奮爭。為此,它力求分擔 園丁的天職——憂思。
在加繆看來,是陽光帶來了慰藉,而更普遍地說,在西方文化傳統中,供人躲避歷史的喧囂與狂躁的庇護聖所,當屬花園——無論實在的還是虛構的花園。本書的讀 者會發現,這一座座花園可能與我們相距迢遙,比如吉爾伽美什一度涉足的神仙之園,希臘傳說中的極樂之島,但丁筆下煉獄山巔的伊甸園;或許,這些園林就坐落 在凡俗城邦的邊緣,譬如柏拉圖的學園,伊壁鳩魯的花園學校,薄伽丘《十日談》里的別墅花園;也許,這些園圃竟展現于都會鬧市,一如巴黎的盧森堡公園,羅馬 的博爾蓋塞別墅園林,還有散布紐約街頭的“無家之園”。殊途同歸︰不論作為一種構想,還是作為由人所創的環境,花園即便不是天堂,也是一種理想的憩園。
盡管如此,由人所創的花園不論多麼封閉自足,也始終立足于歷史,哪怕只為抗拒驅動歷史的種種侵蝕生命的力量。伏爾泰,在《老實人》的結尾處寫道︰“我們應 當耕種我們的花園”(n faut cultiver notre jardin),要理解這句名言中花園的涵義,就不能將它孤立于小說背景中連綿不斷的戰亂、瘟疫和災荒。此處對“耕種”的強調至關重要。正因為我們生來就 被拋入歷史,才須耕種我們的花園。不朽的伊甸園無需栽培養育,它為上蒼所賜,本已盡善盡美。在我們眼中,人間座座花園仿佛在伊甸園後的世界里開啟了一扇扇 通往天堂的門戶,然而,這些園圃必須由我們自己來創建、維護和關照;這一事實足以證明,它們起源于人類失去樂園之後。沒有花園的歷史是一片不毛之地。脫離 了歷史的花園必然淪為多余。
曾給我們所在的這座凡生的伊甸園增色添彩的處處園林,最有力地體現了人類棲居大地的理由。每當歷史一展其破壞與毀滅之能,與之對抗是我們惟一的選擇,為的 是維持我們健全的神志,且不談健全的人性。我們不得不尋求治愈創傷、救贖生命的種種力量,讓它們在我們心中、在我們中間生長。“耕種我們的花園”意義就在 于此。伏爾泰的選詞——“我們的”——指向我們同屬共享的世界,這個紛繁世界借助人類的行動方才氣象萬千。“我們的花園”絕非一方逃避真實、純屬個人的私 密空間;“我們的花園”是大地上、內心深處或社群集體之中的那一塊土壤,在那里,救贖現實、使它不致自毀的文化精髓、倫理美德、公民道德正得到培養。這些 德性始終是我們的。
漫步此書,讀者將會穿行于多種不同的花園——有的來自歷史,有的立足現實生活,有的屬于神話傳說或文學創意——但本書探討的每一處園林多多少少都是“我們 的花園”這一故事的一個篇章。假如歷史終究在于破壞和培養這兩種力量之間驚人的、不間斷的、無止境的抗衡,那麼本書行將加入後者的奮爭。為此,它力求分擔 園丁的天職——憂思。
Copyright notice: Excerpt from pages 1–13 of Gardens: An Essay on the Human Condition by Robert Pogue Harrison, publish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 An excerpt fromGardensAn Essay on the Human ConditionRobert Pogue HarrisonThe Vocation of CareFor millennia and throughout world cultures, our predecessors conceived of human happiness in its perfected state as a garden existence. It is impossible to say whether the first earthly paradises of the cultural imagination drew their inspiration from real, humanly cultivated gardens or whether they in fact inspired, at least in part, the art of gardening in its earliest aesthetic flourishes. Certainly there was no empirical precedent for the mineral “garden of the gods” in the Epic of Gilgamesh, described in these terms: “All round Gilgamesh stood bushes bearing gems… there was fruit of carnelian with the vine hanging from it, beautiful to look at; lapis lazuli leaves hung thick with fruit, sweet to see. For thorns and thistles there were haematite and rare stones, agate, and pearls from out of the sea” (The Epic of Gilgamesh, 100). In this oldest of literary works to have come down to us, there is not one but two fantastic gardens. Dilmun, or “the garden of the sun,” lies beyond the great mountains and bodies of water that surround the world of mortals. Here Utnapishtim enjoys the fruits of his exceptional existence. To him alone among humans have the gods granted everlasting life, and with it repose, peace, and harmony with nature. Gilgamesh succeeds in reaching that garden after a trying and desperate journey, only to be forced to return to the tragedies and cares of Uruk, his earthly city, for immortality is denied him.More precisely, immortal life is denied him. For immortality comes in several forms—fame, foundational acts, the enduring memorials of art and scripture—while unending life is the fabulous privilege of only a select few. Among the Greeks, Meneleus was granted this special exemption from death, with direct transport to the gardens of Elysium at the far end of the earth, where there is made the easiest life for mortals, For all her unmatched beauty, it seems that this was what the great fuss over Helen was really all about: whoever possessed her was destined for the Isles of the Blest rather than the gloom of Hades. Men have gone to war for less compelling reasons.for there is no snow, nor much winter there, nor is there ever rain, but always the stream of the Ocean sends up breezes of the West Wind blowing briskly for the refreshment of mortals. This, because Helen is yours and you [Meneleus] are son in law therefore to Zeus. —(Odyssey, 4.565û69) By comparison to the ghostly condition of the shades in Hades, a full-bodied existence in Elysium is enviable, to be sure, if only because happiness outside of the body is very difficult for human beings to imagine and impossible for them to desire. (One can desire deliverance from the body, and desire it ardently, but that is another matter.) Even the beatified souls in Dante’s Paradise anticipate with surplus of joy the resurrection of their flesh at the end of time. Their bliss is in fact imperfect until they recover in time what time has robbed them of: the bodily matter with which their personal identity and appearance were bound up. Until the restitution of their bodies at the end of time, the blessed in Dante’s heaven cannot properly recognize one another, which they long to do with their loved ones (in Paradiso 14 [61û66], Dante writes of two groups of saints he meets: “So ready and eager to cry ‘Amen’ / did one chorus and the other seem to me / that clearly they showed their desire for their dead bodies, / not just for themselves but for their mothers, / and fathers, and the others who were dear to them / before they became sempiternal flames”). In that respect all of us on Earth, insofar as we are in our body, are more blessed than the saints in Dante’s heaven. It is otherwise with the likes of Meneleus and Utnapishtim and Adam and Eve before the fall. The fantastic garden worlds of myth are places where the elect can possess the gift of their bodies without paying the price for the body’s passions, can enjoy the fruits of the earth without being touched by the death and disease that afflicts all things earthly, can soak up the sunlight so sorely missed by their colleagues in Hades without being scorched by its excess and intensity. For a very long time, this endless prolongation of bodily life in a gardenlike environment, protected from the tribulations of pain and mortality, was the ultimate image of the good life. Or was it? Certainly Meneleus is in no hurry to sail off to his islands in the stream. Telemachus finds him still reigning over his kingdom, a man among men. There is no doubt that Meneleus would opt for Elysium over Hades—any of us would—but would he gladly give up his worldly life prematurely for that garden existence? It seems not. Why? Because earthly paradises like Dilmun and Elysium offer ease and perpetual spring at the cost of an absolute isolation from the world of mortals—isolation from friends, family, city, and the ongoing story of human action and endeavor. Exile from both the private and public spheres of human interaction is a sorry condition, especially for a polis-loving people like the Greeks. It deprives one of both the cares and the consolations of mortal life, to which most of us are more attached than we may ever suspect. To go on living in such isolated gardens, human beings must either denature themselves like Utnapishtim, who is no longer fully human after so many centuries with no human companionship other than his wife, or else succumb to the melancholia that afflicts the inhabitants of Dante’s Elysian Fields in Limbo, where, as Virgil tells the pilgrim, sanza speme vivemo in disio, we live in desire without hope. As Thoreau puts it in Walden,“Be it life or death, we crave only reality” (61). If Meneleus took that craving for reality with him to Elysium, his everlasting life there is a mixed blessing indeed. But why are we posing hypothetical questions to Meneleus when we can consult Odysseus directly? Kalypso’s island, where Odysseus was marooned for several years, is in every respect a kind of Isle of the Blest in the far-flung reaches of the ocean: a flourishing green environment with fountains, vines, violets, and birds. Here is how Homer describes the scene, which is prototypical of many subsequent such idyllic scenes in Western literature: She was singing inside the cave with a sweet voice This is the enchanted place that Kalpyso invites Odysseus to share with her permanently, with an offer of immortality included in the bargain. But we know the story: cold to her offer, Odysseus spends all his days on the desolate seashore with his back to the earthly paradise, sulking, weeping, yearning for his homecoming to harsh and craggy Ithaca and his aging wife. Nothing can console him for his exile from “the land of his fathers” with its travails and responsibilities. Kalypso is incapable of stilling within his breast his desire to repossess the coordinates of his human identity, of which he is stripped on her garden island. Even the certainty that death awaits him after a few decades of life on Ithaca cannot persuade him to give up his desire to return to that very different, much more austere island.as she went up and down the loom and wove with a golden shuttle. There was a growth of grove around the cavern, flourishing, alder was there, and the black poplar, and fragrant cypress, and there were birds with spreading wings who made their nests in it, little owls, and hawks, and birds of the sea with long beaks who are like ravens, but all their work is on the sea water; and right about the hollow cavern extended a flourishing growth of vine that ripened with grape clusters. Next to it there were four fountains, and each of them ran shining water, each next to each, but turned to run in sundry directions; and round about there were meadows growing soft with parsley and violets, and even a god who came into that place would have admired what he saw, his heart delighted within him. —(5.63û74) What Odysseus longs for on Kalypso’s island—what keeps him in a state of exile there—is a life of care. More precisely, he longs for the world in which human care finds its fulfillment; in his case, that is the world of family, homeland, and genealogy. Care, which is bound to worldliness, does not know what to do with itself in a worldless garden in the middle of the ocean. It is the alienated core of care in his human heart that sends Odysseus to the shore every morning and keeps him out of place in the unreal environment of Kalypso’s island. “If you only knew in your own heart how many hardships / you were fated to undergo before getting back to your country, / you would stay here with me and be lord of this household and be an immortal” (5.206û9). But Kalypso is a goddess—a “shining goddess” at that—and she scarcely can understand the extent to which Odysseus, insofar as he is human, is held fast by care, despite or perhaps even because of the burdens that care imposes on him. If Homer’s Odysseus remains to this day an archetype of the mortal human, it is because of the way he is embraced by care in all its unyielding tenacity. An ancient parable has come down to us across the ages which speaks eloquently of the powerful hold that the goddess Cura has on human nature: Once when Care was crossing a river, she saw some clay; she thoughtfully took up a piece and began to shape it. While she was meditating on what she had made, Jupiter came by. Care asked him to give it spirit, and this he gladly granted. But when she wanted her name to be bestowed upon it, he forbade this, and demanded that it be given his name instead. While Care and Jupiter were disputing, Earth arose and desired that her own name be conferred on the creature, since she had furnished it with part of her body. They asked Saturn to be their arbiter, and he made the following decision, which seemed a just one: “Since you, Jupiter, have given its spirit, you shall receive that spirit at its death; and since you, Earth, have given its body, you shall receive its body. But since Care first shaped this creature, she shall possess it as long as it lives. And because there is now a dispute among you as to its name, let it be called homo, for it is made out of humus (earth).” Until such time as Jupiter receives its spirit and Earth its body, the ensouled matter of homo belongs to Cura, who “holds” him for as long as he lives (Cura teneat, quamdiu vixerit). If Odysseus is a poetic character for Care’s hold on humans, we can understand why he cannot lie easily in Kalypso’s arms. Another less joyful goddess than Kalypso already has her claims on him, calling him back to a land plowed, cultivated, and cared for by his fathers and forefathers. Given that Cura formed homo out of humus, it is only “natural” that her creature should direct his care primarily toward the earth from which his living substance derives. Thus it is above all the land of his fathers—as Homer repeats on several occasions—that calls Odysseus back to Ithaca. We must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land not merely geographically but materially, as the soil cultivated by his ancestors and the earth in which their dead bodies are buried.Had Odysseus been forced to remain on Kalypso’s island for the rest of his endless days, and had he not lost his humanity in the process, he most likely would have taken to gardening, no matter how redundant such an activity might have been in that environment. For human beings like Odysseus, who are held fast by care, have an irrepressible need to devote themselves to something. A garden that comes into being through one’s own labor and tending efforts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fantastical gardens where things preexist spontaneously, offering themselves gratuitously for enjoyment. And if we could have seen Odysseus’s patch of cultivated ground from the air, it would have appeared to us as a kind of oasis—an oasis of care—in the landscape of Kalypso’s home world. For unlike earthly paradises, human-made gardens that are brought into and maintained in being by cultivation retain a signature of the human agency to which they owe their existence. Call it the mark of Cura. While care is a constant, interminable condition for human beings, specific human cares represent dilemmas or intrigues that are resolved in due time, the way the plots of stories are resolved in due time. Odysseus experiences the endless delays that keep him from returning home as so much wasted time—for it is only with his return home that the temporal process of resolution can resume its proper course. His story cannot go forward in Kalypso’s earthly paradise, for the latter is outside both world and time. Thus it represents a suspension of the action by which his present cares—which revolve around reclaiming his kingdom and household—work toward an outcome. No resolution is final, of course, and even death does not put an end to certain cares (as Odysseus learns when he talks to the shades of his dead companions in the land of the dead). Yet in general human beings experience time as the working out of one care after another. Here too we find a correlation between care and gardens. A humanly created garden comes into being in and through time. It is planned by the gardener in advance, then it is seeded or cultivated accordingly, and in due time it yields its fruits or intended gratifications. Meanwhile the gardener is beset by new cares day in and day out. For like a story, a garden has its own developing plot, as it were, whose intrigues keep the caretaker under more or less constant pressure. The true gardener is always “the constant gardener.” The account of the creation of humankind in the Cura fable has certain affinities with, but also marked differences from, the account in Genesis, where the Maker of heaven and earth created a naive, slow-witted Adam and put him in the Garden of Eden, presumably so that Adam could “keep” the garden, but more likely (judging from the evidence) to shield him from the reality of the world, as parents are sometimes wont to do with their children. If he had wanted to make Adam and Eve keepers of the garden, God should have created them as caretakers; instead he created them as beneficiaries, deprived of the commitment that drives a gardener to keep his or her garden. It would seem that it was precisely this overprotection on God’s part that caused Adam and Eve to find themselves completely defenseless when it came to the serpent’s blandishments. Despite God’s best intentions, it was a failure of foresight on his part (a failure of gardening, as it were) to think that Adam and Eve could become caretakers of Eden’s privileged environment when he, God, went to such lengths to make sure that his creatures had not a care in the world. Indeed, with what insouciance Adam and Eve performed the momentous act that gets them expelled from Eden! “And when the woman saw that the tree was good for food, and that it was pleasant to the eyes, and a tree to be desired to make one wise, she took of the fruit thereof, and did eat, and gave also unto her husband with her; and he did eat” (Genesis 3:6). It was not overbearing pride, nor irrepressible curiosity, nor rebellion against God, nor even the heady thrill of transgression which caused them to lose, in one mindless instant, their innocence. The act was committed without fear and trembling, without the dramas of temptation or fascination of the forbidden, in fact without any real motivation at all. It was out of sheer carelessness that they did it. And how could it have been otherwise, given that God had given them no occasion to acquire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The problem with Adam and Eve in the garden was not so much their will to disobedience as their casual, thoughtless, and childlike disposition. It was a disposition without resistance, as the serpent quickly discovered upon his first attempt to get Eve to eat the forbidden fruit. It was only after the fall that Adam acquired a measure of resiliency and character. In Eden, Adam was unburdened by worries but incapable of devotion. Everything was there for him (including his wife). After his exile, he was there for all things, for it was only by dedicating himself that he could render humanly inhabitable an environment that did not exist for his pleasure and that exacted from him his daily labor. Out of this extension of self into the world was born the love of something other than oneself (hence was born human culture as such). For all that it cost future humankind, the felix culpa of our mythic progenitors accomplished at least this much: it made life matter. For humans are fully human only when things matter. Nothing was at stake for Adam and Eve in the garden until suddenly, in one decisive moment of self-revelation, everything was at stake. Such were the garden’s impossible alternatives: live in moral oblivion within its limits or gain a sense of reality at the cost of being thrown out. But did we not pay a terrible price—toil, pain and death—for our humanization? That is exactly the wrong question to ask. The question rather is whether the gift of the Garden of Eden—for Eden was a gift—was wasted on us prior to the price we paid through our expulsion. As Yeats said of hearts: “Hearts are not had as gifts but hearts are earned / by those that are not entirely beautiful” (“Prayer for My Daughter,” in The Collected Poems of W. B. Yeats, 188). In Eden, Adam and Eve were altogether too beautiful, hence also heartless. They had to earn their human hearts outside of the garden, if only in order to learn what beauty is, as well as what a gift it is. Through Adam and Eve we lost a gift but earned a heart, and in many ways we are still earning our heart, just as we are still learning that most of what the earth offers—despite its claims on our labor—has the character of something freely given rather than aggressively acquired. Eden was a paradise for contemplation, but before Adam and Eve could know the quiet ecstasy of contemplation, they had to be thrown into the thick of the vita activa. The vita activa, if we adopt Hannah Arendt’s concept of it, consists of labor, work, and action. Labor is the endless and inglorious toil by which we secure our biological survival, symbolized by the sweat of Adam’s brow as he renders the earth fruitful, contending against blight, drought, and disaster. But biological survival alone does not make us human. What distinguishes us in our humanity is the fact that we inhabit relatively permanent worlds that precede our birth and outlast our death, binding the generations together in a historical continuum. These worlds, with their transgenerational things, houses, cities, institutions, and artworks, are brought into being by work. While labor secures our survival, work builds the worlds that make us historical. The historical world, in turn, serves as the stage for human action, the deeds and speech through which human beings realize their potential for freedom and affirm their dignity in the radiance of the public sphere. Without action, human work is meaningless and labor is fruitless. Action is the self-affirmation of the human before the witness of the gods and the judgment of one’s fellow humans. Whether one subscribes to Arendt’s threefold schematization or not, it is clear that a life of action, pervaded through and through by care, is what has always rendered human life meaningful. Only in the context of such meaningfulness could the experience of life acquire a depth and density denied to our primal ancestors in the garden. To put it differently: only our expulsion from Eden, and the fall into the vita activa that ensued from it, could make us fit for and worthy of the gift of life, to say nothing of the gift of Eden. Adam and Eve were not ready—they lacked the maturity—to become keepers of the garden. To become keepers they first would have to become gardeners. It was only by leaving the Garden of Eden behind that they could realize their potential to become cultivators and givers, instead of mere consumers and receivers. Regarding that potential, we must not forget that Adam, like homo in the Cura fable, was made out of clay, out of earth, out of humus. It’s doubtful whether any creature made of such matter could ever, in his deeper nature, be at home in a garden where everything is provided. Someone of Adam’s constitution cannot help but hear in the earth a call to self-realization through the activation of care. His need to engage the earth, to make it his place of habitation, if only by submitting himself to its laws—this need would explain why Adam’s sojourn in Eden was at bottom a form of exile and why the expulsion was a form of repatriation. Once Jupiter breathed spirit into the matter out of which homo was composed, it became a living human substance that was as spiritual in essence as it was material. In its humic unity it lent itself to cultivation, or more precisely to self-cultivation. That is why the human spirit, like the earth that gives homo his body, is a garden of sorts—not an Edenic garden handed over to us for our delectation but one that owes its fruits to the provisions of human care and solicitation. That is also why human culture in its manifold domestic, institutional, and poetic expressions owes its flowering to the seed of a fallen Adam. Immortal life with Kalypso or in Elysium or in the garden of the sun has its distinct appeal, to be sure, yet human beings hold nothing more dear than what they bring into being, or maintain in being, through their own cultivating efforts. This despite the fact that many among us still consider our expulsion from Eden a curse rather than a blessing. When Dante reaches the Garden of Eden at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of Purgatory, he brings his full humanity with him into that recovered earthly paradise, having gained entrance to it by way of a laborious moral self-discipline that took him down through the circles of hell and up the reformatory terraces of Purgatory. Nor does his journey reach its endpoint in Eden, for it continues up through the celestial spheres toward some other more exalted garden: the great celestial rose of the heavenly Empyrium. Yet never once during his journey does the poet-pilgrim lose or forfeit the human care in his heart. Even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Paradise, the fate of human history—what human beings make of it through their own devotion or dereliction—remains his paramount concern. In particular it is the fate of Italy, which Dante calls the “garden of the empire,” which dominates the poet’s concern throughout the poem. To speak of Italy as a garden that is being laid to waste through neglect and moral turpitude takes the garden out of Eden and puts it back onto a mortal earth, where gardens come into being through the tending of human care and where they are not immune from the ravages of winter, disease, decay, and death. If Dante is a quintessentially human poet, it is because the giardino dello ’mperio mattered more to him in the end than either Eden or the celestial Rose. If we are not able to keep our garden, if we are not able to take care of our mortal human world, heaven and salvation are vain. To affirm that the fall was a repatriation and a blessing is not to deny that there is an element of curse in the human condition. Care burdens us with many indignities. The tragedies that befall us (or that we inflict upon ourselves) are undeniably beyond all natural proportion. We have a seemingly infinite capacity for misery. Yet if the human race is cursed, it is not so much because we have been thrown into suffering and mortality, nor because we have a deeper capacity for suffering than other creatures, but rather because we take suffering and mortality to be confirmations of the curse rather than the preconditions of human self-realization. At the same time, we have a tendency to associate this putative curse with the earth, to see the earth as the matrix of pain, death, corruption, and tragedy rather than the matrix of life, growth, appearance, and form. It is no doubt a curse that we do not properly value what has been freely given as long as we are its daily beneficiaries. Achilles, who had a warrior’s contempt for life while he lived, must die and enter Hades before coming to realize that a slave living under the sun is more blessed than any lord of the dead. When Odysseus attempts to console him during his visit to the underworld, Achilles will have none of it: “O shining Odysseus,” he says, “never try to console me for dying. / I would rather follow the plow as thrall to another / man, one with no land allotted him and not much to live on, / than be a king over all the perished dead” (11.488û91). The slave is happier than the shade not because he is laboring under the sun but because he is under the sun, that is to say on the earth. To the dead Achilles, the former seems like a small price to pay for the latter (“I am no longer there under the light of the sun,” he declares regretfully [498]). That such knowledge almost invariably comes too late is part of care’s curse. Care engages and commits us, yet it also has a way of blinding us. Achilles’ eyes are open for a moment, but even in death they close quickly again when his passions are enflamed. In no time at all, while speaking to Odysseus, he imagines himself back in the world of the living not as a slave but as his former formidable and destructive self, killing his enemies and perpetuating the cycle of reciprocal violence: “[I] am not the man I used to be once, when in wide Troad / I killed the best of their people, fighting for the Argives. If only / for a little while I could come like that to the house of my father, / my force and invincible hands would terrify such men / as use force on him and keep him away from his rightful honors” (499û504). That our cares bind us so passionately to our living world, that they are so tenacious as to continue to torment us after death, and that they blind us to the everyday blessings we so sorely miss once we lose them—this suggests that there may be something incorrigible in our nature which no amount of self-cultivation will overcome or transfigure. It is impossible to know for sure, for the story of human care has not yet come to an end. |
以「鳶尾花」(Iris)為名的英國哲學家和小說家莫道格(Iris Murdock),一九九九年辭世前,也是花展常客。她曾說,「一個從沒有花和植物星球來的人,看到我們對花草,充滿如此狂愛的喜悅,一定認為我們瘋了!」【江靜玲】
花園的哲理
本書的翻譯也是問題多多
引用許多作家 不過都不附原文
譬如說 H. Hesse 中國通譯 "黑塞" 而本書為"海塞" 接著是"海賽"
eudaimonic (p.12) 和 eudaimonia (p.186) 後者詳說
Table of Contents
1.Taking Gardens Seriously
2.Art or Nature?
3.Art-and-Nature
4.Gardens, People, and Practices
5.Gardens and the Good Life
6.The Meaning of Gardens
7.The Garden as Epiphany
8.Conclusion: The Garden's Distinction
A Philosophy of Gardens
ISBN13: 9780199290345ISBN10: 0199290342Hardback, 184 pages
Also available:
PaperbackMar 2006, In Stock
Price:
$45.00 (06)Description
Why do gardens matter so much and mean so much to people? That is the intriguing question to which David Cooper seeks an answer in this book. Given the enthusiasm for gardens in human civilization ancient and modern, Eastern and Western, it is surprising that the question has been so long neglected by modern philosophy. Now at last there is a philosophy of gardens. David Cooper identifies garden appreciation as a special human phenomenon distinct from both from the appreciation of art and the appreciation of nature. He discusses the contribution of gardening and other garden-related pursuits to "the good life." And he distinguishes the many kinds of meanings that gardens may have, from their representation of nature to their spiritual significance. A Philosophy of Gardens will open up this subject to students and scholars of aesthetics, ethics, and 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and to anyone with a reflective interest in things horticultural.Reviews
"Cooper's thoughful and engaging book is indeed A Philosophy of Gardens -- his rather unique and stimulating way of conceptualizing how, carefully reflected upom, gardening practices and appreciation can engender an epiphany of sorts on the mysteries of existence."--Donald Crawford, Notre Dame Philosophical Reviews↧
Ex Libris:Confessions of a Common Reader
Ex Libris:Confessions of a Common Reader
This witty collection of essays recounts a lifelong love affair with books and language. For Fadiman, as for many passionate readers, the books she loves have become chapters in her own life story. Writing with remarkable grace, she revives the tradition of the well-crafted personal essay, moving easily from anecdotes about Coleridge and Orwell to tales of her own pathologically literary family. As someone who played at blocks with her father's 22-volume set of Trollope ("My Ancestral Castles") and who only really considered herself married when she and her husband had merged collections ("Marrying Libraries"), she is exquisitely well equipped to expand upon the art of inscriptions, the perverse pleasures of compulsive proof-reading, the allure of long words, and the satisfactions of reading out loud. There is even a foray into pure literary gluttony--Charles Lamb liked buttered muffin crumbs between the leaves, and Fadiman knows of more than one reader who literally consumes page corners. Perfectly balanced between humor and erudition, Ex Libris establishes Fadiman as one of our finest contemporary essayists.
Ex Libris: Confessions of a Common Reader - Google Books Result
books.google.com/books?isbn=1429929421
Anne Fadiman - 2011 - Literary Criticism
Or of my old editor Byron Dobell, who, when he was researching an article on the Grand Tour, once stayed up all night reading six volumes of Boswell's journals ... Anne Fadiman writes:
[J]ust as there is more than one way to love a person, so is there more than one way to love a book. [A chamberlain who was horrified when my brother left his book face down on his bedside table] believed in courtly love. A book's physical self was sacrosanct to her, its form inseparable from its content; her duty as a lover was Platonic adoration, a noble but doomed attempt to conserve forever the state of perfect chastity in which it had left the bookseller. The Fadiman family believed in carnal love. To us, a book's words were holy, but the paper, cloth, cardboard, glue, thread, and ink that contained them were a mere vessel, and it was no sacrilege to treat them as wantonly as desire and pragmatism dictated. Hard use was a sign not of disrespect but of intimacy.
Hilaire Belloc, a courtly lover, once wrote:
What would Belloc have thought of my father, who, in order to reduce the weight of the paperbacks he read on airplanes, tore off the chapters he had completed and threw them in the trash? What would he have thought of my husband, who reads in the sauna, where heat-fissioned pages drop like petals in a storm? What would he have thought (here I am making a brazen attempt to upgrade my family by association) of Thomas Jefferson, who chopped up a priceless 1572 first edition of Plutarch's works in Greek in order to interleave its page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r of my old editor Byron Dobell, who, when he was researching an article on the Grand Tour, once stayed up all night reading six volumes of Boswell's journals and, as he puts it, "sucked them like a giant mongoose"? Byron told me, "I didn't give a damn about the condition of those volumes. In order to get where I had to go, I underlined them, wrote in them, shredded them, dropped them, tore them to pieces, and did things to them that we can't discuss in public."
Byron loves books. Really, he does. . . .
*****
[J]ust as there is more than one way to love a person, so is there more than one way to love a book. [A chamberlain who was horrified when my brother left his book face down on his bedside table] believed in courtly love. A book's physical self was sacrosanct to her, its form inseparable from its content; her duty as a lover was Platonic adoration, a noble but doomed attempt to conserve forever the state of perfect chastity in which it had left the bookseller. The Fadiman family believed in carnal love. To us, a book's words were holy, but the paper, cloth, cardboard, glue, thread, and ink that contained them were a mere vessel, and it was no sacrilege to treat them as wantonly as desire and pragmatism dictated. Hard use was a sign not of disrespect but of intimacy.
Hilaire Belloc, a courtly lover, once wrote:
Child! do not throw this book about;
Refrain from the unholy pleasure
Of cutting all the pictures out!
Preserve it as your chiefest treasure.
What would Belloc have thought of my father, who, in order to reduce the weight of the paperbacks he read on airplanes, tore off the chapters he had completed and threw them in the trash? What would he have thought of my husband, who reads in the sauna, where heat-fissioned pages drop like petals in a storm? What would he have thought (here I am making a brazen attempt to upgrade my family by association) of Thomas Jefferson, who chopped up a priceless 1572 first edition of Plutarch's works in Greek in order to interleave its page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r of my old editor Byron Dobell, who, when he was researching an article on the Grand Tour, once stayed up all night reading six volumes of Boswell's journals and, as he puts it, "sucked them like a giant mongoose"? Byron told me, "I didn't give a damn about the condition of those volumes. In order to get where I had to go, I underlined them, wrote in them, shredded them, dropped them, tore them to pieces, and did things to them that we can't discuss in public."
Byron loves books. Really, he does. . . .
*****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is Thomas Hardy's sixth published novel.
↧
Theodor Reik 一些著作 包括 The Search Within 等
孟祥森﹙孟東籬﹚1937--2009
Wilhelm Reich
http://www.answers.com/topic/wilhelm-reich
Reik, Theodor(tā`ōdōr rīk), 1888–1969, American psychologist and author, b. Vienna, Ph.D. Univ. of Vienna, 1912. He was one of Sigmund Freud's earliest and most brilliant students; their association lasted from 1910 to 1938. In Europe, Reik conducted research and lectured at several psychoanalytic institutes before coming (1938) to the United States. He was naturalized in 1944. He founded (1948) the National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for Psychoanalysis. Among his many writings are From Thirty Years with Freud (tr. 1940), Listening with the Third Ear (1948, repr. 1972), The Secret Self (1952), The Search Within (1956, repr. 1968), Of Love and Lust (1957, repr. 1970), Myth and Guilt (1957, repr. 1970), The Compulsion to Confess (1959, repr. 1972), Creation of Woman (1960), The Temptation (1961), Voices from the Inaudible (1964), Curiosities of the Self (1965), and The Many Faces of Sex (1966).
1948 - Listening with the Third Ear: The inner experience of a psychoanalyst. New York: Grove Press.
Bibliography
See the autobiographical Fragments of a Great Confession (1949, repr. 1965).狄奧多.芮克(Theodor Reik)著《內在之聲:用第三隻耳朵聆聽》Listening with the Third Ear (1948).孟祥森譯.牧童出版 1979年 《內在之聲》The Search Within孟祥森(全)譯1991台北水牛出版社 二版二刷
賴克 《內心底探索》The Search Within : Confession of an Analyst 候平文譯 台北水牛出版社 1979 再版
Reik, Theodor (tā'ōdōr rīk) , 1888–1969, American psychologist and author, b. Vienna, Ph.D. Univ. of Vienna, 1912. He was one of Sigmund Freud's earliest and most brilliant students; their association lasted from 1910 to 1938. In Europe, Reik conducted research and lectured at several psychoanalytic institutes before coming (1938) to the United States. He was naturalized in 1944. He founded (1948) the National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for Psychoanalysis. Among his many writings are From Thirty Years with Freud (tr. 1940), Listening with the Third Ear (1948, repr. 1972), The Secret Self (1952), The Search Within (1956, repr. 1968), Of Love and Lust (1957, repr. 1970), Myth and Guilt (1957, repr. 1970), The Compulsion to Confess (1959, repr. 1972), Creation of Woman (1960), The Temptation (1961), Voices from the Inaudible (1964), Curiosities of the Self (1965), and The Many Faces of Sex (1966).
Bibliography
See the autobiographical Fragments of a Great Confession (1949, repr. 1965).
Reik's psychoanalytic studies include discussions of such writers as Beer-Hofmann, Flaubert, and Schnitzler as well as Shakespeare, Goethe, and Gustav Mahler, to name but a few. He had a unique way of communicating and his writing and conversational style was free associational. His autobiography is to be found in his many works. Among his better known are: Listening with the Third Ear (1948); the monumental Masochism in Modern Man (1949); Surprise and the Psychoanalyst (1935); his recollection of Freud, From Thirty Years with Freud (1940); an autobiographical study, Fragment of a Great Confession (1949); applied psychoanalysis of the Bible in Mystery on the Mountain (1958); anthropology in Ritual (1958); and sexuality in Of Love and Lust (1959), Creation of Woman (1960), and The Psychology of Sex Relations (1961); and music in The Haunting Melody (1960).
Toward the end of his life Reik, who grew a beard, resembled the older Freud and lived modestly, surrounded by photographs of Freud from childhood to old age. He died on December 31, 1969, after a long illness.
一個心理學家眼中的愛 A Psychologist Looks at Love
- 作者:Theodor Reik
- 原文作者:Theodor Reik
- 譯者:孟祥森
- 出版社:圓神
- 出版日期:1997年
譯 序
孟祥森
當我們想要了解愛的時候,必須有一個認知,就是愛是不可被了解的。愛和生命一樣,只能投入,而被了解。
愛和生命,是在「了解」的範圍之外的;它人禁止被了解,拒絕被了解。我們只能用「愛」、用「生活」去對待。
我們不能「了解」愛的核心是什麼,愛的原因是什麼。充其量,我們只能了解愛的運作和心理過程。
對愛的談論和探討,大概只能在這個範圍內,越此便「有說便錯」。
但在可說的範圍之內,仍有人說得好,有人說得不好。狄奧多.芮克便是說得好的一位,而且說得甚好。
狄奧多.芮克(Theodor Reik)是佛洛伊德的入室弟子,是一位深通人性的心理學家,也是心理學家中最有人文素養,最接近詩人氣質的一人。同時,他也是很具批評性、很不妥協的人。
他的著作深深探討人性種種幽深之處,絕不妥協,絕不苟且。但因深曉人性,所以雖嚴謹卻不嚴厲,雖犀利卻不傷人;融科學的探討與詩人的感性為一爐,讓人深思與玩味。
台灣對他的翻譯卻甚少見,據譯者所知,只有兩本。最早是水牛出版社的《內心底探索》(侯平文譯),其次便是譯者所譯的《內在之聲》(牧童出版社);兩本 都是好書,但兩者都已出版二十餘年,現在在坊間大概已難買到。(本書譯成之後得知陳蒼多先生曾譯芮克二書《性關係心理學》和《發現與驚奇》〔新雨〕,另陳 先生提及《歌德情史》亦有中譯。)
《一個心理學家眼中的愛》既深入又驚人,讓譯者自己對愛與慾有更真切的了解,是一個很好的鏡子來覺察自己。我相信對每位讀者都會有鏡子的功能。
唯一讓譯者不能消化的觀點是作者對愛情起源的看法,他認為愛情是越於對自己的不滿與對對方的羨慕、嫉妒與敵意。為了彌補自己的不滿,為了克服對對方的嫉 妒與敵意,內心產生強烈的反彈作用(reaction formation註),而將嫉妒與敵意轉化為愛,並與此對象認同合一。
當然,芮克說這嫉妒與敵意及其轉化過程都是在無意中進行的,因此我們察覺不到。
愛情發生之前,當事者自身的不安與不滿確實是我們自己可以察覺的,這正是《少年維特的煩惱》所描述在戀愛之前的心境;對方的美好之嚮往也是事實,對對方的美質之羨慕與嫉好也有或多或少的蹤跡,但說愛情是敵意之轉化,我卻認為並不符合我自己的感覺。
我的感覺是,對方讓你動心,你渴望跟對方的生命融合,那是一種生命對生命的渴望。我認為性與愛都有一種生命層次的根源,而不僅是生理和心理的現象。
除了這一點我跟芮克的觀點不太相同之外,這本書仍是讓我深深受益、深深享受的。所以,我還是譯了,希望你也讀到這本好書。 註:日譯「反動形成」,中文心理學辭典譯「反向行為」。譯者為求順口易懂,而在本書譯為「反譯」或「反彈作用」。
戀人的心

狄奧多‧芮克, Theodor Reik, 孟祥森 - 圓神出版社,2002-07-01 出版
9789576078132 - 最後更新 2008-10-14
有些書名或其副標題有所不同
Publications
- 1912 – Flaubert und seine "Versuchung des heiligen Antonius". Doctoral thesis, University of Vienna.
- 1923 – Der eigene und der fremde Gott. Neuausgabe: Der eigene und der fremde Gott: zur Psychoanalyse d. religiösen Entwicklung, Mit e. Vorw. z. Neuausg. von Alexander Mitscherlich,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5.
- 1925/1959 – The Compulsion to Confess. In J. Farrar (Ed) The compulsion to confess and the need for punishment. (pp. 176–356).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Cudahy.
- 1932/1959 – The Unknown Murderer. In J. Farrar (Ed) The compulsion to confess and the need for punishment. (pp. 3–173).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Cudahy.
- 1937 – Surprise and the Psycho-Analyst: On the Conjecture and Comprehension of Unconscious Process. New York: E. P. Dutton and Company.
- 1941 – Masochism In Modern Man. New York: Toronto, Farrar & Rinehart.
- 1944/1974 – A Psychologist Looks at Love. In M. Sherman (Ed.) Of Love and Lust. (pp. 1–194). New York: Jason Aronson.
- 1946 – Ritual: Four Psychoanalytic Studies". 1962 Grove Press edition.
- 1948 – Listening with the Third Ear: The inner experience of a psychoanalyst. New York: Grove Press.
- 1952 – The Secret Self.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Young.
- 1953 – The Haunting Melody: Psychoanalytic Experiences in Life and Music.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Young.
- 1957 – Myth and Guilt.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 1959 – Mystery on the Mountain: The Drama of the Sinai Revelation.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 1960 – The Creation of Woman: A Psychoanalytic Inquiry into the Myth of Eve.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 1961 – The Temptation.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 1962 – Jewish Wit. New York: Gamut Press.
- 1963 - The Need To Be Loved. New York: H Wolff.
- 1964 – Voices From the Inaudible: The Patients Speak.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Company.
REIK, THEODOR (1888–1970), psychoanalyst. Reik, who was born in Vienna, met *Freud in 1910 and received his training analysis from Karl *Abraham in Berlin. After World War I he worked as an analyst first in Vienna, and then in Berlin until he moved to The Hague in 1934. In 1938 he immigr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46 he was elected president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Psychoanalytic Psychology.
Reik wrote many psychoanalytic articles on literary and musical figures such as Flaubert and *Mahler, on clin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themes, and on psychological theory. Four of his best-known papers of the 1920s were collected in Das Ritual, psychoanalytische Studien (19282; Ritual, Psychoanalytic Studies, 1931). The first paper dealt with "couvade," the primitive custom in which the father of a newborn child lies in bed, the last two papers with *Kol Nidrei and the shofar. A series of papers on problems of crime – including the compulsion to confess, and Freud's view of capital punishment – were developed in Der unbekannte Moerder (1932; The Unknown Murderer, 1936), in which he sets forth as a major concept that unconscious guilt motivates the crime itself and also the criminal's need to be caught and punished. Reik held that an analyst's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may interfere with treatment and that the therapeutic relationship should be an "unconscious duet" between patient and analyst in which surprises to both parties provide important insights. He wrote about his new technique in Der Ueberraschte Psychologe (1935; Surprise and the Psychoanalyst, 1936), and Listening with the Third Ear (1948). In Aus Leiden Freuden (1940; Masochism in Modern Man, 1941) Reik stated his theory that masochistic suffering is basically a search for pleasure and, as in the case of the Christian martyrs, for final victory. He therefore regarded masochism and the associated death instinct as secondary rather than primary as seen by Freud.
Some of Reik's thought was iconoclastic. In Psychology of Sex Relations (1945) he rejected the classical psychoanalytic theory of the libido and some of the sexual concepts that go with it. Among his more than 50 books are the autobiographical From Thirty Years with Freud (1940), Fragment of a Great Confession (1949), and The Search Within (1956). His biblical tetralogy included The Creation of Woman (1960), and in 1962 he published Jewish Wit. In Pagan Rites in Judaism (1964) he endeavors to show that much of the pagan and prehistoric survives in the rites of Judaism as professed today.
BIBLIOGRAPHY:
R. Lindner (ed.), Explorations in Psychoanalysis (1953), essays in his honor (incl. bibl.); J.M. Natterson, in: F.G. Alexander, et al. (eds.), Psychoanalytic Pioneers (1966), 249–64, incl. bibl.; D.M. Kaplan, in: American Imago, 25 (Spring 1968) 52–58; A. Grinstein, Index of Psychoanalytic Writings, 3 (1958), 1620–32; 7 (1965), 3940–41 (bibl. of his works).
[Louis Miller]
-----這首在 The Search Within 站一席之地 翻譯本66-70 採用的英譯與Wikipedia的三種都有些差異
歌德的這首詩有多重的寓意,野玫瑰象徵著年輕的少女,她拒絕了少年的追求並保衛自己。少年摘采野玫瑰,意味著少年粗野地奪去了少女的貞潔,這在當時 的德國是一種侵犯的象徵。而少年是否會因此永遠的忍受著愛的折磨,是顯而易見的,他想自己強烈的愛喚起野玫瑰回報的愛,然而她的離去和堅持卻使少年心碎。
1770年,年輕的歌德在特拉斯堡結識了弗里德里柯·布里翁(Friederike Brion),回憶著那場難忘的邂逅,歌德改編了一首16世紀的詩歌,創作了這首憂傷的《野玫瑰》。
2008年台灣電影《海角七號》以野玫瑰作為串起整個故事的媒介[1]。
野玫瑰 曲:舒伯特 詞:哥德(周學普譯)
男孩看見野玫瑰 荒地上的野玫瑰
清早盛開真鮮美 急忙跑去近前看
愈看愈覺歡喜 玫瑰、玫瑰、紅玫瑰
荒地上的玫瑰
男孩說我要採你 荒地上的野玫瑰
玫瑰說我要刺你 使你常會想起我
不敢輕舉妄為 玫瑰、玫瑰、紅玫瑰
荒地上的玫瑰
男孩終於來折它 荒地上的野玫瑰
玫瑰刺他也不管 玫瑰叫著也不理
只好由他折取 玫瑰、玫瑰、紅玫瑰
荒地上的玫瑰
"Heidenröslein" or "Heideröslein" ("Rose on the Heath" or "Little Rose of the Field") is a poem by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published in 1799. It was written in 1771 during Goethe's stay in Strasbourg when he was in love with Friederike Brion, to whom the poem is addressed. The episode is the inspiration for Franz Lehár's 1928 operetta Friederike, which includes a setting of "Heidenröslein" by Lehár.
"Heidenröslein" tells of a young man's rejected love; the female is represented by a rose. There is a companion poem by Goethe, "Das Veilchen", in which the man is represented by a violet.
It has been set to music by a number of composers, most notably in 1815 by Franz Schubert as his D. 257. Schubert's setting is partially based on Pamina's and Papageno's duet "Könnte jeder brave Mann" from the end of act 1 of Mozart's The Magic Flute. There are also settings by Carl Friedrich Zelter and Heinrich Werner. The Neue Deutsche Härte band Rammstein used the lyrics in their 2005 song "Rosenrot". The Japanese singer Ringo Sheena covered the Schubert song on her 2002 album Utaite Myōri: Sono Ichi in the song "D. 257".
Text
Sah ein Knab' ein Röslein stehn, Röslein auf der Heiden, War so jung und morgenschön, Lief er schnell es nah zu sehn, Sah's mit vielen Freuden. Röslein, Röslein, Röslein rot, Röslein auf der Heiden. Knabe sprach: "Ich breche dich, Röslein auf der Heiden." Röslein sprach: "Ich steche dich, Dass du ewig denkst an mich, Und ich will's nicht leiden." Röslein, Röslein, Röslein rot, Röslein auf der Heiden. Und der wilde Knabe brach 's Röslein auf der Heiden. Röslein wehrte sich und stach, Half ihm doch kein Weh und Ach, Musst es eben leiden. Röslein, Röslein, Röslein rot, Röslein auf der Heiden. | Saw a boy a little rose, little red rose on the heath, young and lovely like the morning. So he ran to have a close look at it, and gladly did. Little rose, little rose, little red rose on the heath. Said the boy: I will pick you, my red rose on the heath! Said the rose: I will prick you and I won't stand it, and you won't forget me. Little rose, little rose, little red rose on the heath. And the rough boy picked the rose, little red rose on the heath, and the red rose fought and pricked, yet she cried and sighed in vain, and had to let it happen. Little rose, little rose, little red rose on the heath. | Once a boy saw a little rose standing, Little rose of the field, She was so young and beautiful, He dashed there quickly to see her near, Beholden with abundant joy, Little rose, little rose, little rose red, Little rose of the field. The boy then said: "I shall pick thee, Little rose of the field." The little rose said: "I shall stick thee, That you'll always think of me, And, I'll not want to suffer it." Little rose, little rose, little rose red, Little rose of the field. Still the rough boy picked the rose, Little rose of the field. The little rose fought thus and pricked, No prose of pain could help her, Alas, she must suffer it yet. Little rose, little rose, little rose red, Little rose of the field. | Once a boy a Rosebud spied, Heathrose fair and tender, All array'd in youthful pride,-- Quickly to the spot he hied, Ravished by her splendour. Rosebud, rosebud, rosebud red, Heathrose fair and tender! Said the boy, "I'll now pick thee, Heathrose fair and tender!" Said the rosebud, "I'll prick thee, So that thou'lt remember me, Ne'er will I surrender!" Rosebud, rosebud, rosebud red, Heathrose fair and tender! Now the cruel boy must pick Heathrose fair and tender; Rosebud did her best to prick,-- Vain 'twas 'gainst her fate to kick-- She must needs surrender. Rosebud, rosebud, rosebud red, Heathrose fair and tender! [1] |
References
↧
灌園先生日記 / 林獻堂遺著(含《環球遊記》)/林獻堂傳(黃富三)《Attabu 阿罩霧風雲》
◎歷史台灣內容節錄自莊永明先生著《台灣紀事(上)(下)》一書(時報出版社出版),著作權屬莊永明先生所有,非經同意請勿任意轉載。
日期:1956/9/8 林獻堂逝世,享年76歲
祇恐渾荊棘,徒傷雪玉清。
──林獻堂「菜頭」詩
林獻堂名朝琛,號灌園,以字行, 1881 年 11 月 1 日出生於阿罩霧庄(今台中縣霧峰鄉),父允卿,舉人出身,官至道台:他 7 歲啟蒙,一直潛心舊學,可說是儒家思想所薰陶的人物。
20 歲,這位「阿罩霧三少爺」就成為家族代言人,日人雖有意拉攏他,但林獻堂總虛與委蛇;1907 年,他旅日時,得晤梁啟超,聽了任公一番諍言,而啟迪其「非武裝抗日」的思想。
當代知識青年具視林獻堂為「精神領袖」,他亦樂於挺身而出領導大家以「法」、「理」與統治階級力爭,他與林呈祿等請求廢止禁錮台胞的「六三法」未果 後,繼在創辦台灣民報,散佈民族思想,以及「台灣議會設置運動」、「台灣文化協會」、「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等擔任重要角色,因他是「地主」雖有人譏以 他為「收租派社會主義者」,然林獻堂在台灣非武裝抗日運動所投入的精神與物質,自有其舉足輕重的地位,誠於 1941 年,他週甲大壽時,以一首感懷詩明志:「民權重自由,言論規以格,糾合諸同志,上書請變革,帝京冒風雪,歷訪名人宅,或為其愚惱,或視為叛逆,成敗一任天,犧牲何足惜,奔走三十年,此心徒自赤,問君何所得,所得雙鬢白。」台灣光復後,他被選為台灣省參議員、國民參政員,且任台灣省通志館(今台灣省文獻委員會)館長。由於他鍛而不舍策動台灣自治的努力,被尊為:「台灣 議會之父」;外國史家Johanna M. Meskill 且對他讚曰:「台灣第一公民、台灣自治運動的領袖及文化的保姆。」
林獻堂歸葬台灣,行式之日,萬人空巷;何應欽輓聯題曰:「概念論胥,勵圖匡復,扶持文化,鼓吹民族;卓犖平生,歲寒松柏,耆舊台員,永懷高躅。」
林獻堂傳略 (高志彬) 開啟
林獻堂先生年譜 (高志彬) 開啟
林獻堂先生追思錄 (林麗華) 開啟
 1941年(辛巳)1月30日,紀念林獻堂六十歲合影。 前右二葉榮鐘、右四傅錫祺、右五林獻堂、後右二莊遂性、右五莊幼岳。  1939-1940年偕諸友侍林獻堂遊日本箱根。 往《新民報》東京支社任務,攝於強羅。 立者左起陳虛谷、葉榮鐘、林獻堂。  昭和15年(1940年)10月20日,留東詩友會第六回例會紀念撮影。 前右一陳虛谷、右三林獻堂、右四蔡培火、後右四葉榮鐘。 林獻堂遺著 1960 2006海峽書局重印 包括詩集和20萬字的環球漫遊---1928.8.28--1931.10.3 台灣民報週刊聯載 1927第一點停靠廈門 就記載一位老婦因家產完全被政府無償徵收而憤死 下一站到汕頭 因當地戒嚴而取消停靠 *****
◎歷史台灣內容節錄自莊永明先生著《台灣紀事(上)(下)》一書(時報出版社出版),著作權屬莊永明先生所有,非經同意請勿任意轉載。*****
黃富三著 林獻堂傳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2006修定版 1949年 林獻堂先生遠走日本至死 日記;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台灣危邦;亂邦也' 光緒33年 1907丁未12月29 當年秋天粱先生與先生在奈良旅社巧遇 梁任公先生致徐佛蘇先生 希望他領導籌畫中的江漢公報--黨報和江和公學--法政大學 談到目標五萬圓 '此間豪商吳覲堂每年一萬元 尚有台灣林君者亦熱心故國崇拜吾黨 弟擬親往運動.....' 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 台北:世界書局 1958 頁263 光緒33年 1907丁未12月29 當年秋天粱先生與林獻堂先生在奈良旅社巧遇 梁任公先生致徐佛蘇先生 希望他領導籌畫中的江漢公報--黨報和江和公學--法政大學 談到目標五萬圓 '此間豪商吳覲堂每年一萬元 尚有台灣林君者亦熱心故國崇拜吾黨 弟擬親往運動.....' 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 台北:世界書局 1958 頁263 灌園先生日記 = The diary of Lin Hsien-tang / 林獻堂著; 許雪姬等註解 | |||||||||||||||||||||
臺北市 : 中央硏究院臺灣史硏究所籌備處, 民89- [2000- ]
林獻堂先生的〈灌園先生日記〉是台灣最珍貴的私人資料,誠如葉榮鐘先生所言,這部日記應該是全體台灣人民的。它起自1927年,止於1955年,中缺1928、1936年,前後長達27年,跨越日治、戰後兩個時代。 日記中除了家族歷史外,有豐富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活動的資料:尤其是以他為中心所展開的活動,如台灣文化協會、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一新會,故本日記不僅是林獻堂一生最重要的見證,也可補充官方資料的不足,史料價值極高。是對台灣史研究有興趣者最好的參考資料。 撰文 / 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 圖 / 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 (1881–1956),本名朝琛,諱大椿,號,臺中頂厝系,父林允卿為前清舉人。甲午之役,年方十五,奉父之命率全家四十餘口避難泉州,事平回臺。1898年與望族楊晏然之長女結婚。(參見圖1)1901年任區長,1911年為參事,1905年被授紳章。1921年任評議員,後因不滿評議會無,遂向日本帝國請願建設,賦與臺灣自治。同年與等人組織文化協會,任總理。以後成為顧問,再組臺灣聯盟,致力於;他又盡力於保存漢文化的工作,如加入,即使在日人統治後期仍不改其維護漢文之決心。戰後,任臺灣省參議會議員,後又任參政員、委員。退任後改任臺灣省通志館館長及臺灣省文獻會主任委員,也任。1949年他赴日後,即不再回臺,直至亡故。
《灌園先生日記》始於1927年,終於1955年,前後共29年,唯缺漏1928年、1936年,總計27年,均寫在各該年的「當用日記」上,每則三、五百字,筆跡工整,要言不煩。日記中對於女性的紀錄,包含婦女參與婦女親睦會、等活動的情況,以及對於女性解放纏足與接受教育的看法。圖2為在歐遊途中,參觀女王離宮,看到描繪中國風俗的中關於纏足與辮子的,遂於1927年11月3日的日記中寫下「其所畫中國各種方〔風〕俗雜亂無章,其中令人最不快者就是辮子與纏足,留一民族野蠻的污點於異國宮中,永久不能磨滅,斯為可恨耳」,表達出其視女性纏足為民族汙點的觀感。
此外,林獻堂對於女性的看法跳脫傳統的窠臼,主張兩性相互尊重,並鼓勵女性接受。他在1927年2月3日的日記(詳見圖3)即提及議題,他認為「若視彼(婦女)為人須尊重其人格,此則平等之大意」,也提及臺灣女性被視為嬌悍,源於未接受教育。
林獻堂也在日記中記載了,積極投入的女性。1927年2月5日的日記(詳見圖4),提及協會的常務委員,當選11人中包含唯一的女性黃細娥。該會共有組織、、宣傳、、、婦女六部,由黃細娥領導婦女部。黃細娥(洪朝宗妻),1908年生於臺北,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肄業;臺灣文化協會左傾後,擔任婦女部部長。女性於臺灣文化協會的活動,旨在透過通俗文化演講,喚起婦女自覺。
流轉年華—臺灣女性檔案百年特展歡迎您親自透過第一手歷史檔案,來瞭解過往女性經歷的生活及走過的道路。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為深化歷史研究,向來致力於蒐集散藏於各地,不分族群、不問身分、不論性別等的民間檔案。然而,千百年來人類歷史,無論中外,均由男性觀點書寫與詮釋,在滾滾歷史長河中,女性身影幾乎不得見諸於史冊;縱然得見,也是在父權社會的遊戲規則之下,驚鴻一瞥。本次展覽特以「流轉年華—臺灣女性檔案百年特展」,以女性史料為主題,精選臺史所檔案館館藏的臺灣女性資料,從傳統女性、命運轉折、展現自我三個面向,展示從清領到戰後,百年來臺灣女性從傳統宗祧、香火繼承的附屬品,到參與社會、活躍職場的歷程。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為深化歷史研究,向來致力於蒐集散藏於各地,不分族群、不問身分、不論性別等的民間檔案。然而,千百年來人類歷史,無論中外,均由男性觀點書寫與詮釋,在滾滾歷史長河中,女性身影幾乎不得見諸於史冊;縱然得見,也是在父權社會的遊戲規則之下,驚鴻一瞥。本次展覽特以「流轉年華—臺灣女性檔案百年特展」,以女性史料為主題,精選臺史所檔案館館藏的臺灣女性資料,從傳統女性、命運轉折、展現自我三個面向,展示從清領到戰後,百年來臺灣女性從傳統宗祧、香火繼承的附屬品,到參與社會、活躍職場的歷程。 本次展出的藏品,精選自臺史所多年來數位典藏成果,包括婚姻契書、人身買賣契約、個人日記、證件、公文、書信、圖像等數位化檔案。藉由數位典藏科技,不僅保存臺灣歷史檔案的多樣性;且能在彈指之間,以女性為主題,從不同視野,尋覓隱身在歷史長河中她的芳蹤。 有關特展的更多資訊請見:http://herhistory.ith.sinica.edu.tw相關關鍵字:女性 政治 日記 林獻堂 灌園先生 了解台灣典藏計畫阿罩霧風雲小檔案
「阿罩霧(Attabu,霧峰平埔族語的發音)」是一個位在台灣中央、雲霧繚繞的地方,「台灣五大家族」之一的霧峰林家,在這裡建立了與台灣近代史息息相關家族傳奇。 《阿 罩霧風雲》以1895年以前的霧峰林家的興衰史為軸,故事起點在清朝年間,隨成千上萬渡海抵台的移民林文察,為保護親族、延續血脈爭搶生存資源,不僅地方 械鬥頻繁,也在政治的風向裡,苦尋壯大家族基業與勢力的機會。清朝廷為解決內憂外患,延攬台灣阿罩霧剽悍的豪強,協助平定太平天國、戴潮春民變並參與中法 戰爭,林文察則因戰功顯赫,官位一路晉升,卻也引來猜忌與災禍。 眼見一個台灣在地的龐大家族,在每一個歷史的轉折裡大起大落,克紹箕裘的林 文察長子林朝棟,為家族出路被迫面臨價值的抉擇與賭注,不僅成為日後清法戰爭重要的角色之一,位在阿罩霧的林家,也成為近代台灣歷史中叱吒風雲的家族,堂 皇宅第的興建與衰頹,見證台灣歷史起迭。《阿罩霧風雲》透過一個家族的興衰震盪,結合細緻的考據與3D動畫等多樣手法呈現。 許明淳導演、李 崗監製,該劇以台灣紀錄片中較少見的「戲劇重現」手法,由《花岡二郎》蘇達與《金枝演社》副導演施冬麟擔任戲劇指導,《夜奔》尹昭德、歌手蔡振南旁白,另 有《色.戒》美術指導李寶琳、金馬獎最佳造型設計得主陳淑津、《後宮甄嬛傳》服裝陳同勛聯手呈現台灣歷史原貌。 李崗紀錄片《阿罩霧風雲》 重現台灣史詩故事
「對 台灣太好奇,因為接收的資訊太不完全,非常想要解密台灣以前是什麼樣子。」耗時5年,斥資千萬,對一部影片來說,實在不算為難,但是,在政治色彩壁壘分明 的台灣,以霧峰林家為題材,企圖藉由戲劇重現台灣史詩故事,「觀點」,成為李崗所帶領的團隊面臨最大的考驗,也是日後記錄片的處理過程中,最耗心思琢磨的 部分。 於是,《阿罩霧風雲》成為一部跨越與集結了紀錄片、電影、學術三界的人力物力,並以戲劇還原式完成的關於「霧峰林家」的紀錄片。李崗 表示,比較起其他知名的家族,「霧峰林家」最大的不同是它不止是商人世家,它更捲入了中國權力核心的爭鬥。它是清朝的正規武裝部隊,官位權勢曾到達一品, 每個影響台灣命運的重大事件,「霧峰林家」不但都深陷其中,而且它在每一個關鍵點家族所做出的抉擇,都發人深省且影響台灣深遠。 「我們付出 5年的時間去挖掘、研究、拚湊、重現『霧峰林家』,」在觀點的整合方面,李崗說,林家最好的一本文獻是一個美國學者50年前寫的,年代也是停留在1895 年,若以當年的淮軍與湘軍來看,一支在北部、一支在南部,一條濁水溪之隔,林家兩邊押寶。現在也一樣,從不同政黨觀點來看,國民黨不提林家,因為228第 一個抓的是林家的後人,民進黨也不提林家。 即便是學者也會有意識形態,藍綠學者都各有解讀,因此「看林家的歷史,藍的綠的,一個從南門、一 個從北門,都不完全,要從高點看全面。」這部紀錄片從前製資料蒐集與考證就找了5位研究員,即使觀點不同,但台灣學術能力很強,文辯再找證據,然後用最真 誠的心「掌鏡」,李崗說,「希望下一代絕對不能只從政黨或特定團體的眼光去接收歷史、要有求真及獨立思想的能力。」此外,「我們要有自己主體的話語權,如 果我們自己放棄,由別人去解釋,將來若給大陸作,台灣大家族的故事可能都會變成『喬家大院』了。」 李崗說,希望這部片能夠提供多元、客觀、與思考空間,以「霧峰林家」這個移民家族的生存史為主體儘量還原台灣歷史。 |
↧
↧
剑桥美国文学史(第七卷):散文作品1940-1990年Vladimir Nabokov: Life and Lolita - BBC Documentary
如果你大約看得懂此影片 又稍微懂得Nabokov作品
那麼剑桥美国文学史(第七卷):散文作品1940-1990年Vladimir Nabokov: Life ...介紹的Nabokov 就很有價值的.
BBC HD 2010 57:44
那麼剑桥美国文学史(第七卷):散文作品1940-1990年Vladimir Nabokov: Life ...介紹的Nabokov 就很有價值的.
剑桥美国文学史(第七卷):散文作品1940-1990年
↧
美日中 書業一瞥/The 25 Most Beautiful Public Libraries in the World
美國獨立書店數目略有增加 大書店連鎖多虧本.
To Stay Afloat, Bookstores Turn To Web Donors
By JULIE BOSMAN
To survive in a market dominated by Amazon, independent bookstores across the country have started using public financing to help them stay afloat.
西雅圖有史以來的最大地產之開發案厥為Amazon 公司總部之增建. 幾乎可改變整個城市的 風景
神戶百年書店關門
活況、震災…神戸見つめて1世紀 海文堂書店、来月閉店
  100年近い歴史を閉じる海文堂書店=神戸市中央区 100年近い歴史を閉じる海文堂書店=神戸市中央区 |
  階段の踊り場には、船のハンドルや大漁旗が飾られている=神戸市中央区の海文堂書店 階段の踊り場には、船のハンドルや大漁旗が飾られている=神戸市中央区の海文堂書店 |
  海事書が並ぶ2階の売り場に立つ岡田節夫社長(左)と福岡宏泰店長=神戸市中央区、諫山卓弥撮影 海事書が並ぶ2階の売り場に立つ岡田節夫社長(左)と福岡宏泰店長=神戸市中央区、諫山卓弥撮影 |
【石川達也】海に関する書籍を豊富に取りそろえ、港町・神戸とともに歩んだ「海文堂書店」(神戸市中央区)が9月末で閉店する。インターネット通販の波に押され、来年の創業100年を前に幕を下ろす。地域の顔ともいえる書店の閉店に、惜しむ声が相次ぐ。
海文堂は1914(大正3)年、船舶や港湾など海事書の専門出版社として開業。現在は、神戸市中心部の元町商店街に店を構える。海事書の品ぞろえは全国 屈指で、2階の売り場には数千冊が並ぶ。階段の踊り場には船の木製ハンドルや大漁旗。ポストカードなどのミナト・神戸関連のグッズも用意されている。
社長の岡田節夫さん(63)は、日本の海運業がにぎわっていた高度経済成長期のころを懐かしむ。「停泊船の船員が制服を着たまま海事書を買いに来ていたよ。船内での娯楽用の週刊誌や小説を箱に詰め、船によく運んだもんだ」
-----海文堂は1914(大正3)年、船舶や港湾など海事書の専門出版社として開業。現在は、神戸市中心部の元町商店街に店を構える。海事書の品ぞろえは全国 屈指で、2階の売り場には数千冊が並ぶ。階段の踊り場には船の木製ハンドルや大漁旗。ポストカードなどのミナト・神戸関連のグッズも用意されている。
社長の岡田節夫さん(63)は、日本の海運業がにぎわっていた高度経済成長期のころを懐かしむ。「停泊船の船員が制服を着たまま海事書を買いに来ていたよ。船内での娯楽用の週刊誌や小説を箱に詰め、船によく運んだもんだ」
中國人正在遠離讀書。據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公佈的2012年「第十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顯示,成年人1年的紙質圖書閱讀量平均為4.39本。未成年人的閱讀量明顯下降,14~17歲未成年人1年的課外圖書閱讀量為7.96本,與2011年的10.68本相比大幅減少。
天津社會科學院輿情研究所所長王來華指出,年輕人認為互聯網上存在各種各樣的信息,沒有必要閱讀紙質圖書。如果年輕人喜歡閱讀電子書也沒什麼問題,但據調查顯示,電子書終端的使用時間也在減少。
據開展過同類調查的日本全國學校圖書館協議會介紹,日本小學生1個月的紙質圖書閱讀量為10.5本(每年126本),中學生1個月的閱讀量為4.2本(每年50.4本)。日本小學生之所以會閱讀大量的圖書,估計是因為學校規定了在校的閱讀時間。
中國一直希望將出版等領域作為「文化產業」來培育,但長此以往市場將趨於萎縮。中國政府計劃制定閱讀促進條例,以提高圖書閱讀量。
↧
.Hegel: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黑格爾
Hegel: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Paperback] Peter Singer
Paperback: 152 pages
Publish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rst Edition edition (December 6, 2001)
這本書應有1982年版本 台灣的聯經出版1984有李日章的翻譯本. 黑格爾1985年二版
現在看近30年前的聯經版有些問題.
譬如說沒翻譯原書的索引以致翻譯有不一致處.
舉一例: the unhappy consciousness 在74-5頁都翻譯成憂煩意識
到96頁成為不快樂意識 (在英文索引有3處. 我還只找到2處)
↧













 線上預約
線上預約

 迴路轉的奇妙現象。我在武大時,沒能趕上錢穆先生講學的盛況。沒想到在編譯館這位置上,卻因「武聖岳飛事件」,讓我有機會與錢穆先生聯繫上。
迴路轉的奇妙現象。我在武大時,沒能趕上錢穆先生講學的盛況。沒想到在編譯館這位置上,卻因「武聖岳飛事件」,讓我有機會與錢穆先生聯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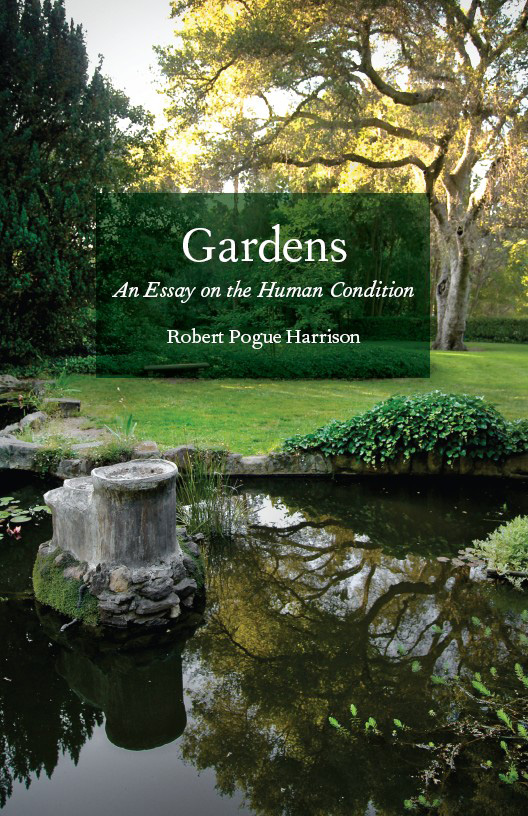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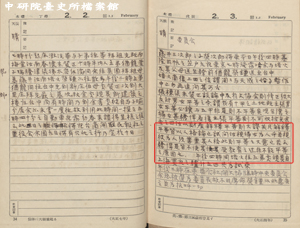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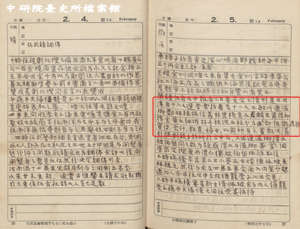
 太平洋の政治地理學的考察
太平洋の政治地理學的考察  南洋周邊並に濠亞の地理政治學 : 太平洋新秩序への理論的展開
南洋周邊並に濠亞の地理政治學 : 太平洋新秩序への理論的展開  紐育萬國博覽會を彩る見よ女性の活躍
紐育萬國博覽會を彩る見よ女性の活躍  アジヤロシアの政治組織
アジヤロシアの政治組織  臺灣日記特展移展至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臺灣日記特展移展至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台史所「流轉年華—臺灣女性檔案百年特展」邀請您來參觀!
台史所「流轉年華—臺灣女性檔案百年特展」邀請您來參觀!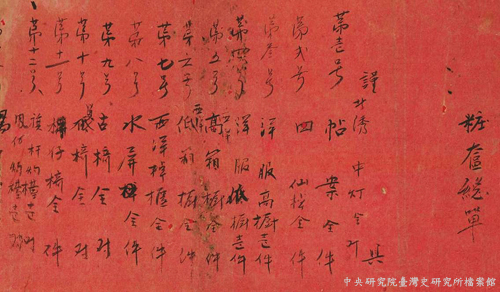 「待估而嫁」— 粧奩清單中的臺灣女性
「待估而嫁」— 粧奩清單中的臺灣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