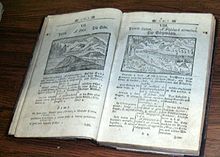《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2008
自 序──中國現代的文化危機與民族認同
曾國藩與「士大夫之學」
從中國史的觀點看毛澤東的歷史位置
打天下的光棍──毛澤東一生的三部曲
在榻上亂天下的毛澤東──讀《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
霸才無主始憐君──談周恩來
談魯迅與周作人
談郭沫若的古史研究
試論林語堂的海外著述
香港與中國學術研究──從理雅各和王韜的漢學合作說起
記艾理略與中國學社的緣起
「六四」過後的浮想
「六四」幽靈在中國大陸遊蕩──「六四」五週年紀念
和平演變與中國遠景
〈試論和平演進〉讀後
展望中國民主化的前景──從「國家」與「社會」的關係說起
中國文化危機及其思想史的背景
再論中國現代思想中的激進與保守──答姜義華先生
越過文化認同的危機──《錢穆與中國文化》序
人文研究與泛政治化
文化的病態與復健──劉笑敢《兩極化與分寸感》序
談費正清的最後一本書──《費正清論中國》中譯本序
中國史上政治分合的基本動力
合久必分,話三國大勢
自 序──中國現代的文化危機與民族認同
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中國的文化危機隨著時序的遷流而不斷加深,一直到今天還看不到脫出危機的跡象。不但如此,今天中國的文化危機反而更為深化了,因為在這個世紀末(用中國的說法是「末世」)的年代裡,世界各地,尤其是西方,都出現了極其嚴重的文化危機,而這些外面的危機現在又都與中國原有的危機合流了。最近我讀到大陸和臺灣新一代知識分子的文字,其中充滿了「後現代」、「後殖民」、「後結構」、「東方主義」、「解構」、「文化多元」種種最流行的時尚論說。世界的一切文化危機似乎都已由中國知識界全面承受下來了。
在這個後冷戰時代的世界,文化危機的論說方式雖然千奇百怪,但大體言之,只有兩種相反的傾向,一種是伴隨著多元化而來的相對主義,多元化本是現代文化的一個健康的發展。然而多元化一旦和極端的懷疑論和虛無論合流之後,便形成了各式各樣的相對主義,終至失去任何共同的標準,使人不再能判斷善惡,真偽或美醜。《莊子》「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相對主義論點,也是由「道術將為天下裂」的局勢造成的,不過與現代的情況相較,有如小巫見大巫而已。
相對主義所涵蘊的文化危機,如果發展到極限,便是墨子所謂「一人一義,十人十義」。這一危機在今天知識分子中表現得最為突出,但在後冷戰的時代,集體認同的新尋求則涵蘊著另一文化危機,這一論說方式大致可以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所憂慮的「文明的衝突」為代表。東歐和前蘇聯的極權體制崩解以後,以「無產階級革命」為號召的意識形態澈底破產了;以前長期受壓制的各民族文化開始復甦。同時,文化相對主義的興起也不斷向西方文化獨霸的意識挑戰,以致西方社會科學主流中的學人如杭廷頓也不得不承認世界上其他文化傳統──以宗教為中心──已構成對西方文化的威脅。這一多元化傾向的正面意義也是人所共見的。但是這一傾向發展到極端也會引生「返本論」("fundamentalism")的文化危機。「返本論」一般譯為「原教旨論」,因為這是宗教史上的常見現象。原教旨論者一方面以創教者的最早教義號召族群,另一方面則具有強烈的排他性。杭廷頓所說的「文明的衝突」主要便是以伊斯蘭教的「原教旨論」為對象。我改譯「原教旨」為「返本」則是因為這一現象並不限於宗教。不久以前美國奧克拉荷馬市的爆炸案已追溯到一種「密西根民兵」(Michigan Militia)的組織,其根據即在美國建國時期的原始理想。這一組織與宗教無關,但顯然也是一種fundamentalism。所以中國舊有的「返本」一詞恰好可以借用,因為「返本論」較之「原教旨論」無疑更適用於中國的儒家和道家。而且照最近中國大陸上所謂「易學」和「氣功」的流行情況來看,如果將來中國出現儒家、道家或儒道混合的「返本論」運動,那也是不足為異的。
總之,在後冷戰時代,源於西方的政治意識形態在中國大陸也同樣破產了。現在不但一部分知識分子表現出重新認識文化傳統的嚴肅要求,甚至官方也開始對中國文化,尤其是儒學,發生了興趣。前者可用近兩、三年大陸上出現的一股「國學」新潮為代表。這股新潮的性質並不簡單,暫時還無法分析得清楚。但是如果我們說:在「國學」新潮的後面,存在著一種文化認同的潛意識,大概尚不致於離題太遠。從這一角度看,這一新潮也未嘗不和「後殖民」、「後現代」、「東方主義」等來自西方的時尚論說,有其消息互通的一面。
至於後者──大陸官方對中國文化的興趣──則既見之於最近對臺灣的統戰文件,又見之於倡議「世界儒學聯合會」之類的組織,雖然在姿態上仍不免給人以「猶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覺。官方的動機自然不是學術性的,甚至也未必與文化認同有什麼關聯。但是我們可以推測,在原有的意識形態破產之後,中共官方似乎不得不轉向民族文化的傳統中去尋求統治權力的精神根據。
不可否認地,近幾年來,在一般中國人的意識中,中國文化傳統的位置確有所提昇。但文化危機則仍非短期內所能挽回。這裡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1949年以後,由於民間社會為政治暴力摧毀殆盡,中國傳統的文化價值已失去了存在的依據,許多基本價值不是遭到唾棄,便是受到歪曲。據最近的實地調查,不但仁義道德、慈孝、中庸、和諧、容忍等傳統德目失其效用,而且一切宗教信仰──包括敬祖先的意識──也在若存若亡之間。這種思想狀態遍及於各年齡層,其主要造因則在1949年以後,而以「文化大革命」為最大的關鍵。所以研究者沈痛地指出,三十年的毛澤東統治給中國人留下了一個史無前例的文化危機,舊的價值系統已殘破不堪,但新的價值系統卻並未出現。這是一種文化真空的狀態,前景如何則無人能加以預測。(詳見Godwin C. Chu and Yanan Ju, The Great Wall in Ruins,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in China,紐約州立大學出版社,1993)中國文化的實況如此,決不是空言所能濟事的。
其次,大陸學人的反傳統激情現在雖有開始退潮的跡象,但新的「國學」研究僅在萌芽階段,目前還不足以承擔闡明中國歷史和文化的任務。一般而言,人文研究和科學研究一樣,都需要有一個長期的研究傳統作為它的根據地。研究傳統越深厚,則取得的成績也越大。但所謂研究傳統並不是「定於一尊」,經久不變,而是一個不斷推陳出新的發展歷程,其中往往發生「典範式的革命」。事實上,「典範式的革命」之所以能夠出現,正是由於研究傳統的存在。西方人文研究在近二、三十年中變異迭出,但整個傳統卻因此而變得更為豐富。與此相反,中國的人文研究傳統自1949年以後便中斷了。以「國學」而言,二十世紀前半葉原已建立起深厚的基礎,一方面繼承了傳統經、史、子、集各部門的遺產,另一方面又發展了新的觀點與方法,而且研究的取向也是多元的。但是自五○年代起,大陸上的人文研究便已為粗暴的意識形態所全面籠罩,以往「國學」研究的業績被澈底否定了,甚至「國學」這個名詞也長期成為禁忌。在這種背景之下,今天要想復活「國學」研究真是談何容易!
最近一位俄國史學家分析蘇聯解體後史學研究所面臨的種種困難,對於我們瞭解中國大陸的人文現狀很有參考價值。他說,馬克思主義史學破產以後,俄國只剩下了一片「哲學的空白」("a philosophical void");現在許多人竟順手亂抓一切荒謬的東西來填補這片「空白」,從神秘主義、「旁門左道」("occultism"),到侵略性的沙文主義都大為流行。蘇維埃帝國的崩潰誘發了人們操縱歷史記憶的需要和思古的情緒,其結果是對歷史的建構流入隨心所欲而且往往出人意表的境地。思想的自由竟變成了不負責任的恣縱;人們在舊神話的殘骸上又編織了新神話。這位史學家也希望通過史學研究以重建俄國的文化價值,因此他特別強調「從內部研究歷史」的重要性,更強調史學家必須同時對他研究的對象和他所寄身的社會負起嚴肅的責任。(見Aaron I. Gurevich, The Doubl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istorian, Diogenes, No. 168, Vol. 42/4, Winter, 1994)我們以俄國的情況與八○年代「文化熱」以來的大陸相對照,便可以看出,中國也同樣存在著一片精神和思想的「空白」,中國知識人也同樣有「順手亂抓」一切東西來填補「空白」的傾向。他們不僅「抓」《周易》、特異功能、氣功、道家、儒家,而且更不分皂白地「抓」任何西方流行的「新奇可喜之論」。我相信「順手亂抓」的一個主要動力來自文化認同的新追尋,但尋求文化認同如不出之以嚴格的認知態度,則結局可能是加深,而不是消解文化的危機。
最後,大陸官方如果真有意假借中國文化或儒家以緣飾其政權的合法性,則對於中國文化或儒家而言,這將成為「死亡之吻」。自「中國特色」的提法出現以來,大陸官方越來越乞靈於民族主義的情緒。前兩年在人權問題上,他們附和新加坡李光耀的說法,強調民主與人權的內容因民族與文化而異。不但如此,他們甚至公然宣稱,中國人的「人權」首先便是「吃飽飯」。前面已提到,大陸官方不但開始重視儒家(這也是追隨李光耀的倡議,可看Foreign Affairs 1994年3、4月號李光耀的長篇訪談紀錄),而且正式用「五千年文化」的口號向臺灣進行「統戰」。把這許多跡象聚攏起來看,我們不能不疑心大陸官方確在採取一種偷梁換柱的新策略,想用「中國文化」或「儒家」來取代破了產的馬克思主義。一切證據都顯示:大陸官方決無絲毫放棄原有的意識形態的意願,他們仍然堅持「共產黨領導」為最高原則。對於「人權」、「民主」、「自由」等價值,他們更是一貫地深惡痛絕,那麼他們為什麼不直截了當地根據馬克思主義來否定「人權」,而必須隨著李光耀的曲調起舞,另提出「吃飽飯」為具有「中國特色」的「人權」觀念呢?(關於馬克思主義者必然否定人權的分析,可看Steven Lukes, Can a Marxist Believe in Human Rights一文,收在他的Moral Conflict and Politic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很顯然地,這是因為官方的意識形態已無人信從,而民族情緒和文化傳統在後冷戰時代又開始激動人心。這裡我們看到在文化多元化的趨勢下,中國文化正面臨著另一可能的厄運:它將為官方歪曲利用,變成極權統治的工具,以抗拒人權、民主、法治、自由等普遍性的現代價值。儒家思想恐怕更難逃此劫。如果真的不幸而言中,那麼袁世凱「祀孔」和《新青年》「打倒孔家店」的歷史未嘗不會重演,而中國人也將再一次失去平心靜氣理解自己文化傳統的契機。這正是我所憂慮的「死亡之吻」。
由以上所論,可見今天中國的文化危機確是處在一種十分微妙的階段:一方面充滿著「危險」,另一方面又呈現出新的「契機」。(據說這是美國甘迺地總統在字面上對中文「危機」一詞的理解;其實英文crisis也指一種關鍵性的時刻,有轉好或轉壞兩種可能的方向。)但我們必須認清:這一「危機」是世界性的,由於冷戰的終結而全面暴露了出來。這裡有一個特別值得注意的弔詭,今天世界上各民族追求文化認同並向西方的文化霸權挑戰,雖然出於十分複雜的背景,但理論上的根據卻仍然是由西方學人提供的。西方的人類學家、文化評論家、歷史學家、哲學家等,在最近二、三十年間頗多致疑於所謂「啟蒙心態」,因此不再奉直線社會進化論、極端實證論、現代化理論等為金科玉律。文化多元論便是在這一新思潮之下成長起來的。「多元文化論」("multiculturalism")目前在美國這個多元族群的社會已成為爭論的焦點。幾年前斯坦福大學的教授會以三十九票對四票取消了該校唯一的「西方文化」的共同課程,而代之以「文化、觀念與價值」的新課。在這門新課程中,歐洲的經典雖仍占有一個很高的比重,但其他非西方的作品──包括非洲、亞洲、美洲原住民以及婦女的述作──也構成重要的部分。這一破天荒的改變引起了極熱烈的論戰,戰火至今未熄。由此可知,美國學術界不但在理論上而且在實踐中,已承認社會上一切族群的文化都應該包括在大學的通識課程之內,西方文化必須從原來的獨霸位置上撤退下來。把這一原則從美國社會推廣到全世界,我們便不能不進一步承認:世界上每一民族所創造的文化都有其獨特的價值,因此也都同樣應該受到尊重。這便為世界各民族尋求文化認同的整體動向提供了理論的根據。今天中國的知識分子,無論在大陸、臺灣或海外,也都或多或少、或正或反地受到這一後冷戰思潮的衝擊。
文化多元論是不是必然否認不同文化之間還可以有共同標準呢?是不是必然涵蘊所有的文化都具有完全相等的價值,更無高下優劣之可言呢?不同文化之間是否可以互相開放,互相影響,終於達成一種基本的共同瞭解呢?今天我們雖然已較能認識到文化傳統的韌性,不再單純地把它化約為社會、經濟、或政治力量的依附品,但是我們是否應該走向文化決定論的另一極端呢?文化傳統(包括觀念和價值)在長期的歷史進程中不斷變動,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那麼所謂「文化認同」──無論是個人的還是集體的,究竟是什麼意思呢?以中國而言,是認同於「道術將為天下裂」時代的原始智慧呢?還是認同於西方文化傳入以前,甚至佛教傳入以前的儒、道等傳統呢?如果文化認同也包涵著「與古為新」或「與時俱新」的意思,那麼「認同」豈非主要變成了一種創造性的活動,並且不可避免地要容納外來的文化成分於其中?(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是1905年《國粹學報》第一期的〈例略〉說:「於泰西學術,其有新理特識足以證明中學者,皆從闡發。」這是因為當時,國粹學派認為「取外國之宜於我國而吾足以行焉者,亦國粹也」。引自胡逢祥〈論辛亥革命時期的國粹主義史學〉,《歷史研究》,1985年第五期,頁一五○)這些關於文化多元論的問題都不是容易解答的。西方學者近來的討論雖汗牛充棟,但也只能澄清正反兩派的論據,一時還無法消解基本的分歧。(參看Charles Taylor,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和Joyce Appleby, Lynn Hunt \& Margaret Jacab,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4, pp. 291-302)
文化認同在西方學術的討論仍在熱烈進行中;這種討論對於中國當前的文化危機會發生什麼影響是一個最值得注意的問題。今天無論是在中國大陸、臺灣、香港或海外,中國知識分子中都不乏倡導文化認同的人。(臺灣更出現了僅僅認同於臺灣本土的聲音。)但是我們細察他們的持論,便會發現他們很少從內部對於自己文化傳統的價值作出令人信服的新理解與新闡發。相反地,他們的主要論據是西方流行的一套又一套的「說詞」,包括前面所提到的「東方主義」、「後現代」、「後殖民」、「解構」之類。這些「說詞」並非不可引用,不過如果文化認同不是出於對自己族群的歷史、文化、傳統、價值等的深刻認識,而主要是為西方新興的理論所激動,或利用西方流行的「說詞」來支持某種特殊的政治立場,則這種「認同」是很脆弱的,是經不起嚴峻的考驗的。一旦西方的思想氣候改變了,或政治情況不同了,文化認同隨時可以轉化為文化自譴。無論如何,中國的文化認同論者似乎在思想上還是認同於西方的「文化霸權」。這真是一個十分奇妙的弔詭。
這一心理的矛盾自然不自今日始。遠在本世紀初,國粹學派便一方面痛斥當時中國學人「尊西人若帝天,視西籍如神聖」,而另一方面則奉達爾文、斯賓塞的社會進化論為無上的真理。他們事實上已為「五四」的啟蒙心態,包括貶低中國傳統打開了方便之門。我們可以說,國粹派在表面上認同於中國文化,在實質上則認同西方的主流思潮。因為自十九世紀下半葉始,達爾文和斯賓塞的理論恰恰在西方思想界占據著中心的地位。(可看Peter Gay, The Cultivation of Hatred, W. W. Norton Company, 1993, pp. 38-54)同樣地,今天不少中國知識分子轉向文化認同也是因為西方各種認同理論已在學術界奪得了相當大的一片領域,並從邊緣進入中心了。(參看Elazar Barkan, History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Ralph Cohen and Michael S. Roth, eds., History and Histories within the Human Sciences,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5, pp. 349-369)
這是我為什麼要說,中國的文化危機今天仍在持續之中,甚至更為深化了。一百年來,在中國文化界發生影響的知識分子,始終擺脫不掉「尊西人若帝天,視西籍如神聖」的心態。西方知識界稍有風吹草動,不用三、五年中國知識分子中便有人聞風而起。所以清末的「神聖」是達爾文、斯賓塞一派的社會進化論,「五四」時代是科學主義、實證主義,三、四○年代是馬克思主義,現在則是「東方主義」、解構主義之類。但是另一方面,中國知識分子對自己歷史、文化、傳統的認識則越來越疏遠,因為古典訓練在這一百年中是一個不斷墮退的過程。到了今天,很少人能夠離開某種西方的思維架構,而直接面對中國的文學、思想、歷史了;他們似乎只有通過西方這一家或那一家的理論才能闡明中國的經典。在三十年整理國故的時期,陳寅恪已慨嘆:「今日之談中國古代哲學者,大抵即談其今日自身之哲學者也。」現在我們恐怕更要下一轉語說:「今日之談中國文、史、哲諸學者,大抵即談西方某一流派之學者也。」如果這一「視西籍若神聖」的心態不能根本扭轉,中國人的文化認同勢將長期停留在認同西方的流行理論的階段。族群的自我認同儘管現在已成為一個相當普遍的世界現象,中國知識分子恐怕未必能把握住這一契機,而在中國的人文研究方面有積極的建樹。
今天大概不會有人抱殘守闕到完全拒斥西方文化的地步。上面提到的陳寅恪也強調中國「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在近代學人中,他是少數能自踐其信念的一個。他對西方和印度的經典都有直接的瞭解,但是他的心靈從來沒有為西方所征服。相反地,他卻能以不同文化為參照系統而發展出自己對於中國文化的認同。所以他的文化認同中已綜合了西方現代的價值,如學術獨立、思想自由、男女平等之類。這是讀過他的著作的人很容易發現的。然而他的基本認同在中國文化則是毫無可疑的。他確實沒有忘記「本來民族之地位」。我並不是說,陳寅恪的文化認同的方式具有典型性。事實上,文化認同對於個人而言都是如莊子所謂「鼠飲河,不過滿腹」而已,因此沒有兩個人的認同是完全一致的。我舉此一例,以見認同於中國文化與接受外來文化可以是相反相成的。個人如此,推之集體亦然。
薩依德(Edward Said)在1978年刊行的《東方主義》一書,對於文化認同的研究發生了深遠的影響。他嚴重地指責西方的「東方學家」的偏見,把「東方」描寫為西方的反面──
非理性、神秘、怪誕、淫亂。他認為這代表了西方帝國主義建立文化霸權的企圖,東方人必須起而反抗。這一說法的必然涵義之一自然是東方人必須擺脫西方人所強加的文化宰制,建立起自己的文化認同。但是薩依德的「東方」主要指中東的阿拉伯世界,並不包括中國。以中國而言,事實適得其反。自十七、八世紀以來,西方的「東方學家」對古典中國是頌揚遠過於貶斥。由於啟蒙時代的西方作家對中國描寫得太美好,以致造成研究啟蒙運動的專家之間的困惑。其中有人提出一種解釋,即當時啟蒙思想家為了批判西方文化,故意用中國為一種理想來鞭策自己,這就是所謂「打棍子理論」("beating-stick theory"):中國是西方人打自己的一根棍子。我們只要一讀《中國:歐洲的模範》(Louis S. Maverick, China: A Model for Europe, 1947)這本書,就可以明白其大概的情形了。這是中國人引用「東方主義」的說詞時首先必須注意的重要事實。另一應注意之點是薩依德雖然主張中東阿拉伯世界各族群建立自己的文化認同,以抵抗西方帝國主義的文化霸權,但他並不取狹隘的部落觀點。相反地,他認為文化認同絕不等於排斥一切「非我族類」的文化。在1993年刊行的《文化與帝國主義》一書中,他毫不含糊地指出,他一方面既不能接受美國某些白人保守派的文化霸權的觀點,以為「我們」只需要關心「我們自己經典」;另一方面也不能同情反霸權者的矯枉過正,例如說:阿拉伯人只讀阿拉伯的書,用阿拉伯的方法。他指出一個事實,在今天的世界,西方文化已傳布到一切地區,其中有些成分已變成世界性的了。(他的例子是:貝多芬的音樂已成為「人類遺產的一部分」。)總之,今天世界一切文化都是混合體,都雜有異質的、高度分殊的因子,沒有一個文化是單一而純粹的。美國如此,阿拉伯世界也是如此。但是在美國和阿拉伯世界,今天都不乏偏狹甚至多疑的民族主義者,他們往往教育子弟去特別尊崇「自己的」傳統,敵視一切「非我族類」的東西。這是一種沒有批判精神、沒有思維能力的原始衝動。薩依德的新著便是為了矯正這一流弊而寫成的。(見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Vintage Books Edition, 1994, Introduction, xxv-xxvi)
薩依德的立場其實和上引陳寅恪的說法不過重點不同而已。他是一方面要求阿拉伯世界的人「不忘其本來之民族地位」,但另一方面在對抗西方帝國主義的文化霸權時,又不應連已成為「人類遺產的一部分」的西方文化也一併拋棄了。他們兩人相同之處是在文化認同上強調折衷去取。文化認同折衷論自然比「全盤西化」或「全盤本土化」麻煩得多,更不及後兩種方式來得乾脆痛快。但二十世紀的中國經驗卻清楚地告訴我們:在社會大轉變時代,文化認同並沒有捷徑可循,無論是個人還是民族集體,都必須在長期嘗試和不斷調整的過程中才能找得到適當的方向。所謂「全盤西化」或「全盤本土化」都只能是少數人的主觀想像,可以成為理論上的「理想型」或「模式」,但在現實生活中決無可能出現。以常態情形而言,文化認同必然是在實際生活中逐漸發展和形成的,其間本土的成分和外來的成分互為作用,保守和創新也相反相成,折衷是無可避免的結局。即使是過去的「全盤西化」論者,儘管反對「折衷」,也未嘗不承認這一事實。例如1935年胡適在評論「本位文化」問題時便說:「我們肯往前看的人們,應該虛心接受這個科學工藝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後的精神文明,讓那個世界文化充分和我們的老文化自由接觸,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氣銳氣來打掉一點我們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氣。將來文化大變動的結晶品,當然是一個中國本位的文化,那是毫無可疑的。」(《胡適論學近著》,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頁五五六)可見「全盤西化」論者當時所提倡的不過是一個主觀的態度,並不是真的認為中國可以百分之百地變成西方。
「全盤西化」論者都是自由主義者,他們並不曾想到運用政治暴力來改變中國的文化狀態。因為他們有一個牢固的信念:「政府無論如何聖明,終是不配做文化的裁判官。」(胡適,上引文,頁五五五)因此儘管「全盤西化」是一個有嚴重語病的名詞,它的負面影響畢竟有限;具有獨立判斷能力的讀者不一定會接受他們的論斷。但「全盤西化」的偏激提法恐怕也對中國一部分知識分子發生了一種暗示作用,使他們感覺根據一種西方的模式來全面改造中國文化是可能的。1949年,特別是1966年以後,中國經歷了一個長期的文化破滅的過程。當時的口號是「不破不立」、「破舊立新」、「破字當頭」、「興無滅資」之類。所以「破」的是中國文化,「滅」的則是十九世紀末以來傳入中國的西方文化(所謂「資產階級文化」),而「立」與「興」的則是前蘇聯的斯大林體制,美其名曰「社會主義」。其實這才不折不扣地是一種「全盤西化」的革命。但它和三○年代自由主義者所提倡的「全盤西化」有兩點最重大的差異:第一、它以政治暴力為推行的方法,第二、它可以說是「反西方的西化」("anti-Western Westernization",此名詞借自Robert Bellah et al., The Good Societ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1, p. 250)。「反西方的西化」是一種矛盾的或「辯證的」統一;它對中國知識分子更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一方面「反西方」可以滿足反帝國主義的民族情緒,另一方面「西方化」以「科學的社會主義」的新面貌出現,又恰好符合「視西籍若神聖」的潛意識。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般魅力在非西方世界的特殊表現。(關於馬克思主義最能運用「科學規律」與「道德熱情」兩種相反的力量,使之互為支援,以激動西方一般的知識分子,可看Michael Polanyi, Personal Knowledge, Toward a Post-Critical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pp. 227-233)從這一角度看自由主義者的「全盤西化」和馬克思主義者的「反西方的西化」在思想內容上雖然南轅北轍,但在心理上仍不免有一脈相通之處。
無論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或馬克思主義者,他們的主要努力也是要為中國尋求一個集體的現代認同。認真地說,他們也不是拋棄了中國,一味「崇洋媚外」。這種常見的道德譴責不僅不公平,而且搔不著癢處。上面已引了胡適的話承認充分「西化」(或「世界化」)並不致導致「中國本位文化」的消滅。同樣的話在他的英文論著中更多,不必詳引了。即使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也常唱對中國文化應該「取其精華,棄其糟粕」之類的調子。他們的共同問題,在我看來,毋寧在於把中國文化看成了一個「化」的對象──「西化」、「蘇維埃化」、「世界化」或「現代化」。他們似乎認為只有在澈底被「化」了以後,中國文化才有可能重新發揮積極的作用。至於在整個「化」的過程中──這是一個相當長的過程──中國文化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些主動的貢獻?或者我們是不是也應該努力使中國文化積極地、正面地參預這個「化」的歷史進程?這些問題,從他們的觀點上看,是沒有意義的,因此也就沒有提出來過。我必須聲明,我在這裡僅僅指出自由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都把中國文化看作一個靜物,而不是動力,因此只能被動地接受改造,而不能主動地自我轉化。借用禪宗的話說,即是「心迷《法華》轉」,而不是「心悟轉《法華》」。但是兩派在這一點上雖持相同的觀點,並不能掩蓋他們在其他許多方面的根本差異。
現在我要對中國文化危機和文化認同的問題作一次總結的說明了。
一個世紀以來,文化危機和文化認同在中國相伴而生,並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互相激盪。中外史學家的論斷大致都以西方經濟勢力的入侵為現代中國文化危機的起源。所以「中國對西方挑戰的回應」成為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基本典範。這一典範最初起於中國史學界,但最近三、四十年來在美國發展得更成熟。根據這一典範,中國近代史始於鴉片戰爭,此後的每一階段也都是對西方帝國主義的「回應」。由於「回應」不當,中國的危機於是越陷越深。「回應」理論當然是建立在下面這個假定之上,即中國歷史自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便停滯不動。換句話說,中國史已無內在發展的動力,一切變動都起於被動地應付西方勢力的衝擊。試將這個一般性的歷史理論移用於文化危機和文化認同的問題上,我們便立刻可以看出「回應」說與上面所論證的「《法華》轉」說是完全一貫的。不過由於以前史學家過於看重經濟、制度、社會的因素,而視文化為寄附品,所以「回應」的觀點沒有大規模而系統性地運用在文化史的研究上面而已。
但是文化和歷史是不能截然分開的。因此在文化認同的問題上修正「《法華》轉」的觀點便必然要求在近代史研究上修正「回應」的典範。因為如果一部中國近代史的進程基本上只是對於西方衝擊的一系列的「回應」,而中國本身在此期間並沒有內在的發展,那麼中國文化當然也就只能成為被「化」的對象了。然而有趣得很,大約從七○年代開始,美國史學界便逐漸對中國近代史領域中的「回應」典範發生懷疑。許多人不約而同地發現中國近代史幾乎在每一方面──政治、經濟、社會、思想──都顯示出內在發展的軌跡,而不能完全解釋為對西方的「回應」。到八○年代中期,這一新的研究取向已表現得相當明顯,所以有人正式提出:「回應」說代表著以西方為中心的歷史觀,是西方霸權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上的實現,而新取向則預示著以中國為中心的觀點將越來越受到新一代史學家的重視了。但新觀點的出現也不是對「回應」說的全盤否定,因為西方勢力的入侵引起了近代中國的巨大動盪畢竟是無可否認的歷史事實。所以新觀點並不取消舊觀點,不過糾正後者的偏頗罷了。不但如此,如果史學家不能從內部觀察近代中國的發展,則中國為什麼以這樣或那樣的特殊方式「回應」西方的衝擊也無法得到比較完整而深刻的說明。(關於美國史學界對「回應」典範的批評以及新研究取向的興起,可看Paul A. Cohen的系統分析: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以中國為中心的近代史研究在美國不過剛剛起步,還需要通過大量的專題探討才能建立起它的新典範的穩定地位。但僅僅是這一轉變的本身已大有助於文化認同問題的認識。這一轉變也受到薩依德的「東方主義論」的某些影響,因此確和文化認同的問題消息相通。(參看Cohen前引書,頁一五○及頁二一九注二所引文獻)前面已提及,薩依德在《文化與帝國主義》新著中,也承認阿拉伯世界的文化認同不應該是排斥一切外來的──尤其是西方的──文化成分。在他看來,有些文化價值即使源於西方,但經過長時期的傳播已為非西方的民族所廣泛接受,因此便具有世界性了。薩依德先後見解的變遷值得重視。中國的讀者如果曾受到《東方主義》的啟發而傾向於一種近乎原教旨式的中國文化認同論,現在也有必要參考《文化與帝國主義》的論點而重新體認開放精神的現代意義。文化認同如此,史學研究也是如此。我十分重視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中國史各方面的內在動力,但並不否認西方文化對近代中國也有正面的、積極的影響。西方並不完全等於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掠奪。真正的關鍵在於我們尋求文化認同或從事史學研究的時候能不能把握住適當的分寸。
近一、二十年來西方多元文化觀點的興起,特別是冷戰終結以後,各民族文化在以前共產黨統治下各地區的迅速復活,使許多學者不能不重新估計民族和文化的力量。因此這四、五年來,西方討論民族認同和文化傳統的著作相當豐富。這些討論雖然沒有直接涉及中國,但對中國近百年來在文化危機與文化認同上所經歷的曲折道路卻有參考的價值。有些上面已隨文有所引證。現在為了總結全文,讓我再提綱挈要,略加申論。
第一、除了十九世紀晚期,馮桂芬至張之洞等人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那一短暫階段外,中國知識界面對西方文化越往後便越不敢相信自己的民族文化在尋求中國的現代認同中能發生積極的作用。但「中體西用」說是早期對西方認識不深的產物,自嚴復、胡禮垣等人駁斥以後,逐漸無人問津。二十世紀以來,無論是「國粹派」或「西化派」都或暗或明地以西方為模式而鑄造中國的現代認同。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籠罩之下,中國知識界接受了兩個觀念:一、所有社會都依循一定的進化階段而發展,如神權、君權、與民權。二、西方不但比中國超前至少一個階段,而且代表了社會發展的最完美的方式。(因為完美,故能超前。)受著這兩個觀念的支配,為中國尋求現代認同的人自然便義無反顧地「師法西方」了。雖然不同時期、不同流派之間對於如何「師法西方」以及在哪些地方「師法西方」,意見大有出入,但整體而論,他們都認定中國的現代認同以「認同西方」為其主要的部分。國粹派的方式是以現代西方的基本價值早已在古代中國出現(所謂「古已有之」);孫中山的方式早期是「迎頭趕上」西方,晚年則改為「以俄為師」(孫以1917後的俄國代表了新的西方);胡適的「西化」以美國為範式;毛澤東「向西方尋找真理」則歸宿於「反西方的西化」。總之,「西方」永遠是中國現代認同的核心部分;比較有影響力的中國知識分子似乎都不承認自己的文化傳統還能在民族的認同中發揮什麼積極的作用。這種情況甚至在抗日戰爭期間也沒有改變。舉一個最極端的例子:聞一多一方面說:「民族主義是西洋的產物,我們的所謂『古』裡,並沒有這東西」(《聞一多全集‧雜文》,頁一一),另一方面,更說「中國文化精神」有三個代表,即「儒家、道家、墨家」,順序為「偷兒、騙子、土匪」(同上,頁一九─二三)。民族主義在中國也成為澈底否定自己文化傳統的力量了。
但前面已指出,中國知識界的這些觀點大致上都是西方主流思潮的反映。(聞一多的「偷兒、騙子、土匪」論便直接來自H. G. Wells。)在本世紀六○年代以前,西方學人也自以為西方現代文化代表著「普遍性的價值」,一切落後的民族都只有依照西方的模式進行變革,才能進入「現代化」的階段。民族文化的傳統僅僅代表「特殊性的事實」,並沒有自我轉化的能力。甚至民族主義在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前半葉的西方思想中也不受重視,馬克思主義尤其是一個最顯著的例子。思想史家柏林(Isaiah Berlin)和人類學家格爾茲(Clifford Geertz)都要到七○年代初才真正認識到民族主義的強大生命力。(前者見Nationalism: Past Neglect and Present Power,收在Against the Current, Penguin Books, 1982;後者見After the Revolution: The Fate of Nationalism in the New States,收在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Basic Books, 1973)
這是中國現代文化認同陷入長期困境的一個主要根源:知識分子一心一意以「西方」(不同的「西方」)為範式,並借助西方的「新思想」、「新方法」來重建中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文化傳統不但沒有獲得其應有的位置,而且愈來愈被看作「現代化」的阻礙,「現代化」每受一次挫折,推動者對文化傳統的憎惡便隨之更深一層。這一心態的長期發展終於造成一種普遍的印象,即以為文化傳統可以一掃而光,然後在一張白紙上建造一個全新的中國。(這一點當然又和現代的烏托邦思想相關聯,此處不能涉及。)但是冷戰後的事實和研究使我們認識到民族文化的傳統具有一種看不見的韌力,決非現代的經濟、政治的力量所能完全取代;即使是極權統治的暴力也只能暫時壓住它,只要壓力一鬆,它又會復甦。所以今天討論民族認同和民族主義的形成,我們已不能不把文化傳統的因素充分考慮在內。(可參看Anthony D. Smith,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一文,收在Henry
Harris, Ident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及Liah Greenfield,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後一書分別討論英、法、俄、德、美五國民族主義的發展過程,論證尤為充實。)中國認同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對於文化傳統缺乏足夠的認識。我不是說我們必須無條件地肯定或讚揚傳統,那是沒有用的。我指的是我們必須研究從清代中葉到現在,傳統的一切具體方面的表現和變遷。以前不少知識分子只是一味以情緒的語言詛咒傳統,其結果則是加深了危機。
第二、前面討論中國現代認同的問題,其關鍵性的功用自然是繫於中國的知識階層。上文因避免頭緒太多,未加討論。現在總結之際,不能不作一簡單提示。現代的民族認同必須先由每一社會中的文化精英階層在思想上從事奠基的工作,這是各國歷史所共同昭示的。民族觀念的界定、釐清、及傳播,是知識分子的中心任務。所以在英、法、俄三國,起主導作用的是貴族階層中的知識精英,在德國則是中產階級知識分子。(見Greenfield前引書,頁二二)中國的情況稍有不同,而大致可分作兩個歷史階段:在清末尋求民族認同及倡導民族意識的是傳統的士大夫,但在民國則是現代型的知識分子。但前者既非貴族,後者也不屬於中產階級。這兩階段中的認同方式也略有差異:甲午戰後流行的「西學源出中國說」及稍後維新、國粹兩派將西方現代的價值觀念說成「古已有之」,雖都是附會,但卻有加深中國人歷史意識的意外效果。國粹派的提倡「國魂」、章炳麟用黃帝紀年,都是歷史意識高漲下的產物。但在第二階段中,由於受到康有為「托古改制」和西方史學觀念的雙重影響,「整理國故」的運動轉以「疑古」、「辨偽」為其指導思想,一切古代傳說都因受到嚴厲的質疑而動搖了。專就史學本身說,這當然是一個進步。然而以民族文化的認同而言,一般社會上的人士,尤其是青年學生,則因此反陷於困惑。何況「五四」以後中國知識界又首先認同於「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中國的民族認同與現代認同竟由此而分裂了。從此再換步移形,自不難滑入「反西方的西化」的軌道。
我們若以其他國家民族認同的歷程作對照,中國知識分子在這一方面的特色便十分顯著。例如希臘、愛爾蘭、伊色列等地的知識分子都強調他們在古代的共同文化起源和「黃金時代」;他們甚至大量運用神話、傳說、宗教經典等來支持這種虛構的歷史,以致引起史學家的嚴厲批評。但研究民族認同的專家則認為這是另一領域的活動,批評者的指摘儘管有根據,卻未搔到癢處。(參看Anthony D. Smith前引文,頁一三九─一四○;一四九)不但西方如此,日本民族認同的要求也一直阻止了它的史學家和一般知識分子對於天皇開國神話的公開質疑和研究。總之,民族文化的認同和客觀知識的追求都是現代的價值,但這兩個價值之間竟存在著必然的內在緊張。我在這裡只是指出這一事實和中國文化危機的關係,並無下價值判斷的用意。這是必須聲明的。
第三、中國的民族認同從師法西方歸結於「反西方的西化」是一個重要的歷史發展。1949年以後中國大陸正式宣布「一面倒」,開始全面模仿斯大林體制。中共借民族主義的力量在中國奪取政權以後,立即拋棄了民族文化的認同,轉而認同蘇聯。在文化政策上,中共不但澈底反西方近代的主流文化(資本主義)而且更強烈地反中國傳統(封建主義),至「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而達到最高潮。不但如此,在毛澤東1957年再度訪問莫斯科之後,他已開始醞釀反蘇聯所代表的「新西方」(修正主義)了。自此以後,他雖然仍堅持「階級鬥爭」這一「西方真理」,但「西方」或「新西方」已只剩下一個烏托邦的影子,再也沒有現實的基礎了。
以上一段只是現象的描述,而不是譴責。現在我們要對這一現象作進一層的理解。以前一般人常說:中國一向以「天朝」自居,視一切外國人為夷狄,但清代中葉以來屢敗於西方帝國主義,受盡屈辱,終於在心理上為西方所征服,從此由妄自尊大一變而為極端的自卑。這一心理的解釋稍嫌簡單,而且最多只能說明中國人為什麼長期以西方為模仿的範本,但不能說明以後那些迂迴的轉折。最近社會學家研究西方各國民族主義的興起與演變,特別重視「羨憎交織」("Ressentiment")這一心理因素,似乎很可以供我們參考。所謂「羨憎交織」的心理狀態起於企羨和憎惡的情緒受到壓制,而又不可能得到滿足。它的社會學基礎有兩個方面:第一是一個民族(或個人)自認對於它所企羨的對象基本上是平等的;第二是在現實上它和對方是處於不平等的狀態,以致這一理論上存在的平等幾乎沒有可能完成。在西方各國民族認同史上,「羨憎交織」的情緒因主觀和客觀條件的種種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現,未可一概而論。但它的存在和影響則相當普遍,如法國之於英國,德國之於英、法(尤其後者),俄國之於西方各國,都是顯例。這種心理狀態之所以特別顯現於上述諸國當然首先是因為它們之間,無論就歷史、文化或國家規模而言,都相當接近,也就是在理論上確互不相下。其次是在現代文化的成就上,英國起步最先(故無「羨憎交織」的心理),法國次之,德、俄最晚。其中俄國的處境和中國最相似(但並非相同)。俄國彼得大帝在十八世紀初年便開始效法西方,且取得很大的成績。到十八世紀的末期,已有俄國史學家認為俄國歷史上的光輝決不在英、法之下,西方不過偶然領先一步而已。俄國只要急起直追,必可趕上並超越西方。在整個十九世紀,俄國貴族知識分子大體都抱著同樣的心理──一方面師法西方,一方面與西方競賽。他們之間也有「國粹派」("Slavophilism")與「西化派」("Westernism")之分,然而兩派同為建造民族的現代認同而努力,也同以超越西方為最後目標。但在這兩個世紀之中,「羨憎交織」的情緒也逐漸在貴族知識分子的心中潛滋暗長。因為他們一方面已看到西方並不完美,現實與理想之間距離頗大,而另一方面又感到趕上西方仍是可望而不可及。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生根與成長便得力於「羨憎交織」情緒的最後爆炸。俄國最早的一批馬克思主義者既是西化派的主要代表,也是幻滅的「民粹派」("Narodnichestvo"),即「人民意志」;他們已下定決心要拒斥西方了。他們可以說是「反西方的西化派」的原型。他們在1917年發動的革命便是要毀滅俄國師法了兩個世紀的「西方」,這場革命當然首先毀滅了俄國自己的文化傳統;但他們認為這是必須而且值得付出的代價。列寧的國際主義的背後也藏著一股「羨憎交織」的俄羅斯民族情緒,通過「無產階級革命」,俄羅斯人超過了西方資本主義的歷史階段,率先進入社會主義。這便是俄羅斯民族的驕傲,他們在與西方長期競賽中終於勝利了。(以上論「羨憎交織」的心理與俄國民族認同的複雜過程都根據Liah
Greenfield前引書,特別參看頁一五─一六;二六五─二七一)
與俄國民族認同的歷史進程相對照,我們立刻可以發現「羨憎交織」的心理在二十世紀的中國也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首先,中國對於西方恰好具有「羨憎交織」的兩個實際的條件:一、中國的文明足以與西方比肩,這是世界公認的事實。二、中國在十九世紀與西方強弱懸殊,處於絕對不平等的地位。由於理論上的平等,中國才有資格效法西方,見賢思齊;由於實際上的不平等,中國才會對西方發生企羨的心理,並在效法無成,長期挫折之中轉羨為憎,而激起強烈的反西方的情緒。晚清士大夫稍明國際形勢者早就主張模仿西方。魏源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和馮桂芬的「采西學議」都是盡人皆知的例子。從十九世紀六○年代開始,中國模仿西法,範圍逐步放大,由技藝、政法、學術思想,至於整個文化的改造。無論是晚清士大夫或二十世紀的知識分子,儘管其中有些人主張模仿西方的言論在當時聽起來十分刺耳,都沒有對中國的民族地位真正失去信念。他們仍深信中國與西方從歷史的長程上看,是並駕齊驅的;眼前的優劣是暫時的,只要中國肯努力,西方是能夠趕得上的。所以我決不贊成譏笑西化派,甚至嚴厲自責的知識分子為「喪失了民族自尊心的洋奴買辦」。相反地,一個知識分子在文化認同的問題上,敢於公開主張學別人的長處和敢於責備自己的短處,他都首先必須對自己民族的過去和未來具有相當堅強的信心。至於言論是否過偏、用詞是否失當,則是另一個問題。中國近代知識分子長期地堅持效法西方正好說明他們在心理上對於中國「本來之民族地位」並未動搖。西化派如此,即所謂「國粹派」或「文化本位派」也是如此。1919年底陳寅恪在美國哈佛大學和吳宓討論中西文化的優劣,便承認中國的哲學、美術、科學都遠不如西方,但他對中國文化的獨特價值的肯定一點也沒有猶疑。(可看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清華大學出版社,1992,頁九─一○所引《吳宓日記》)
就我閱讀所及的直覺印象,二十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對於中西文化大多數都有矛盾複雜的情緒。國粹派或文化本位派的人在正面自然維護中國的傳統,但在側面往往對西方文化流露一種仰慕的意味;西化派則相反,正面提倡西方的價值,側面仍未能忘情於傳統。這個印象希望將來有人作全面的研究,也許可以得到證實、否證或修訂。現在姑引傅斯年在1929年的一個現身說法的觀察,他對胡適說:「孫中山有許多很腐敗的思想,比我們陳舊得多了,但他在安身立命處卻完全沒有中國傳統的壞習氣,完全是一個新人物。我們的思想新、信仰新;我們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處,我們仍舊是傳統的中國人。」(《胡適的日記》,第八冊,臺北,遠流出版社,1988,民國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胡適的評語說:「孟真此論甚中肯。」這個例子可以說明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身上確交織著中西兩種文化的成分,並且彼此交戰。這種情況便給「羨憎交織」的心理提供了基礎,遇到客觀形勢發生變化,它就會有種種不同的表現。民國以來,西方各國(包括西化成功的日本)給予中國人民的一般印象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知識分子對他們所師法的西方自然便逐漸從企羨轉向憎恨;反西方的情緒一天天地在滋長。孫中山便是由於對英、美失望,一變而「以俄為師」;陳獨秀也從謳歌「德先生」和「賽先生」而改宗馬克思主義。自「五四」以後,中國傳統的地位早已在青年知識分子的心中一落千丈;在思想激進化的總趨勢下,他們雖反西方卻不認同於中國的文化傳統。因此在政治和思想上活躍的知識分子越來越感到「反西方的西化」具有難以抗拒的吸引力。「羨憎交織」的心理終於把他們推向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
我必須著重地指出,「羨憎交織」的心理並不是解釋二十世紀中國文化認同與文化危機的唯一根據,但它確實可以開啟一道理解中國現代史的新門徑,這是比較史學和歷史社會學的一項貢獻。
第四、最後我要回到多元文化的問題,並提出一個較為具體的看法。冷戰終結以來的世局發展和近二十年來的研究都已證明民族文化的傳統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因此前蘇聯與東歐的共產體制崩解以後,每一民族的古老文化力量──
尤其是宗教──都很快地復甦了。這是三、四十年前人文社會科學家很難想像的。他們當時受實證論──尤其是社會經濟決定論──的影響太大,對於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的文化並不重視。照當時的一般想法,工業化帶來的社會結構的變遷和科學發展帶來的理性覺醒必然導致文化狀態的根本改觀。甚至宗教也難免要漸歸消寂。現代化將使各不相同的落後國家循著大致相同的途徑走上同一類型的社會,到了那時所謂各民族文化之間的不同,最多也不過是「風格」上的差別而已。無論是「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或馬克思主義在這個問題上都相去不遠。(四○年代馮友蘭寫《新事論》便已持此看法,而馮氏同時又以繼承中國文化的傳統自許。一直到晚年寫《三松堂自序》他似乎都沒有發現自己想法的矛盾。)
現在我們既改變了看法,承認民族文化也有它的自主性,我們便不能不接受「世界上的文化是多元的」這一事實。這些不同文化單元所構成的世界至少在可見的將來似乎還不可能達到「大同」的境界,更不必說整齊劃一了。前面提到杭廷頓的「文明衝突」說便是從這一新的前提上出發的。(杭廷頓將「文明」界定為「文化實體」("cultural entity"),故二詞可以通用。見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93, p. 23)但是把這個前提推向其邏輯的極端便自然出現文化相對主義的危險。依照文化相對主義,則每一文化都是獨特的,都有其內在的價值標準,因此誰也不能用自己的價值標準去評判另一文化的是非。舉例來說,中國不少知識分子都說中國只有專制傳統,沒有民主制度;只有綱常名教,沒有人權與個人自由。民主、自由、人權都是西方文化的產物。如果循著文化相對主義的邏輯論證,我們便可以理直氣壯地為中國的專制和綱常名教辯護說:這在中國文化系統之內是完全正常的、合理的。即使今天中國所實行的是現代專制、現代綱常名教,文化相對主義的論證也依然是有效的。這是文化相對主義的危險性的最顯著的例子。
但是事實上,我們承認文化的自主性並不必然要流入文化相對主義;而且即使我們接受某種程度的文化相對主義也不必然要把它推向邏輯的極端。上述的危險不是無法避免的。我們強調文化的自主性並不涵蘊文化決定一切的意思,只不過是為了修正以前的社會經濟決定文化的偏激之論而已。如果我們具有知識真誠,我們便必須承認:世界上文化單元雖多,並不是全沒有優劣高低可言,今天有些人受到美國流行的「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的庸俗觀念的影響,竟不敢再涉及文化的優劣與高低,這是很可笑的。湯因比(Arnold
Toynbee)從前曾用過「高級文明」("higher civilizations")這一名詞,我認為現在還有其效用。但是主要由於人類學研究的進展,今天我們評判文化優劣高低所使用的標準比從前精密多了。最重要的是今天西方學人也不再提「普遍的文明」("universal civilization")這一西方的觀念了,因為這一觀念的潛合詞是以西方代表「普遍」。在幾個「高級文明」之間,我們至少可以說是互有優劣,互有高低,依我們比較的方面而定。
極端的文化相對主義之所以不能成立是因為它必須假定各文化之間從無交通,也完全不能互相瞭解,更不能互相吸收。這顯然與歷史的事實不符。杭廷頓專講「文明的衝突」倒是有走入極端的危險。在世界各文化單元互相交流、互相瞭解──
雖然不可能達到完整的境界──的情況下,共同的標準還是可以出現的。從前我們過於重視共同標準的作用,以為只要有了它,各文化便可依之實踐。例如以「公平」、「民主」、「人權」為共同而普遍的標準,一切國家都可以建立起符合這些標準的制度。以前的人類學家也特別重視尋找「文化共相」("cultural universals"),並企圖在「文化共相」的基礎上創造出一個「普遍的文明」,事實證明這都是走不通的路。
今天我們覺悟到一切文化都是個別的,共同原則雖然存在,但其實現仍然要靠各文化內部自尋途徑、自創方式。例如即使在西方文化圈內,民主、自由、人權、公平等的具體實現仍然在不同國度有不同的方式,英、法、美、德之間的差異很大。最近華爾澤(Michael
Walzer)提出了「厚」("thick")與「薄」("thin")的一對觀念,對於解決我們此處的困難頗有啟發之處。他說的「厚」是指每一社會或文化的特殊性,「薄」則指人類的普遍性。因為一切不同種族、文化、社會的人都是「人」,所以人的普遍性是無法否認的;但是沒有一個人是不屬任何特殊社會或文化的,因此人的特殊性也不能抹殺。然而兩者相較,他特別重視人的特殊社會、文化背景,「薄」是從「厚」中出來的,也只有在「厚」中,「薄」才能發展。在平常的日子裡,人都生活在他的特殊社會文化之中,並在其中追求某些普遍原則的充分實現。在這種情況下,他不需要把這些普遍原則清楚地提煉出來,爭取國際上的同情,一切批判都在他的社會文化的內部進行。但是每逢內在批判遭到國內統治者的殘酷鎮壓而爆發危機,以致引起國際的注意時,內部的抗議便自然會從「厚」中提煉出「薄」──即普遍原則,以昭告於全世界。華爾澤曾特別舉出1989年捷克人民在普拉格反共遊行時所揭櫫的「真理」與「公平」兩個口號和同年北京天安門學生所高舉的「民主女神」作為例證。在他看來,這三個觀念都代表捷克與中國內部發展出來的普遍原則。他完全能同情地理解這些原則,但是他不可能完全瞭解這些普遍原則後面所代表的文化背景。換句話說,他只能同情「薄」,而不知道「薄」所由出的「厚」,因為這是只有內部的人才能充分把握得到的。以中國的學生運動為例,他說:中國知識分子所倡導的「民主」自然是他所願意支持的。然而知識分子以民主為己任的表現便與美國文化不甚協調了。因為美國人並不以為實現民主的責任可以完全由知識分子承擔起來;而且美國文化中有一股反知識分子的傾向。所以他推測這種知識精英主義的現象只有從中國的特殊文化社會背景中去求答案:它或起於列寧主義的前衛政治或出於共產黨以前的文化傳統──儒家傳統。如果民主一旦在中國實現,它仍將具有中國文化的特徵。最後華爾澤在一切抽象的、普遍的原則之上,提出了一個最後的但同時也是最基本、最普遍的觀念,即「自決」("self-determination")──包括個人與社群。這是古今一切文化與社會中都共同承認的核心價值,民主、人權等原則也由此出。「民主」、「人權」的語言起於西方,但這些普遍原則則潛存在一切文化、社會之中,因為沒有一個人或社群不重視「自決」的價值。但是我們不能僅注重這些「薄」的普遍原則,而當更重視「厚」的文化背景。「薄」怎樣在「厚」中落實才是真正的關鍵所在。這只有每一文化中的人自己從內部去尋找最合適的途徑與方式。(Thick and Thin, Moral Argument at Home and Abroa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5)
很顯然的,華爾澤不但接受了文化多元論,而且也強調每一文化的內在力量。然而他並沒有陷入文化相對主義;他從共同人性中找到了共同標準。讓我暫時以他的觀察結束這篇文字。
余英時
1995年7月19日於普林斯頓
-------
《現代危機與思想人物》
 防火牆:抵擋新自由主義的入侵
防火牆:抵擋新自由主義的入侵
 布赫迪厄論電視
布赫迪厄論電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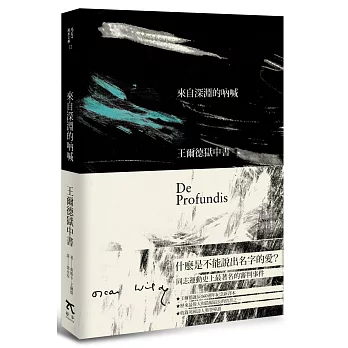








































![「 Les funérailles de Victor Hugo, la foule place de l'Etoile (1er juin 1885) Jean Béraud 1885 @[159737906547:274:Musée Carnavalet - Histoire de Paris] 」](http://fbcdn-sphotos-b-a.akamaihd.net/hphotos-ak-xpf1/v/t1.0-9/p240x240/19493_842775475808930_7923198242478759601_n.jpg?oh=4b146d8542c6245c5d521c31fe2d32c4&oe=55FA6D11&__gda__=1443493941_13468257f1a0c00ce90187b0320ce96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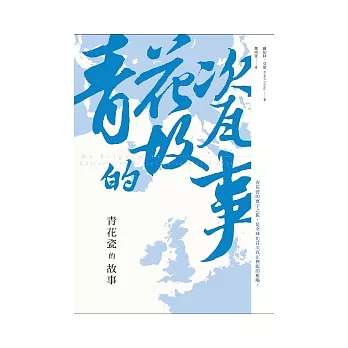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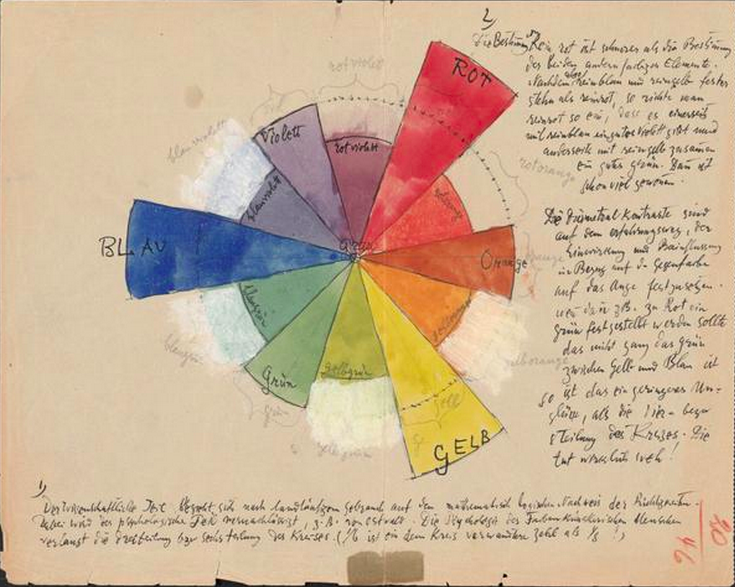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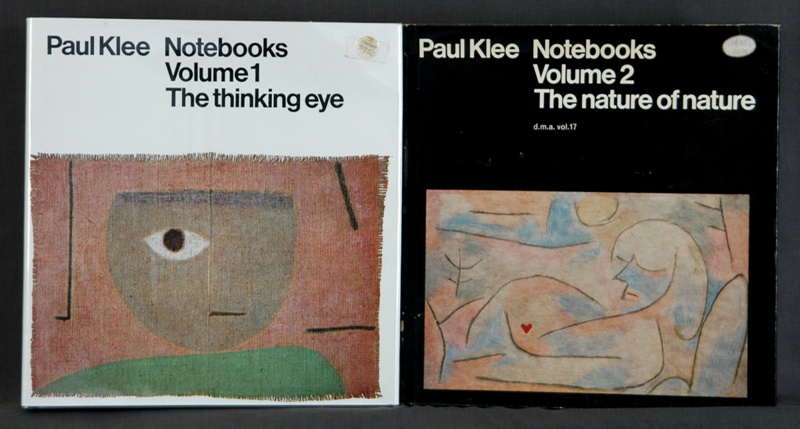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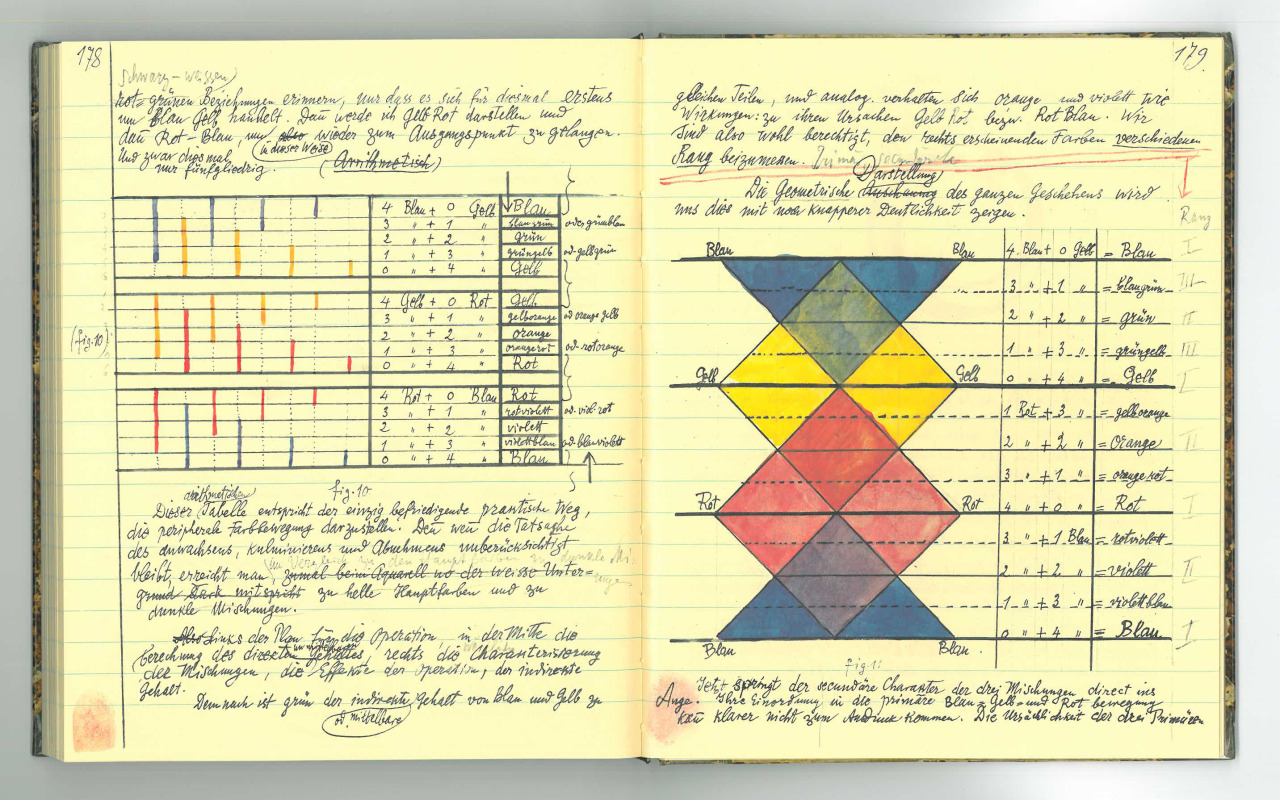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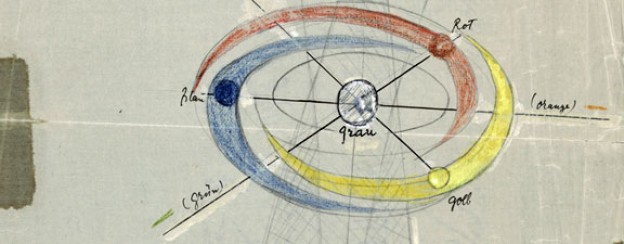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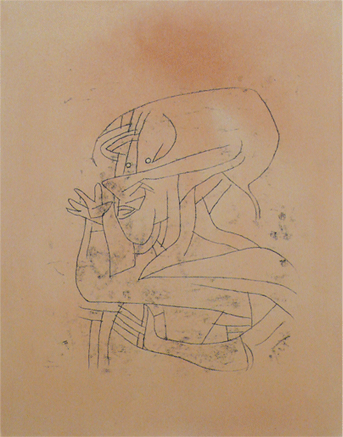





 【本書目錄】
【本書目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