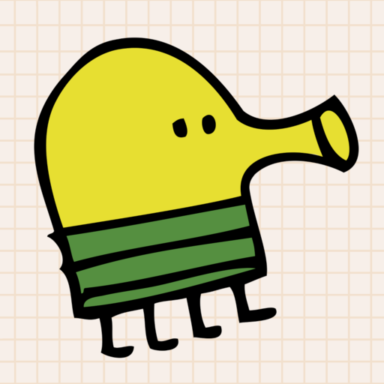伊格言
【我所知道的台灣社會】
於二戰時被送進奧茲維茲集中營的義大利籍猶太化學家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在《滅頂與生還》第八章中分享了一位德國讀者的來信。這位德國讀者海蒂在戰後閱讀了李維前此的著作《奧茲維茲殘存》(義大利文初版於一九四七年,德文版則在十多年後出版),並陳述自己的親身經歷──關於戰後的德國人如何看待自己在二戰時的行為。
- 海蒂表示,有一次她去旁聽了一場關於安樂死的審判(犯人是位醫生,於法庭上陳述時旁及他對納粹集中營毒氣室殺人的看法),回家後在飯桌上和兒子分享在法庭上聽到的一切。然而此刻,與他們一起用餐的清潔女傭(一位寡婦)卻突然發難:這女人放下她的叉子,挑釁地打斷我的話:
「現在進行的這些審判有什麼意義?他們又能怎樣?我們那些可憐的士兵只是奉命行事,他們有什麼辦法?我先生休假從波蘭回來時,告訴我說他們唯一做的事就是射殺猶太人,一天到晚射殺猶太人,開槍開到他們的手臂都痛了。但是別人命令他,他又能怎麼辦?」
- 我把她解雇,強忍住衝動,沒有出口恭喜她可憐的丈夫在戰爭中身亡。所以你看,直到今天,在德國,我們都還不時看到這樣的人。
- ふ‐しぎ【不思議】
- [名・形動]《「不可思議」の略》 1 どうしてなのか、普通では考えも想像もできないこと。説明のつかないこと。また、そのさま。「―な出来事」「成功も―でない」 2 仏語。人間の認識・理解を越えてい...
德國人海蒂這段證言讀來令人心驚肉跳。但我首先想到的竟是「因政治立場不同而解雇員工是違反勞基法的」──這似乎有些好笑,然而我隨即明白,說這位雇主海蒂因為「政治立場相異」而解雇員工並不全然準確。正確說法是,她是因為某些「難以容忍的道德歧異」而解雇員工的。這裡確然有些比例原則上的問題,也值得探討,但暫不深究。我想討論的是那位清潔女傭戰死的丈夫──也就是那位奉命不停射殺猶太人的士兵。理論上,若情況允許,我們應該在被迫執行一次或數次屠殺任務之後辭職;而這項基於道德良知的選擇(辭職),其難度則因周邊客觀條件有所差異:舉例,若是我們經濟狀況困難,求職不易,亟需「士兵」此份軍職軍餉,那麼辭職的難度則較高;反之則較低。然而我們終究必須辭職(或作相關努力)──此點殆無疑義。讓我們繼續推想這位士兵(代稱為士兵A)的情況:如若士兵A確實基於道德良知而辭職,並且也存活至戰後;如若士兵A對自己的決定(與其他德國士兵不同,也確實和當時許多其他德國人不同)感到自豪,也因此在戰後自鳴得意地宣揚自己的良知行為──思慮及此,我便不免想到台灣。在我的理解裡,台灣是一個這樣的社會:它極可能會竭盡所能地嚴厲詆毀這位因為自己的良知而選擇辭職的士兵A,只因他「自鳴得意」,令人看不順眼;而同時以完全不成比例的方式輕縱那許許多多其他沒有辭職(沒有做出良知行為)的士兵──極輕量極微小的譴責,完全不及於對士兵A的巨量攻擊──甚至不惜忽略遺忘。
這是一個沒有能力分辨孰輕孰重的社會。或許也是一個有著莫名其妙的奇怪偏執的社會。或許也是一個在該寬容時卻不寬容,該嚴厲時也未見嚴厲的社會。我不清楚其他國家或其他領域是否如此,但很令人失望地,我所認識的台灣社會卻是這樣。
(圖為普利摩‧李維,來源:http://yalebooksnetwork.org/yupblog/wp-content/uploads/sites/4/2014/01/primo-levi-berel-lang-featured.jpg)
金銀銅さわって「元素のふしぎ」体感 特別展スタート
  展示されている元素周期表=東京・上野の国立科学博物館、長島一浩撮影 展示されている元素周期表=東京・上野の国立科学博物館、長島一浩撮影 |
  内覧会で公開された、特別展「元素のふしぎ」=東京・上野の国立科学博物館、長島一浩撮影 内覧会で公開された、特別展「元素のふしぎ」=東京・上野の国立科学博物館、長島一浩撮影 |
これまで知られている118の元素の素顔に迫る特別展「元素のふしぎ」(朝日新聞社など主催)が21日、東京・上野の国立科学博物館で始まった。さまざまな元素を含む鉱物などの展示や体験コーナーなどで、宇宙のあらゆるものをつくる元素を身近に感じることができる。
同じ大きさの金、銀、銅、アルミの延べ棒を比べるコーナーでは、元素で異なる重さを体感できる。フェルメールの絵画や有田焼の色が、元素と密接に関わっ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展示や、私たちの体の6割が酸素でできているとわかる「元素体重計」もある。
10月8日まで。料金は大人1300円、小中高校生500円。問い合わせはハローダイヤル(03・5777・8600)まで。
同じ大きさの金、銀、銅、アルミの延べ棒を比べるコーナーでは、元素で異なる重さを体感できる。フェルメールの絵画や有田焼の色が、元素と密接に関わっ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展示や、私たちの体の6割が酸素でできているとわかる「元素体重計」もある。
10月8日まで。料金は大人1300円、小中高校生500円。問い合わせはハローダイヤル(03・5777・8600)まで。
Il Sistema Periodico
His best-known work, The Periodic Table (1975), is a collection of 21 meditations, each named for a chemical element.
週期表
Il Sistema Periodico ( The Periodic Table )
類別: 自然‧科普‧數理>物理化學Il Sistema Periodico ( The Periodic Table )
叢書系列:科學人文系列
作者:普利摩.李維
Primo Levi
譯者:牟中原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98年
書摘 1
第一章 氬Argon
我所知道的祖先和這些氣體有點像。
並不是他們身體怠惰,
但他們的精神無疑屬惰性,
傾向玄想和巧辯。
他們事蹟雖然多,
但都有靜態的共同特點,
一種不介入的態度,
自動(或接受)
被納入生命長河的邊緣支流。
在我們呼吸的空氣裡有所謂惰性氣體。它們有奇怪的希臘名字,博學的字源,意指「新」、「隱」、「怠惰」、「奇異」。它們真的是很遲鈍,對現狀極為滿意。它 們不參加任何化學反應,不和任何元素結合,因此幾世紀都沒被發現。直到1962年,一個努力的化學家,絞盡腦汁,成功地迫使「奇異」(氙氣)和最強悍的氟 結合。由於這功夫非常獨特了不起,他因而得了諾貝爾獎 (註1) 。它們也稱為貴族氣體--這裡有討論餘地,不知是否所有貴族氣體都為惰性,或所有惰性氣體都高貴。最後,它們也叫稀有氣體,即使其中之一的「氬」(怠惰),多到佔空氣的百分之一,也就是地球上的生命不可或缺的二氧化碳的二、三十倍。
我所知道的祖先和這些氣體有點像。我不是說他們身體怠惰,他們沒有能耐如此。他們反而必須相當努力來賺錢養家,以前還有「不做沒得吃」的道德信條。但他們 的精神無疑屬惰性,傾向玄想和巧辯。他們事蹟雖然多,但都有靜態的共同特點,一種不介入的態度,自動(或接受)被納入生命長河的邊緣支流。這些並非偶然。 無論貴重、惰性或稀有,和義大利、歐洲其他猶太族比起來,他們的經歷貧乏得多。他們似乎約在1500年左右從西班牙經法國南部來到皮埃蒙特 (註2) ,這可以從他們以地名來命名的姓氏看得出來。例如,Bedarida-Bedarrides , Momigliano-Montmelian , Segre (這是流過西班牙東北部的一條支流名) , Foa-Foix , Cavaglion-Cavaillon , Migliau-Millau ;位於法國的蒙彼利埃和尼姆間隆河口的倫內鎮 (Lunel) 翻譯成希伯來文成了yareakh(義大利文luna指月亮),由此而衍生了皮埃蒙特猶太人的姓氏Jarach。
在杜林 (註3) ,雖遭到排斥或冷淡接納,他們還是在南皮埃蒙特各處農村安頓下來,並引進造絲技術。即使最興盛時,他們還是極少數。他們既非受歡迎,也不討人厭;並沒有受 欺壓的故事流傳下來。但,與其餘民眾之間,有一層無形牆把他們隔開;是那疑心、嘲弄、帶敵意之牆。即使在1848年革命解放,而得以移居都市後也是如此。 父親說起在Bene Vagienna的童年時,學校裡,同伴會不帶敵意地取笑他,拿衣角捲在拳頭裡成驢耳朵,唱道:「豬耳朵,驢耳朵,送給猶太佬多多。」耳朵沒什麼特別含 義,手勢則是褻瀆模仿虔誠猶太教徒,在會堂應召上台念教律的彼此祈福動作--互相展示祈禱披肩摺邊,其流蘇的數目、長度、形狀都有神祕的宗教意義。但那些 孩子早就遺忘了這些動作的來源。順便提一下,對祈禱披肩的褻瀆和反猶太主義一樣古老,關在集中營的猶太人被沒收披肩後,黑衫隊便拿來做內褲。
排斥總是相互的。猶太人對基督徒也豎起對立的高牆 (goyim, narelim指「異教徒」,「沒行割禮的」),在平靜鄉下小地方,重演聖經選民的史詩。這從根的錯序,使我們的叔叔、阿姨們到今天都還自稱「以色列子民」。
這裡要趕快對讀者聲明「叔叔」、「阿姨」這些稱呼要從寬解釋。我們的習俗管任何年長親戚都叫叔、姨,即使關係很遠。日子久了,幾乎所有社區裡的大人都有親 戚關係,所以叔叔很多。叔叔是那些抽煙草的長老,阿姨是掌管全家的皇后,他們聰明有智慧。而對很老很老的叔姨(我們從諾亞以後就都長壽),「巴 伯」(barba,指「叔叔」),「瑪娜」(magna,指「阿姨」)這些字頭就連到他們的名字上了。因為希伯來文和皮埃蒙特方言的一些發音巧合及一些奇 妙字尾安排,造就了一些奇怪的名字,而這些妙語就同他們的故事,一代一代地傳了下來。於是有了巴伯伊托(伊利亞叔)、巴伯撒欽(以撒叔)、瑪娜麗亞(瑪麗 亞姨)、巴伯摩欽(摩西叔,據說他把兩顆下門牙拔了以便好咬煙斗)、巴伯姆林(山姆叔)、瑪娜維蓋亞(阿比蓋亞姨)、瑪娜弗林亞(柴伯亞姨,源自希伯來文 Tsippora,意指「小鳥」,一個漂亮名字)。雅各叔一定是幾代以前的人。他去過英國,所以穿格子裝,他弟弟「巴伯帕欽」(波拿帕特叔,這仍是一個常 用的猶太名字,以紀念拿破崙解放猶太人)後來則從叔叔輩退了下來。上天不仁,賜了他一個無法忍受的妻子,他絕望到去受洗,成了傳教士,到中國去傳教,如此 可離她遠遠地。
賓芭奶奶年輕時很美,脖子上圍著一條鴕鳥羽毛的圍巾,是個伯爵夫人。拿破崙賞給她家族伯爵名位,因他們曾借他錢 (manod) 。
巴伯隆寧(阿隆叔)個子高,健朗,又有些怪主意。他離家到杜林,幹過很多行業。他曾和卡力南諾劇院簽約當臨時演員,並寫信要家人來參加開演。內森叔和亞勒格娜姨來了坐在包廂中。當幕升起,亞勒格娜姨看到兒子打扮得像非利士人 (註4) ,她拚命大喊:「阿隆,你在搞什麼?把劍放下!」
巴伯米林腦筋簡單;在亞奇,人們把傻子當上帝的兒女,沒人可以喊他笨蛋,他受到保護。但他們叫他「種火雞的」。因為有個拉山(rashan,異教徒)騙他 說養火雞像種桃樹,種火雞羽毛到土中,樹上就長火雞。也許是由於牠那無禮、笨拙、暴躁的反面脾氣,火雞在這家族世界中有牠特別被用以取笑的地位。譬如,巴 西菲可叔養了隻母火雞,而且對牠疼愛有加。而他家對街住著拉特先生,是位音樂家,火雞老吵到他。他求巴西菲可叔讓火雞安靜,這大叔回答:「遵命!火雞小 姐,給我閉嘴。」
加布里叔是個猶太教士,所以人稱巴伯莫仁諾,就是「我們的老師叔」。他既老又快瞎,有次從外地回來,看到馬車經過,就喊停要求載一程。和車伕講話時,他發 覺那是一輛載基督徒到墳地去的靈車,多可怕的事。按教律,一個碰了死人,甚至進到停屍間的教士,就受污染7天。他跳起來:「我和異教徒死女人同車!車伕, 快停!」
可倫坡先生和格拉西狄奧先生兩人亦敵亦友。據傳說,這兩個對頭住在莫卡弗鎮一條巷子裡兩邊。格拉西狄奧是個瓦匠,很有錢。他有點以身為猶太人為恥,娶了個 基督徒。她有一頭及地長髮,與人私通,讓丈夫戴了綠帽。雖然是個異教徒 (goya) ,但大家還是叫她瑪娜奧西麗亞,表示有點接納她。她爸是船長,送格拉西狄奧一隻圭亞那來的彩色鸚鵡。牠會用拉丁文講:「認識你自己」。可倫坡先生是個窮 人,鸚鵡來了以後,他就去買了隻禿背烏鴉,也教會牠講話。每當鸚鵡喊「認識你自己」,烏鴉就會回答「臭神氣」。
加布里叔的pegarta,格拉西狄奧先生的goya,賓芭奶奶的manod和我馬上要談的haverta這些字需要一番解釋。Haverta是個希伯來 字,字的形和義都已改變,有特別含義。事實上,它是haver的不規則陰性字,等於「友伴」而意指「女佣」,但引申的含義是出身低下,風俗信仰都不同,但 不得不讓她住同一屋簷下的女人。Haverta習性不淨,態度不雅,對主人談話簡直有惡意的好奇心,令人討厭得不得了,以致她在場時,他們不得不用些特別 術語,haverta就是其中之一。這些術語行話現在幾乎消失了,幾代以前還有幾百個字。它們多半有希伯來字源,帶上皮埃蒙特字尾。只要粗略研究一下,就 可看出隱語的功能,是用來在goyim面前談goyim,或詛罵些沒旁人懂的話,或用來對付社會上的限制與壓迫。
因為頂多只有幾千人說隱語,這話的歷史價值不大,但人性意義可不少,所有變化中的語言大抵如此。一方面,它有皮埃蒙特方言粗獷、清晰、簡潔的特性(除了打 賭,從不寫成文字);另一方面又混雜神聖、莊嚴,經千年砥礪,光滑如冰河的希伯來文。兩種文字的對比帶來不少喜劇力量。這語言上的對比,又反映了四散的猶 太人,在猶太文化上的衝突。自從四散於異教徒之間(是的,在goyim之間),他們在所受神聖召喚和日常困頓之間總是不停掙扎。人就像那神話中的人頭馬 身,半靈半肉,聖靈與塵土都是召喚來源。猶太人兩千年來就悲傷地和這衝突共存,也就從中吸取了智慧和笑話,而後者是聖經和先知所缺的。它佈滿在意底緒 (Yiddish) 語中,也滲透到地上之父 (註5) 的奇言怪語中。在沒消失之前,我要記下來。這語言初聽之下,還以為是褻瀆神祇的,事實上和上帝間有種親密關係--如Nossgnor(我們的主),Adonai Eloeno(讚美主),Cadoss Barokhu(親愛的主)。
它屈辱的根源很容易看出來。例如,有些字因沒用就沒有了--「太陽」,「男人」,「城市」;而「夜晚」,「躲藏」,「錢」,「牢獄」,「偷」,「吊」, 「夢」這些字是有的。(最後的「夢」字只用於bahalom(在夢中)這個情境,以作為反義詞,指別想。)除此之外,有許多嘲弄的字,有時用來批判人,更 多時候是夫妻在基督徒店東面前舉棋不定時用的。我們有n sarod這複詞,已不再指希伯來文中的tsara(霉運),而是指不值錢的貨。它的暱稱則是優雅的sarodnn。我也忘不掉惡毒的sarod e senssa manod,這是媒人 (marosav) 用來指沒嫁妝的醜女人。Hasirud是從hasir(豬)字而來,指骯髒。值得注意的是,法文中“u”這個音在希伯來文中不存在,但是有“ut”這字尾 (義大利的“u”),用來製造抽象觀念的詞(例如,malkhut指王國),但沒有特殊用語裡帶有的強烈嘲弄含義。另外,它常出現的場合是在店裡,店東和 伙計用來損客人。上個世紀皮埃蒙特的服裝業是受猶太人掌控,從這行業產生了一些術語,在伙計做了店東後又傳了下來,後來也不一定是猶太人,很多店一直到現 在還用。很多說的人偶爾發現其字源是希伯來文,還大吃一驚。譬如,很多人還用“na vesta a kinim”代表格子裝。而kinim是蝨子,是古埃及十大災難的第三個,是猶太人逾越節中所教唱的儀文中字。
然而也有一大堆不是很雅的字,不但在小孩面前用,也用來代替詛咒。不像義大利話和皮埃蒙特話,它既可發洩,又不髒嘴,別人郤聽不懂。
譯註1:Neil Bartlett得此發現,成就非凡,但未因此得諾貝爾獎,此處為原作者之誤。
編註2:Piedmont,義大利西北部的一個地區。
編註3:Turin,皮埃蒙特地區最大城市,又譯都靈。
譯註4:古代居於巴勒斯坦的好戰民族,曾多次攻擊猶太人。
原註5:這兒是對比基督徒的禱文起頭:「我們在天之父……」。
並不是他們身體怠惰,
但他們的精神無疑屬惰性,
傾向玄想和巧辯。
他們事蹟雖然多,
但都有靜態的共同特點,
一種不介入的態度,
自動(或接受)
被納入生命長河的邊緣支流。
在我們呼吸的空氣裡有所謂惰性氣體。它們有奇怪的希臘名字,博學的字源,意指「新」、「隱」、「怠惰」、「奇異」。它們真的是很遲鈍,對現狀極為滿意。它 們不參加任何化學反應,不和任何元素結合,因此幾世紀都沒被發現。直到1962年,一個努力的化學家,絞盡腦汁,成功地迫使「奇異」(氙氣)和最強悍的氟 結合。由於這功夫非常獨特了不起,他因而得了諾貝爾獎 (註1) 。它們也稱為貴族氣體--這裡有討論餘地,不知是否所有貴族氣體都為惰性,或所有惰性氣體都高貴。最後,它們也叫稀有氣體,即使其中之一的「氬」(怠惰),多到佔空氣的百分之一,也就是地球上的生命不可或缺的二氧化碳的二、三十倍。
我所知道的祖先和這些氣體有點像。我不是說他們身體怠惰,他們沒有能耐如此。他們反而必須相當努力來賺錢養家,以前還有「不做沒得吃」的道德信條。但他們 的精神無疑屬惰性,傾向玄想和巧辯。他們事蹟雖然多,但都有靜態的共同特點,一種不介入的態度,自動(或接受)被納入生命長河的邊緣支流。這些並非偶然。 無論貴重、惰性或稀有,和義大利、歐洲其他猶太族比起來,他們的經歷貧乏得多。他們似乎約在1500年左右從西班牙經法國南部來到皮埃蒙特 (註2) ,這可以從他們以地名來命名的姓氏看得出來。例如,Bedarida-Bedarrides , Momigliano-Montmelian , Segre (這是流過西班牙東北部的一條支流名) , Foa-Foix , Cavaglion-Cavaillon , Migliau-Millau ;位於法國的蒙彼利埃和尼姆間隆河口的倫內鎮 (Lunel) 翻譯成希伯來文成了yareakh(義大利文luna指月亮),由此而衍生了皮埃蒙特猶太人的姓氏Jarach。
在杜林 (註3) ,雖遭到排斥或冷淡接納,他們還是在南皮埃蒙特各處農村安頓下來,並引進造絲技術。即使最興盛時,他們還是極少數。他們既非受歡迎,也不討人厭;並沒有受 欺壓的故事流傳下來。但,與其餘民眾之間,有一層無形牆把他們隔開;是那疑心、嘲弄、帶敵意之牆。即使在1848年革命解放,而得以移居都市後也是如此。 父親說起在Bene Vagienna的童年時,學校裡,同伴會不帶敵意地取笑他,拿衣角捲在拳頭裡成驢耳朵,唱道:「豬耳朵,驢耳朵,送給猶太佬多多。」耳朵沒什麼特別含 義,手勢則是褻瀆模仿虔誠猶太教徒,在會堂應召上台念教律的彼此祈福動作--互相展示祈禱披肩摺邊,其流蘇的數目、長度、形狀都有神祕的宗教意義。但那些 孩子早就遺忘了這些動作的來源。順便提一下,對祈禱披肩的褻瀆和反猶太主義一樣古老,關在集中營的猶太人被沒收披肩後,黑衫隊便拿來做內褲。
排斥總是相互的。猶太人對基督徒也豎起對立的高牆 (goyim, narelim指「異教徒」,「沒行割禮的」),在平靜鄉下小地方,重演聖經選民的史詩。這從根的錯序,使我們的叔叔、阿姨們到今天都還自稱「以色列子民」。
這裡要趕快對讀者聲明「叔叔」、「阿姨」這些稱呼要從寬解釋。我們的習俗管任何年長親戚都叫叔、姨,即使關係很遠。日子久了,幾乎所有社區裡的大人都有親 戚關係,所以叔叔很多。叔叔是那些抽煙草的長老,阿姨是掌管全家的皇后,他們聰明有智慧。而對很老很老的叔姨(我們從諾亞以後就都長壽),「巴 伯」(barba,指「叔叔」),「瑪娜」(magna,指「阿姨」)這些字頭就連到他們的名字上了。因為希伯來文和皮埃蒙特方言的一些發音巧合及一些奇 妙字尾安排,造就了一些奇怪的名字,而這些妙語就同他們的故事,一代一代地傳了下來。於是有了巴伯伊托(伊利亞叔)、巴伯撒欽(以撒叔)、瑪娜麗亞(瑪麗 亞姨)、巴伯摩欽(摩西叔,據說他把兩顆下門牙拔了以便好咬煙斗)、巴伯姆林(山姆叔)、瑪娜維蓋亞(阿比蓋亞姨)、瑪娜弗林亞(柴伯亞姨,源自希伯來文 Tsippora,意指「小鳥」,一個漂亮名字)。雅各叔一定是幾代以前的人。他去過英國,所以穿格子裝,他弟弟「巴伯帕欽」(波拿帕特叔,這仍是一個常 用的猶太名字,以紀念拿破崙解放猶太人)後來則從叔叔輩退了下來。上天不仁,賜了他一個無法忍受的妻子,他絕望到去受洗,成了傳教士,到中國去傳教,如此 可離她遠遠地。
賓芭奶奶年輕時很美,脖子上圍著一條鴕鳥羽毛的圍巾,是個伯爵夫人。拿破崙賞給她家族伯爵名位,因他們曾借他錢 (manod) 。
巴伯隆寧(阿隆叔)個子高,健朗,又有些怪主意。他離家到杜林,幹過很多行業。他曾和卡力南諾劇院簽約當臨時演員,並寫信要家人來參加開演。內森叔和亞勒格娜姨來了坐在包廂中。當幕升起,亞勒格娜姨看到兒子打扮得像非利士人 (註4) ,她拚命大喊:「阿隆,你在搞什麼?把劍放下!」
巴伯米林腦筋簡單;在亞奇,人們把傻子當上帝的兒女,沒人可以喊他笨蛋,他受到保護。但他們叫他「種火雞的」。因為有個拉山(rashan,異教徒)騙他 說養火雞像種桃樹,種火雞羽毛到土中,樹上就長火雞。也許是由於牠那無禮、笨拙、暴躁的反面脾氣,火雞在這家族世界中有牠特別被用以取笑的地位。譬如,巴 西菲可叔養了隻母火雞,而且對牠疼愛有加。而他家對街住著拉特先生,是位音樂家,火雞老吵到他。他求巴西菲可叔讓火雞安靜,這大叔回答:「遵命!火雞小 姐,給我閉嘴。」
加布里叔是個猶太教士,所以人稱巴伯莫仁諾,就是「我們的老師叔」。他既老又快瞎,有次從外地回來,看到馬車經過,就喊停要求載一程。和車伕講話時,他發 覺那是一輛載基督徒到墳地去的靈車,多可怕的事。按教律,一個碰了死人,甚至進到停屍間的教士,就受污染7天。他跳起來:「我和異教徒死女人同車!車伕, 快停!」
可倫坡先生和格拉西狄奧先生兩人亦敵亦友。據傳說,這兩個對頭住在莫卡弗鎮一條巷子裡兩邊。格拉西狄奧是個瓦匠,很有錢。他有點以身為猶太人為恥,娶了個 基督徒。她有一頭及地長髮,與人私通,讓丈夫戴了綠帽。雖然是個異教徒 (goya) ,但大家還是叫她瑪娜奧西麗亞,表示有點接納她。她爸是船長,送格拉西狄奧一隻圭亞那來的彩色鸚鵡。牠會用拉丁文講:「認識你自己」。可倫坡先生是個窮 人,鸚鵡來了以後,他就去買了隻禿背烏鴉,也教會牠講話。每當鸚鵡喊「認識你自己」,烏鴉就會回答「臭神氣」。
加布里叔的pegarta,格拉西狄奧先生的goya,賓芭奶奶的manod和我馬上要談的haverta這些字需要一番解釋。Haverta是個希伯來 字,字的形和義都已改變,有特別含義。事實上,它是haver的不規則陰性字,等於「友伴」而意指「女佣」,但引申的含義是出身低下,風俗信仰都不同,但 不得不讓她住同一屋簷下的女人。Haverta習性不淨,態度不雅,對主人談話簡直有惡意的好奇心,令人討厭得不得了,以致她在場時,他們不得不用些特別 術語,haverta就是其中之一。這些術語行話現在幾乎消失了,幾代以前還有幾百個字。它們多半有希伯來字源,帶上皮埃蒙特字尾。只要粗略研究一下,就 可看出隱語的功能,是用來在goyim面前談goyim,或詛罵些沒旁人懂的話,或用來對付社會上的限制與壓迫。
因為頂多只有幾千人說隱語,這話的歷史價值不大,但人性意義可不少,所有變化中的語言大抵如此。一方面,它有皮埃蒙特方言粗獷、清晰、簡潔的特性(除了打 賭,從不寫成文字);另一方面又混雜神聖、莊嚴,經千年砥礪,光滑如冰河的希伯來文。兩種文字的對比帶來不少喜劇力量。這語言上的對比,又反映了四散的猶 太人,在猶太文化上的衝突。自從四散於異教徒之間(是的,在goyim之間),他們在所受神聖召喚和日常困頓之間總是不停掙扎。人就像那神話中的人頭馬 身,半靈半肉,聖靈與塵土都是召喚來源。猶太人兩千年來就悲傷地和這衝突共存,也就從中吸取了智慧和笑話,而後者是聖經和先知所缺的。它佈滿在意底緒 (Yiddish) 語中,也滲透到地上之父 (註5) 的奇言怪語中。在沒消失之前,我要記下來。這語言初聽之下,還以為是褻瀆神祇的,事實上和上帝間有種親密關係--如Nossgnor(我們的主),Adonai Eloeno(讚美主),Cadoss Barokhu(親愛的主)。
它屈辱的根源很容易看出來。例如,有些字因沒用就沒有了--「太陽」,「男人」,「城市」;而「夜晚」,「躲藏」,「錢」,「牢獄」,「偷」,「吊」, 「夢」這些字是有的。(最後的「夢」字只用於bahalom(在夢中)這個情境,以作為反義詞,指別想。)除此之外,有許多嘲弄的字,有時用來批判人,更 多時候是夫妻在基督徒店東面前舉棋不定時用的。我們有n sarod這複詞,已不再指希伯來文中的tsara(霉運),而是指不值錢的貨。它的暱稱則是優雅的sarodnn。我也忘不掉惡毒的sarod e senssa manod,這是媒人 (marosav) 用來指沒嫁妝的醜女人。Hasirud是從hasir(豬)字而來,指骯髒。值得注意的是,法文中“u”這個音在希伯來文中不存在,但是有“ut”這字尾 (義大利的“u”),用來製造抽象觀念的詞(例如,malkhut指王國),但沒有特殊用語裡帶有的強烈嘲弄含義。另外,它常出現的場合是在店裡,店東和 伙計用來損客人。上個世紀皮埃蒙特的服裝業是受猶太人掌控,從這行業產生了一些術語,在伙計做了店東後又傳了下來,後來也不一定是猶太人,很多店一直到現 在還用。很多說的人偶爾發現其字源是希伯來文,還大吃一驚。譬如,很多人還用“na vesta a kinim”代表格子裝。而kinim是蝨子,是古埃及十大災難的第三個,是猶太人逾越節中所教唱的儀文中字。
然而也有一大堆不是很雅的字,不但在小孩面前用,也用來代替詛咒。不像義大利話和皮埃蒙特話,它既可發洩,又不髒嘴,別人郤聽不懂。
譯註1:Neil Bartlett得此發現,成就非凡,但未因此得諾貝爾獎,此處為原作者之誤。
編註2:Piedmont,義大利西北部的一個地區。
編註3:Turin,皮埃蒙特地區最大城市,又譯都靈。
譯註4:古代居於巴勒斯坦的好戰民族,曾多次攻擊猶太人。
原註5:這兒是對比基督徒的禱文起頭:「我們在天之父……」。
對風俗有興趣的人,那些談到天主教的字就更有意思。此處,原始的希伯來文形式就變化得更厲害了。有兩個理由:第一,祕密是絕對必要,萬一異教徒聽懂了,可 會召來褻瀆之罪,第二,用意本來就是要扭曲,扭到否定意義,去除原來超凡德性。同樣道理,在所有語言裡,「魔鬼」都有各種文飾的講法,不講它,指的郤是 它。教會(天主教)是叫toneva,它的來源我無法查考,也許只從希伯來文取其音;而猶太會堂則謙虛地只叫scola(學校),一個學習成長的場所。對 等地,教士不是用rabbi或rabbenu(我們的教士),而是用moreno(我們的老師)或khakham(智者)。事實上,在「學校」裡,人不是 被基督徒中狠毒的khaltrum所苦:khaltrum或khantrum是天主教徒講究儀式和偏執的結果,因為多神而拜偶像,令人無法忍受。(「出埃 及記」第20章第3節:「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別的神,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向任何偶像跪拜。」)這個詞在長久詛咒中成長,來源已不可考,幾乎可 確定不是來自希伯來文,而是某種猶太-義大利隱語中的形容詞khalto,亦即「偏執」,用來形容崇拜偶像的基督徒。
A-issa是聖母(就是「那女人」)。而全然不可解、祕密的字--可預料到的--是Odo,當無可避免時,壓低聲音,四處張望,用這字指耶穌。越少提基督越好,因弒上帝之神話難以磨滅。
還有很多從禱文、聖書來的字。上世紀出生的猶太人,大致都熟讀希伯來原文,至少懂得部份;但成了隱語時,就任意扭曲。Shafokh這字根,意指「傾 倒」,它出現在「詩篇」第79章(「願你將你的忿怒,傾倒在那不認識你的外邦,和那不求告你名的國度」)。我們的老祖母們就把fe sefokh(to make a sefokh) 用來形容嬰兒嘔吐。Ruakh(複數rukhod) 意指「呼吸」,出現在黑暗而可敬的<創世記>第二句(「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從這發展出tire "n ruakh(放屁)這生理詞,由此可看出一點選民與造物主間特殊的親密感。舉個實例吧,多年來流傳著雷琪娜姨的一句話,她和大衛叔坐在波街上弗羅里奧咖啡 店,說:「Davidin, bat la cana, c"as sento nen le rukhod!」(「大衛,用力跺你的拐杖,免得人家聽到你放屁!」)這是夫妻間親密的話。那時,拐杖是社會地位的象徵,就像今天坐特等艙旅行。譬如,我 父親有兩把手杖,平常是用竹拐杖,禮拜天則用籐手杖,杖柄鑲銀。他不用手杖撐身體(無此需要),而是在空中比劃,及用來趕無禮的狗,簡言之,那是一個和粗 俗大眾區隔的權杖。
一個虔誠的猶太人,應該每天頌禱barakha這詞上百次。他應深深感恩,因每次如此做,就履行了與神的千年對話。雷翁寧爺是我曾祖。他住在蒙弗拉多,有 扁平足,而他屋前巷子鋪了圓石頭,他每次在上頭走就腳痛。有天出門,發現巷子改鋪了平石板,他高興得大呼:“N abrakha a coi goyim c"a l"an fait I losi!”(祝福那鋪路的不信教者!)至於詛咒,有一怪詞meda meshona,直譯是「怪死」,但事實上是模仿皮埃蒙特語assident,在義大利語直說就是「去死吧!」雷翁寧爺還留下了這句怪話:“C"ai takeissa "na meda meshona faita a paraqua.”(願他碰上狀如雨傘的災難。)
我也沒法忘掉巴伯里柯,他只早一代,差點就是我真正的叔叔。對他,我有清晰而複雜的回憶,他不是其他前面說的「固守某種姿態」的傳奇性人物,而是活生生的記憶。本章開始所說的惰性氣體的比喻,對巴伯里柯是再貼切不過。
他學醫,也成了個好醫生,但他並不熱愛這世界。也就是說,他雖喜歡人(尤其女人)、草原、天空,但可不愛辛苦工作、承諾、時程、期限、為前程而處心積慮、 為五斗米而折腰。他會想出走,但太懶沒做。有個愛他的女人,他則心不在焉的容忍她。女人和朋友們說服他去考越洋客輪的船醫,他輕易考取,從熱那亞到紐約航 行了一次,回到熱那亞就辭職了,因為在美國「太吵了」。
那以後,他就定居在杜林。他有好幾個女人,每個都想嫁他、拯救他,但他認為結婚、診所、開業都是過多的承諾。在1930年代,他已是個怯懦的小老頭,深度 近視,也沒人理。他和一個壯碩粗俗的goya女人同居,不時怯怯地想離開她。他喊她“"na sotia”(瘋子)、“"na hamorta”(驢子)和“"na gran beema”(巨獸),但總是略帶不可解的溫柔。那goya甚至想要他samda(受洗,字面解是「毀滅」),他則總是推拒--並不是出於宗教信念,而是 沒動機,事不關己。
巴伯里柯有12個兄弟姊妹,他們給了他女伴一個殘忍的名字「瑪娜嗎啡娜」(嗎啡姨)。這女人既是異教徒又沒兒女,不能真算是個瑪娜;事實上對她,瑪娜這頭 銜代表恰好相反的意思,一個「非瑪娜」,不被家族承認的人。而這名字殘忍,是因為它可能不正確的暗指,她利用巴伯里柯的空白藥單取得嗎啡。
他們兩人住在凡奇里亞街一個髒亂的閣樓。叔叔是個有智慧、有能力的好醫生,但他鎮日躺在那兒看書讀舊報紙。他記憶奇佳,閱讀廣博,深度近視讓他戴著酒瓶底 厚度的眼鏡,書只離臉3吋。他只有出去行醫時才起來,因他幾乎從不要錢,常有人來求他。他的病人多是住在郊外的窮人,他會收下半打蛋,菜園的菜,或舊鞋子 作為診費。因沒錢坐街車,他走路去看病人。路上,透過近視眼微弱的視力,看到小姐朦朧的身影,他會上去在一呎距離仔細打量,弄得人家不知如何是好。他幾乎 不吃東西,好像無此需要,最後以90高齡,尊嚴地過世。
費娜奶奶排斥世界的程度和巴伯里柯不相上下。她們4姊妹都叫費娜:因為從小4姊妹都先後被送到同一個叫戴費娜的保姆那兒,她叫這些小孩同一名字。費娜奶奶 住在卡馬諾拉一棟2樓公寓,很會鉤織。86歲時,她得了個小病,那時女士常有,現在則似乎都神祕地消失了。從那以後20年,直到過世,她再也沒出過門,禮 拜時,她就在滿佈花朵的陽台向從scola(會堂)出來的人揮手。但她年輕時一定不一樣。她的故事是:她丈夫帶蒙卡弗教士來家做客,這教士是一個博學廣受 尊敬的人。家裡沒什麼吃的,她在他不知情下,讓他吃了豬肉。她弟弟巴伯拉弗林(拉飛爾),在升格成巴伯之前,人稱“l fieul d" Moise "d Celin”(色林摩西之子),現因賣軍用物資而成富人。他愛上加西諾的瓦拉布里加夫人,她是個大美女。他不敢公開追求,給她寫很多從沒寄的情書,然後給 自己寫熱情的回信。
馬欽叔也有段失意的愛情。他戀上蘇珊娜(希伯來文是「百合」之意),是個輕巧、虔誠的女人,擁有百年特製鵝香腸的祕方,用鵝脖子本身做香腸的外膜。因此在 Lasson Acodesh(「聖言」,即我們所討論的術語)中,脖子有3種相似詞留傳了下來。第一個mahane是中性字,代表脖子的字面意思。第二個savar只 用在隱喻,例如「有斷頸危險的快速度」。而第三個khanec就非常委婉且有暗示性,指可被阻絕、斷去的重要通道,例如「斷你生路」。 Khanichesse的意思則是「上吊自殺」。好了,馬欽當蘇珊娜的助手,在她廚房兼工廠和店裡幫忙,她架子上有香腸、聖物、護身符和祈禱書。蘇珊娜拒 絕了他,而馬欽惡毒報復的法子,是把祕方偷賣給一個goy。顯然,這goy不懂它的價值,因蘇珊娜死後(遙遠以前的事),市面上就找不到這祖傳的鵝香腸 了。因這令人厭惡的報復,馬欽叔就被開除「叔」級了。
最古最古,充滿惰性,籠罩在層層傳說之下的是那令人難以相信,化石級的巴伯布拉敏,來自切里的我外婆的叔叔。很年輕時他就很富裕,從貴族手上,買了很多切 里附近的農地。親戚靠他,吃喝跳舞旅行浪費了他不少錢。有天,他媽米爾卡(女王)姨病了,和丈夫吵了很久,終於決定僱個haverta做女佣。之前,她有 先見之明,總是拒絕家裡有其他女人。果然,巴伯布拉敏愛上這haverta,也許這是他第一個有機會遇上的可愛女人。
她名字沒傳下來,但德性大家知道一些。她豐滿而美麗,有雙壯觀的khlaviod(乳房):這詞在古希伯來文沒有,那時khalav指「牛奶」。她當然是 個goya,傲慢無禮,不識字,但燒一手好菜。她是個農家女,在家裡打赤腳。但這就是我叔叔愛死的地方:她的腳踝,直率的言語,和她的菜。他和女孩沒說什 麼,但告訴他父母他要娶她。他雙親馬上發狂,叔叔就躺上床。他就留在床上22年。
那麼多年布拉敏做什麼呢?有很多說法。毫無疑問,大多時候,他把日子花在睡覺和賭錢。據說,他經濟狀況垮掉是因為「他沒夾好」債券,或因為他信任一個 mamser(雜種)管理他的農場,那人把它賤價賣給自己的同伙。米爾卡姨完全料中,我叔叔就這樣把全家拖垮了,到今天他們還為這後果悲嘆。
也據說他在床上讀了不少書,最後也算成了公正有知識的人,在床邊還接見切里名人並仲裁爭執。也聽說,那同一個haverta,也到床上去了。至少我叔叔自 願上床閉關的頭幾年,晚上還會偷溜出去到樓下酒店打彈子。但他總算是在床上待了幾乎四分之一世紀。當米爾卡姨和所羅門叔過世後,他娶了個goya,真的帶 她上了床。到那時,他腿已完全無力站起來。1883年,他死時很窮,但名聲可富,精神也平安。
做鵝香腸的蘇珊娜,是我祖母瑪利亞奶奶的表姊。奶奶留下1870年在相館照的一張膠腫、盛裝打扮的相片。在我小時遙遠的記憶,她是個邋遢、皺皮、暴躁、聾 透了的老太婆。直到今天,不知怎麼搞的,櫥子裡最高架子上還有她的寶貝:黑絲花邊披肩、絲織巾、一個長了四代霉的貂皮手筒、刻有她名字的巨大銀器。好像, 歷經五十年後,她的靈魂還回家來看看。
年輕時,她可是個令很多人傷心的大美女。年紀輕輕她就守寡了,謠傳先祖父受不了她的不貞自殺了。她獨自節儉地帶大3個男孩,令他們讀書。但到年老,她讓步 了,嫁了個天主佬醫生,一個堂皇、寡言、大鬍子的老人。自此以後,她就傾向古怪小氣,雖然年輕時,她像多數美麗被愛的女人一樣慷慨大方。隨著年歲的增長, 她逐漸斷絕家庭溫暖(本來大概就不是很深)。她和醫生住在波街一個陰暗的公寓,冬天只有一個小富蘭克林爐,幾乎暖不了。她不再丟掉任何東西,因為都可能有 用處,連乳酪皮、巧克力箔紙都留著--她用箔紙做銀色小球,好送給教會以「拯救黑人小孩」。也許因害怕自己的選擇錯誤,她輪流去佩俄斯五世街的猶太 scola及聖歐塔維奧教堂做禮拜,她似乎甚至還去告解呢!1928年,她八十多歲過世,一群身著黑衣,邋遢的街坊鄰居為她送終,由一個叫西林柏格夫人的 女巫帶頭。雖然為腎臟病所折磨,奶奶到最後一口氣還小心地骷著西林柏格,怕她找到藏在床墊下的maftekh(鑰匙),偷走manod(錢)和 hafassim(珠寶),後來證實這些東西都是假的。
她死後,她兒子和媳婦氣急敗壞地花了幾星期清理屋裡堆積如山的垃圾。瑪利亞奶奶不分青紅皂白,存下垃圾和寶貝。從雕工複雜的核桃木櫃子裡蹦出成千的臭蟲, 有從沒用過的床單,又有打補釘脫線、薄得透明的床單。地下室中有幾百瓶好酒,都已經變成醋了。他們找到八件醫生全新的大衣,還塞了樟腦丸,但她允許他穿的 唯一那件郤打滿補釘,衣領油膩。
對她,我不記得很多,爸爸喊她媽姆(也用第三人稱),帶著孝意地愛說她的絕事。每星期天早上,爸帶我走路去看瑪利亞奶奶。沿著波街,我們走去,一路爸爸停 下摸摸貓咪,聞聞美食,翻翻舊書。爸爸是工程師,口袋總裝著書,認識所有豬肉販子,因他用計算尺算所買的豬肉。他買時並不輕鬆,並非宗教原因而是迷信。打 破食物禁忌令他不自在,但他愛豬肉,只要看到豬肉店櫥窗,每次都無力抗拒。他嘆一口氣,閉嘴詛咒兩下,以眼角骷我三次,似乎怕我批評或期望我的贊同。
當我們到公寓台階下,父親按鈴,奶奶來開門,他會對她耳朵大喊:「他考第一名!」祖母有點不情願地讓我們進去,帶我們經過一串積滿灰塵、沒人居住的房間, 其中一間有奇怪的儀器,是醫生半棄置的診所。很少看到醫生,我也不想看到他。尤其是自從有次我無意中聽到爸爸告訴媽媽,有人帶口吃的小孩就診,他拿剪刀把 他舌下的筋肉剪掉。當我們到了起居室,奶奶會挖出一盒巧克力,總是同一盒,給我一顆。巧克力已叫蟲咬了,我困窘地趕快藏進口袋裡。
A-issa是聖母(就是「那女人」)。而全然不可解、祕密的字--可預料到的--是Odo,當無可避免時,壓低聲音,四處張望,用這字指耶穌。越少提基督越好,因弒上帝之神話難以磨滅。
還有很多從禱文、聖書來的字。上世紀出生的猶太人,大致都熟讀希伯來原文,至少懂得部份;但成了隱語時,就任意扭曲。Shafokh這字根,意指「傾 倒」,它出現在「詩篇」第79章(「願你將你的忿怒,傾倒在那不認識你的外邦,和那不求告你名的國度」)。我們的老祖母們就把fe sefokh(to make a sefokh) 用來形容嬰兒嘔吐。Ruakh(複數rukhod) 意指「呼吸」,出現在黑暗而可敬的<創世記>第二句(「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從這發展出tire "n ruakh(放屁)這生理詞,由此可看出一點選民與造物主間特殊的親密感。舉個實例吧,多年來流傳著雷琪娜姨的一句話,她和大衛叔坐在波街上弗羅里奧咖啡 店,說:「Davidin, bat la cana, c"as sento nen le rukhod!」(「大衛,用力跺你的拐杖,免得人家聽到你放屁!」)這是夫妻間親密的話。那時,拐杖是社會地位的象徵,就像今天坐特等艙旅行。譬如,我 父親有兩把手杖,平常是用竹拐杖,禮拜天則用籐手杖,杖柄鑲銀。他不用手杖撐身體(無此需要),而是在空中比劃,及用來趕無禮的狗,簡言之,那是一個和粗 俗大眾區隔的權杖。
一個虔誠的猶太人,應該每天頌禱barakha這詞上百次。他應深深感恩,因每次如此做,就履行了與神的千年對話。雷翁寧爺是我曾祖。他住在蒙弗拉多,有 扁平足,而他屋前巷子鋪了圓石頭,他每次在上頭走就腳痛。有天出門,發現巷子改鋪了平石板,他高興得大呼:“N abrakha a coi goyim c"a l"an fait I losi!”(祝福那鋪路的不信教者!)至於詛咒,有一怪詞meda meshona,直譯是「怪死」,但事實上是模仿皮埃蒙特語assident,在義大利語直說就是「去死吧!」雷翁寧爺還留下了這句怪話:“C"ai takeissa "na meda meshona faita a paraqua.”(願他碰上狀如雨傘的災難。)
我也沒法忘掉巴伯里柯,他只早一代,差點就是我真正的叔叔。對他,我有清晰而複雜的回憶,他不是其他前面說的「固守某種姿態」的傳奇性人物,而是活生生的記憶。本章開始所說的惰性氣體的比喻,對巴伯里柯是再貼切不過。
他學醫,也成了個好醫生,但他並不熱愛這世界。也就是說,他雖喜歡人(尤其女人)、草原、天空,但可不愛辛苦工作、承諾、時程、期限、為前程而處心積慮、 為五斗米而折腰。他會想出走,但太懶沒做。有個愛他的女人,他則心不在焉的容忍她。女人和朋友們說服他去考越洋客輪的船醫,他輕易考取,從熱那亞到紐約航 行了一次,回到熱那亞就辭職了,因為在美國「太吵了」。
那以後,他就定居在杜林。他有好幾個女人,每個都想嫁他、拯救他,但他認為結婚、診所、開業都是過多的承諾。在1930年代,他已是個怯懦的小老頭,深度 近視,也沒人理。他和一個壯碩粗俗的goya女人同居,不時怯怯地想離開她。他喊她“"na sotia”(瘋子)、“"na hamorta”(驢子)和“"na gran beema”(巨獸),但總是略帶不可解的溫柔。那goya甚至想要他samda(受洗,字面解是「毀滅」),他則總是推拒--並不是出於宗教信念,而是 沒動機,事不關己。
巴伯里柯有12個兄弟姊妹,他們給了他女伴一個殘忍的名字「瑪娜嗎啡娜」(嗎啡姨)。這女人既是異教徒又沒兒女,不能真算是個瑪娜;事實上對她,瑪娜這頭 銜代表恰好相反的意思,一個「非瑪娜」,不被家族承認的人。而這名字殘忍,是因為它可能不正確的暗指,她利用巴伯里柯的空白藥單取得嗎啡。
他們兩人住在凡奇里亞街一個髒亂的閣樓。叔叔是個有智慧、有能力的好醫生,但他鎮日躺在那兒看書讀舊報紙。他記憶奇佳,閱讀廣博,深度近視讓他戴著酒瓶底 厚度的眼鏡,書只離臉3吋。他只有出去行醫時才起來,因他幾乎從不要錢,常有人來求他。他的病人多是住在郊外的窮人,他會收下半打蛋,菜園的菜,或舊鞋子 作為診費。因沒錢坐街車,他走路去看病人。路上,透過近視眼微弱的視力,看到小姐朦朧的身影,他會上去在一呎距離仔細打量,弄得人家不知如何是好。他幾乎 不吃東西,好像無此需要,最後以90高齡,尊嚴地過世。
費娜奶奶排斥世界的程度和巴伯里柯不相上下。她們4姊妹都叫費娜:因為從小4姊妹都先後被送到同一個叫戴費娜的保姆那兒,她叫這些小孩同一名字。費娜奶奶 住在卡馬諾拉一棟2樓公寓,很會鉤織。86歲時,她得了個小病,那時女士常有,現在則似乎都神祕地消失了。從那以後20年,直到過世,她再也沒出過門,禮 拜時,她就在滿佈花朵的陽台向從scola(會堂)出來的人揮手。但她年輕時一定不一樣。她的故事是:她丈夫帶蒙卡弗教士來家做客,這教士是一個博學廣受 尊敬的人。家裡沒什麼吃的,她在他不知情下,讓他吃了豬肉。她弟弟巴伯拉弗林(拉飛爾),在升格成巴伯之前,人稱“l fieul d" Moise "d Celin”(色林摩西之子),現因賣軍用物資而成富人。他愛上加西諾的瓦拉布里加夫人,她是個大美女。他不敢公開追求,給她寫很多從沒寄的情書,然後給 自己寫熱情的回信。
馬欽叔也有段失意的愛情。他戀上蘇珊娜(希伯來文是「百合」之意),是個輕巧、虔誠的女人,擁有百年特製鵝香腸的祕方,用鵝脖子本身做香腸的外膜。因此在 Lasson Acodesh(「聖言」,即我們所討論的術語)中,脖子有3種相似詞留傳了下來。第一個mahane是中性字,代表脖子的字面意思。第二個savar只 用在隱喻,例如「有斷頸危險的快速度」。而第三個khanec就非常委婉且有暗示性,指可被阻絕、斷去的重要通道,例如「斷你生路」。 Khanichesse的意思則是「上吊自殺」。好了,馬欽當蘇珊娜的助手,在她廚房兼工廠和店裡幫忙,她架子上有香腸、聖物、護身符和祈禱書。蘇珊娜拒 絕了他,而馬欽惡毒報復的法子,是把祕方偷賣給一個goy。顯然,這goy不懂它的價值,因蘇珊娜死後(遙遠以前的事),市面上就找不到這祖傳的鵝香腸 了。因這令人厭惡的報復,馬欽叔就被開除「叔」級了。
最古最古,充滿惰性,籠罩在層層傳說之下的是那令人難以相信,化石級的巴伯布拉敏,來自切里的我外婆的叔叔。很年輕時他就很富裕,從貴族手上,買了很多切 里附近的農地。親戚靠他,吃喝跳舞旅行浪費了他不少錢。有天,他媽米爾卡(女王)姨病了,和丈夫吵了很久,終於決定僱個haverta做女佣。之前,她有 先見之明,總是拒絕家裡有其他女人。果然,巴伯布拉敏愛上這haverta,也許這是他第一個有機會遇上的可愛女人。
她名字沒傳下來,但德性大家知道一些。她豐滿而美麗,有雙壯觀的khlaviod(乳房):這詞在古希伯來文沒有,那時khalav指「牛奶」。她當然是 個goya,傲慢無禮,不識字,但燒一手好菜。她是個農家女,在家裡打赤腳。但這就是我叔叔愛死的地方:她的腳踝,直率的言語,和她的菜。他和女孩沒說什 麼,但告訴他父母他要娶她。他雙親馬上發狂,叔叔就躺上床。他就留在床上22年。
那麼多年布拉敏做什麼呢?有很多說法。毫無疑問,大多時候,他把日子花在睡覺和賭錢。據說,他經濟狀況垮掉是因為「他沒夾好」債券,或因為他信任一個 mamser(雜種)管理他的農場,那人把它賤價賣給自己的同伙。米爾卡姨完全料中,我叔叔就這樣把全家拖垮了,到今天他們還為這後果悲嘆。
也據說他在床上讀了不少書,最後也算成了公正有知識的人,在床邊還接見切里名人並仲裁爭執。也聽說,那同一個haverta,也到床上去了。至少我叔叔自 願上床閉關的頭幾年,晚上還會偷溜出去到樓下酒店打彈子。但他總算是在床上待了幾乎四分之一世紀。當米爾卡姨和所羅門叔過世後,他娶了個goya,真的帶 她上了床。到那時,他腿已完全無力站起來。1883年,他死時很窮,但名聲可富,精神也平安。
做鵝香腸的蘇珊娜,是我祖母瑪利亞奶奶的表姊。奶奶留下1870年在相館照的一張膠腫、盛裝打扮的相片。在我小時遙遠的記憶,她是個邋遢、皺皮、暴躁、聾 透了的老太婆。直到今天,不知怎麼搞的,櫥子裡最高架子上還有她的寶貝:黑絲花邊披肩、絲織巾、一個長了四代霉的貂皮手筒、刻有她名字的巨大銀器。好像, 歷經五十年後,她的靈魂還回家來看看。
年輕時,她可是個令很多人傷心的大美女。年紀輕輕她就守寡了,謠傳先祖父受不了她的不貞自殺了。她獨自節儉地帶大3個男孩,令他們讀書。但到年老,她讓步 了,嫁了個天主佬醫生,一個堂皇、寡言、大鬍子的老人。自此以後,她就傾向古怪小氣,雖然年輕時,她像多數美麗被愛的女人一樣慷慨大方。隨著年歲的增長, 她逐漸斷絕家庭溫暖(本來大概就不是很深)。她和醫生住在波街一個陰暗的公寓,冬天只有一個小富蘭克林爐,幾乎暖不了。她不再丟掉任何東西,因為都可能有 用處,連乳酪皮、巧克力箔紙都留著--她用箔紙做銀色小球,好送給教會以「拯救黑人小孩」。也許因害怕自己的選擇錯誤,她輪流去佩俄斯五世街的猶太 scola及聖歐塔維奧教堂做禮拜,她似乎甚至還去告解呢!1928年,她八十多歲過世,一群身著黑衣,邋遢的街坊鄰居為她送終,由一個叫西林柏格夫人的 女巫帶頭。雖然為腎臟病所折磨,奶奶到最後一口氣還小心地骷著西林柏格,怕她找到藏在床墊下的maftekh(鑰匙),偷走manod(錢)和 hafassim(珠寶),後來證實這些東西都是假的。
她死後,她兒子和媳婦氣急敗壞地花了幾星期清理屋裡堆積如山的垃圾。瑪利亞奶奶不分青紅皂白,存下垃圾和寶貝。從雕工複雜的核桃木櫃子裡蹦出成千的臭蟲, 有從沒用過的床單,又有打補釘脫線、薄得透明的床單。地下室中有幾百瓶好酒,都已經變成醋了。他們找到八件醫生全新的大衣,還塞了樟腦丸,但她允許他穿的 唯一那件郤打滿補釘,衣領油膩。
對她,我不記得很多,爸爸喊她媽姆(也用第三人稱),帶著孝意地愛說她的絕事。每星期天早上,爸帶我走路去看瑪利亞奶奶。沿著波街,我們走去,一路爸爸停 下摸摸貓咪,聞聞美食,翻翻舊書。爸爸是工程師,口袋總裝著書,認識所有豬肉販子,因他用計算尺算所買的豬肉。他買時並不輕鬆,並非宗教原因而是迷信。打 破食物禁忌令他不自在,但他愛豬肉,只要看到豬肉店櫥窗,每次都無力抗拒。他嘆一口氣,閉嘴詛咒兩下,以眼角骷我三次,似乎怕我批評或期望我的贊同。
當我們到公寓台階下,父親按鈴,奶奶來開門,他會對她耳朵大喊:「他考第一名!」祖母有點不情願地讓我們進去,帶我們經過一串積滿灰塵、沒人居住的房間, 其中一間有奇怪的儀器,是醫生半棄置的診所。很少看到醫生,我也不想看到他。尤其是自從有次我無意中聽到爸爸告訴媽媽,有人帶口吃的小孩就診,他拿剪刀把 他舌下的筋肉剪掉。當我們到了起居室,奶奶會挖出一盒巧克力,總是同一盒,給我一顆。巧克力已叫蟲咬了,我困窘地趕快藏進口袋裡。
Levi, Primo (prē'mō lā'vē) , 1919–87, Italian writer. A chemist of Jewish descent, Levi was sent to the concentration camp at Auschwitz during World War II. His first memoir, If This Is a Man (1947; also tr. as Survival in Auschwitz) is a restrained yet poignant testimony, devoid of rancor or protest, of the atrocities he witnessed. In his other autobiographical books, The Reawakening (1963; film, 1996) and the dark, posthumously published The Drowned and the Saved (1988), Levi relates the manner in which physical torture and annihilation were accompanied by a process of moral degradation. He stresses that survival was as much a spiritual quest to maintain human dignity as a physical struggle. The Periodic Table (1975), a collection of 21 meditations, each named for a chemical element, draws analogies between a young man's moral formation and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that circumscribe our humanity. Levi's novels include The Monkey's Wrench (1978) and If Not Now, When? (1986). He also wrote short stories, essays, and poetry. He died in a fall that was widely thought a suicide.
Bibliography
See his The Voice of Memory: Interviews 1961–1987 (2001), ed. by M. Belpoliti and R. Gordon; biographies by M. Anissimov (1996, tr. 1998), C. Angier (2002), and I. Thomson (2003).
LEAD: Primo Levi, the writer who fell down the stairwell of his apartment on Saturday in an apparent suicide, was buried today in a simple ceremony attended by family friends and members of Italy's Jewish community.
Primo Levi, the writer who fell down the stairwell of his apartment on Saturday in an apparent suicide, was buried today in a simple ceremony attended by family friends and members of Italy's Jewish community.
About a thousand people attended the funeral, which was followed by burial in the Jewish section of the cemetery in Turin where Mr. Levi lived. His grave was marked with a simple marble headstone giving his name and the dates of his birth and death.
Mr. Levi, who wrote of his experiences as a prisoner at Auschwitz, was 67 years old. He was said to have been depressed over poor health.
ELEMENTS OF A LIFE
Date:Byline:
Lead:
THE PERIODIC TABLE
By PrimoLevi. Translated by Raymond Rosenthal. 233 pp.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6.95.
TO the beginning chemistry student, the periodic table is likely to seem little more than a checkerboard chart of the elements, whose atomic symbols, weights and numbers are so many ciphers to be memorized. To the initiated, however, as one learns from Primo Levi's ''The Periodic Table,'' the Mendeleevian system is poetry, a possible bridge between the world of words and the world of things, and hence an unexpected means of understanding the universe and ourselves.
As Mr. Levi, the Italian writer and chemist, distills these means, they are endlessly metaphorical, as they must be to afford the correspondences he seeks between the otherwise disparate worlds of physical and human nature. The 21 pieces in ''The Periodic Table,'' each named after an element, are, therefore, at one and the same time rigorous ''confrontations with Mother-Matter'' and vividly drawn portraits of human types - analytical ''tales of militant chemistry'' and imaginative probings of personal, social and political experience. It is rare to find such diverse aims in combination, and rarer still to find them so successfully integrated in a contemporary work of literature. Yet that is what we have in this beautifully crafted book, the most recent and in many ways the most original of Mr. Levi's three volumes of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
Text:
Primo Levi is known to American readers, if at all, as the author of ''Survival in Auschwitz.'' That book, an affirmation of lucid, humane intelligence in the face of Nazi barbarism, is one of the truly distinguished works of Holocaust literature and has become something of a classic. It was followed by ''The Reawakening,'' in which the author described his long and bizarre journey home after his liberation from Auschwitz. In his native Italy these volumes, along with several others, have won for Mr. Levi a considerable reputation, but because so little of his work has been available to English readers, he has remained all but unknown here. This situation has now happily changed with Raymond Rosenthal's admirable translation of ''The Periodic Table.''
The book's first piece, ''Argon'' (named for a gas ''so inert, so satisfied with (its) condition'' that it does ''not combine with any other element'') is a homage to the author's Jewish ancestors, themselves a breed apart. Intent on retrieving his innumerable aunts and uncles from a legendary past, Mr. Levi at the same time rescues for posterity snatches of their lost language, a local version of Judeo-Italian that combined Hebrew roots with Piedmontese endings and inflections - ''a skeptical, good-natured speech . . . rich with an affectionate and dignified intimacy with God.'' The revivification of this jargon (which Mr. Levi elsewhere refers to as a kind of ''Mediterranean Yiddish'') and of some of the people who once spoke it is a sizable accomplishment and, in its linguistic precision and playful wit, sets the tone and direction for the pieces that follow.
Like ''Argon,'' these are similarly patterned on analogies between the elements and a variety of human types and develop a mode of imagining reality that is striking in its fusion of physical, chemical and moral truths. To Mr. Levi there are no such things as emotionally neutral elements, just as there are no emotionally neutral men and women. Thus, whether a given story's focus is on friendship, mountain-climbing, early encounters with love or the troubled status of being a Jew in Mussolini's Italy, the author is able to strike a fitting correlation with one of the elements. Mercury, ''always Alvin H. Rosenfeld teaches in the English Department at Indiana University. His ''Imagining Hitler'' will be published in April. restless,'' is ''a fixed and volatile spirit.'' Zinc, by contrast, is ''a boring metal,''''not an element which says much to the imagination'' (it requires the presence of impurities to react, and in Fascist Italy, as Mr. Levi's imagination seizes upon the analogy, the Jew was to be the impurity - in his case, almost proudly so). There are elements, such as iron and copper, that are ''easy and direct, incapable of concealment''; others, such as bismuth and cadmium, that are ''deceptive and elusive.'' The point of these figurations is to revive ''the millennial dialogue between the elements and man'' and to show that in none of its aspects is nature impermeable to intelligence.
The intelligence made manifest throughout this book is a relentlessly inquisitive one, dedicated to understanding the most subtle dimensions of matter and of man. At once analytic and novelistic, it is the intelligence of a writer who has been able to forge an unusual synthesis of scientific learning and poetic sensibility, of rational procedures and moral perceptions. Its aim, therefore, is both to comprehend and to create, and thereby to keep from being victimized by all outward assaults, spiritual as well as material.
In following Mr. Levi in his pursuit of the elements, one comes to see how the insights of the analyst serve to illuminate a wide range of personal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including the author's experiences as an anti- Fascist partisan and his subsequent arrest and incarceration in Auschwitz. To readers of the earlier work, ''Zinc,''''Gold,''''Cerium,''''Chromium'' and ''Vanadium'' will be of particular interest, for they fill in or otherwise expand on episodes recounted in ''Survival in Auschwitz.''''Vanadium,'' the book's penultimate story and its most dramatic one, for instance, vividly describes an uncanny correspondence that Levi had after the war with a Dr. M"uller, a German chemist who turns out to have been the chief of the laboratory in Auschwitz where, in 1944, the author slaved to stay alive. The confrontation in this story strikes to the heart of Mr. Levi's subject and shows him at his contemplative best - putting the questions, pondering their manifold implications and reaching a resolution that is both rigorous and humane.
Indeed, for all of its musings upon the enigmas of matter, ''The Periodic Table'' is best read as a historically situated book and will mean most to those readers who are alert to the mind's engagements with moral as well as physical truths. Thus ''Iron,'' dedicated to Sandro Delmastro, a fellow chemistry student (and the first Resistance fighter to be killed in the Piedmont), is primarily about the nobility of friendship, as ''Phosphorus'' is more a tale of sexual attraction than it is an anatomy of life in the laboratory. Both pieces, set in the 1940's, have far more to do with the vagaries of human relationships under the Italian racial laws than with the laws of chemistry.
The real attraction of ''The Periodic Table,'' therefore, lies in the author's ability to probe human events with as much discriminating power as he probes nature and in his refusal to surrender the sovereignty of independent inquiry to either stolid matter or a stupid and savage politics. If one sees the book in this way, it is not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how chemistry became for Mr. Levi as much a ''political school'' as a trade and how its terms might be grasped as an ''antidote to Fascism . . . because they were clear and distinct and verifiable at every step, and not a tissue of lies and emptiness.''
FOR all of its immersion in the most wrenching of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The Periodic Table'' is not an angry or a brooding book. On the contrary, it is a work of healing, of tranquil, even buoyant imagination. The meditative power of ''Survival in Auschwitz'' and ''The Reawakening'' is fully evident but is joined by a newly acquired power of joyful invention. No doubt every chemist is a bit of a wizard (as every writer wants to be) and looks to extract gold from gangue, though few manage to do so. By descending deep into the matrix of both physical and human nature, Primo Levi seems to have learned the secrets behind such transformations, and he has written what can only be described as a liberating book.
To see just how liberating, read ''Carbon,'' the concluding story, a wondrous tale of a single atom of carbon that traverses the universe, courses through the intricate processes of photosynthesis and comes to rest almost magically at the tip of the author's pen. What that pen has wrought with these stories as the result of that imperceptible but vital element is a new opening on to life, and one that validates the point of the Yiddish proverb used as an epigraph for the book: ''Ibergekumene tsores iz gut tsu dertseylin'' (''Troubles overcome are good to tell'').B
DRIVEN TO WRITE BY THE UNEXPECTED Primo Levi says he is ''a chemist by conviction'' and never expected to become a writer. What drove him to write was his time in Auschwitz. ''After Auschwitz, I had an absolute need to write,'' he says. ''Not only as a moral duty, but as a physiological need.'' Mr. Levi was sent to Auschwitz after he was arrested in Italy's Piedmont region for Resistance activities and discovered to be a Jew. He emphasizes that the persecution of Jews in Italy was largely imposed by the Nazis, who invaded the country after Mussolini's fall, and that Mussolini's own anti-Semitic laws were frequently flouted. ''Italians never liked laws, either then or now,'' recalled the 65-year old author in a telephone interview from his home in Turin. ''And so, during the racial law period, it became a matter of glory for a Christian to have a Jewish friend.''''Survival in Auschwitz'' did not really become successful until it was reissued in 1957. ''After the success,'' Mr. Levi notes, ''I accepted the advice of several friends who said, 'why not continue your story?'''''The Reawakening'' described what followed Auschwitz for him. ''I was liberated by the Russians who saved my life. But after saving my life, (they) deported me to Russia with the other prisoners.'' Ironically, Mr. Levi's two works of science fiction have only been translated into two languages - German and Russian. Through it all, the author had stuck to his chemistry. But he says he could only write ''The Periodic Table'' after his retirement from the field. ''I wanted to describe to the nonprofessional what it's like to be a chemist,'' he says. ''Every element brings a kind of 'click' for me. It triggers a memory.'' - E. J. Dionne
翻譯李維
.牟中原
《週期表》這本書的翻譯工作,跟了我有6年了,真久!如今終於交稿,即將問市,如釋重負。
1992年夏,大學聯考,我入闈場工作。等考題定稿,校閱安畢後,有7天無事而失去行動自由的時間。當時帶了李維的《週期表》英文版作為讀物,順手也就開 始翻譯,純為好玩,打發時間,當時也沒想到要出版。多年來,研究工作是越來越忙,越起勁,翻譯的事也就斷斷續續,算是自娛吧!但每次重新開動,整個稿子又 重改一次,前後也三易其稿了。直到去年底,讓老友林和知道手頭上有這本書的八成譯稿,他好心幫忙聯絡出版,這才終於下了決心收拾這沒完沒了私祕譯作。
譯完了,該說些什麼?實在不多,因我理想中的譯者應該只留下譯文,不作其他文章,來指導讀者,提供意見。但這好像不是西洋文學中譯的傳統。
傅雷雖然說「在一部不朽的原作之前,冠上不倫的序文是件褻瀆的行為」,但他通常還是寫了「譯序」。楊絳譯《堂吉訶德》寫了23頁的譯者序。韓少功譯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也有11頁的序。意見都不少。
其實譯者大約都知道翻譯文學本身就是件「訊息轉折」的工作,沒法完全跨越語言的鴻溝,最多只能說神似罷了。《週期表》原著是義大利文,我不懂義文,根據的 是Raymond Rosenthal的英譯本。作為一個化學家,我知道我可以不讀德文原著,而從英文譯本完全了解化學專著,因為大家有共通的化學術語及基本原理。但《週期 表》不是關於化學知識的傳述,李維的語言是文學的,回憶的,沉思的,我終究是沒法確定譯文和原文的差異,而我很好奇這點。這其實是寫這短文的目的,希望有 人有興趣根據義大利文再譯一次,到時這譯本也就可放一邊了。
作者李維本人其實是相當在意翻譯文字的,他在納粹集中營的回憶錄《奧茲維茲殘存》 (Survival in Auschwitz) 第一次譯成德文時,非常緊張。「我害怕我的文字會喪失原色,失掉涵義……看到一個人的思想被扭曲、打折,他挖空心思的用詞被誤解、轉換。」就因此,他的著作的英譯本都是非常小心進行的,Rosenthal成為李維後來大部份著作的英譯者,並因此而得翻譯獎。
有意思的是,李維本人也從事譯作,他是卡夫卡《審判》義大利文版譯者。我也很好奇,他的譯文能否保留卡夫卡文字特殊的稜角?
看樣子,這些翻譯「忠實」的問題真是沒解,尤其小國家(如捷克)文學的翻譯多只能從英文或法文轉譯,這更沒法說了。
但我想翻譯真正要做的是居中負起不同語言,不同文化的溝通工作。我們讀《週期表》這樣的書是嚮往一種整體文化,在那兒「科學」和「文學」並不割裂,而語言 可以穿透國度。化學家這行業的故事是可以欣賞,了解的。「集中營」的極端殘忍,雖無法以文字描述,但我們仍然要反覆聽殘存者的聲音。這些文化的整體感是可 以透過翻譯傳達的。
《週期表》一書不止是李維的自傳,他這行業的記錄,更是他那一代的故事。透過化學元素的隱喻,科學式的文筆,他寫下自己和他周圍一群人的遭遇,及他的冥想 和反思。《週期表》是一本很難分類的書,很難用簡單幾句話描述它。李維的吸引力在於他所傳遞的整體感,他的世界裡每樣事都奇妙地連接在一起。
於台灣大學化學系
1998年6月24日
1992年夏,大學聯考,我入闈場工作。等考題定稿,校閱安畢後,有7天無事而失去行動自由的時間。當時帶了李維的《週期表》英文版作為讀物,順手也就開 始翻譯,純為好玩,打發時間,當時也沒想到要出版。多年來,研究工作是越來越忙,越起勁,翻譯的事也就斷斷續續,算是自娛吧!但每次重新開動,整個稿子又 重改一次,前後也三易其稿了。直到去年底,讓老友林和知道手頭上有這本書的八成譯稿,他好心幫忙聯絡出版,這才終於下了決心收拾這沒完沒了私祕譯作。
譯完了,該說些什麼?實在不多,因我理想中的譯者應該只留下譯文,不作其他文章,來指導讀者,提供意見。但這好像不是西洋文學中譯的傳統。
傅雷雖然說「在一部不朽的原作之前,冠上不倫的序文是件褻瀆的行為」,但他通常還是寫了「譯序」。楊絳譯《堂吉訶德》寫了23頁的譯者序。韓少功譯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也有11頁的序。意見都不少。
其實譯者大約都知道翻譯文學本身就是件「訊息轉折」的工作,沒法完全跨越語言的鴻溝,最多只能說神似罷了。《週期表》原著是義大利文,我不懂義文,根據的 是Raymond Rosenthal的英譯本。作為一個化學家,我知道我可以不讀德文原著,而從英文譯本完全了解化學專著,因為大家有共通的化學術語及基本原理。但《週期 表》不是關於化學知識的傳述,李維的語言是文學的,回憶的,沉思的,我終究是沒法確定譯文和原文的差異,而我很好奇這點。這其實是寫這短文的目的,希望有 人有興趣根據義大利文再譯一次,到時這譯本也就可放一邊了。
作者李維本人其實是相當在意翻譯文字的,他在納粹集中營的回憶錄《奧茲維茲殘存》 (Survival in Auschwitz) 第一次譯成德文時,非常緊張。「我害怕我的文字會喪失原色,失掉涵義……看到一個人的思想被扭曲、打折,他挖空心思的用詞被誤解、轉換。」就因此,他的著作的英譯本都是非常小心進行的,Rosenthal成為李維後來大部份著作的英譯者,並因此而得翻譯獎。
有意思的是,李維本人也從事譯作,他是卡夫卡《審判》義大利文版譯者。我也很好奇,他的譯文能否保留卡夫卡文字特殊的稜角?
看樣子,這些翻譯「忠實」的問題真是沒解,尤其小國家(如捷克)文學的翻譯多只能從英文或法文轉譯,這更沒法說了。
但我想翻譯真正要做的是居中負起不同語言,不同文化的溝通工作。我們讀《週期表》這樣的書是嚮往一種整體文化,在那兒「科學」和「文學」並不割裂,而語言 可以穿透國度。化學家這行業的故事是可以欣賞,了解的。「集中營」的極端殘忍,雖無法以文字描述,但我們仍然要反覆聽殘存者的聲音。這些文化的整體感是可 以透過翻譯傳達的。
《週期表》一書不止是李維的自傳,他這行業的記錄,更是他那一代的故事。透過化學元素的隱喻,科學式的文筆,他寫下自己和他周圍一群人的遭遇,及他的冥想 和反思。《週期表》是一本很難分類的書,很難用簡單幾句話描述它。李維的吸引力在於他所傳遞的整體感,他的世界裡每樣事都奇妙地連接在一起。
於台灣大學化學系
1998年6月24日
化學世界裡的詩意
.蕭勝明
《週期表》,出版不到兩個月就被朋友大力推薦,趕緊買來閱讀了。卻一直不知道怎麼下筆介紹這本書。
初聽到這個名字,誰能不馬上反射性想到門德列夫的化學元素週期表呢。記得天下文化曾出版一本使用淺近語言,跟一般讀者介紹週期表的書,輕輕鬆鬆歷歷數來, 化學概念卻建立得清清楚楚。比起國高中化學教科書來,要有趣多了。看時報將這本書列為「科學人文類」,本以為也是如此「大眾科學」的書,誰知全然不是這麼 回事。
書名標榜「週期表」,只因作者普利摩‧李維本職是化學家,轉借十多種化學元素特質,比喻自己人生經歷某些值得以螢光筆鮮明標點的段落。幾個元素並列,隱然 是自己生命小小的週期表。實在是數篇自傳式的小說,跟科學、化學原理根本毫不相罕。被胡亂編派到曖昧的所謂「科學人文」來,真不曉得說什麼才好。
李維原文以義大利文寫成,譯者牟中原自英譯本轉譯,雖然轉了兩手,原味相信畢竟還是留存了許多。雖是化學家,經歷反法西斯諸戰爭,他猶然執著把思想心念化 成文字,以散文、詩、戲劇、小說等不斷發表出來,獲得諸多文學獎。換言之,「化學家」和「文學家」同樣是他的身分,沒有孰輕孰重,更不需要互相幫襯。
王浩威對本書的「導讀」裡寫得明白:在 1994 年,米蘭慶祝義大利脫離法西斯政權 49 週年,其中一則標語只寫了「勿忘 174517」幾個字。原來,174517就是李維當年淪落奧茲維茲集中營時的個人編號。可以想像,在義大利,李維是個家喻戶曉的文學作家,否則誰知道那 寥寥幾字暗示了什麼?李維的文學造詣未能被出版界肯定,被隱藏在科普書裡才得以介紹到台灣,實在是一大憾事。
相同的,由於李維與卡爾維諾都出生於杜林(都靈),不論中譯本封底和王浩威的「導讀」,都提到「卡爾維諾對李維十分推崇」云云。卡爾維諾目前已是台灣讀者 人人熟知的文學大師,「推崇」一語,倒像是李維必須得到卡爾維諾「加持」後,才能得到台灣讀者的肯定似的。這實在是過慮了。我想,李維自身的文學功力,便 足以使人信服。
王浩威的「導讀」裡,將書中『原子序』作了幾個區分。第一章「氬」追溯祖先脈絡;由「磷」到「鈰」各章記述他失去自由後的囚禁;從「鉻」至「釩」漫談戰後 一切、告別浪漫面對現實的轉變;最後一章的「碳」幾乎是地球萬物化合的終極形式,用來代表人生最後永恆的平靜。這樣的解剖十分有趣,值得作為參考。在這樣 簡短概述後,大家不難了解整本書的脈絡所在。
李維對各章節所取的代表元素,有的取其性質以為內容的暗喻,有的是事件過程的主角,也有兩三個是李維寓言小故事裡的事物本質金屬等。比如,第二章的 「氫」,就描述了李維年少時迷戀化學世界的往事。 那時他與伙伴,對實驗室裡種種化學反應,感到十分興奮神奇。用了氨水和硝酸想製造笑氣(氧化亞氮),不懂混合比例而失敗了。李維沮喪之餘發現乾電池,改玩 「電解水使氫氧分離」的遊戲(我們在中學時代都實驗過的,是不?),果然成功製出並收集了氫與氧,同時藉氣體體積恰成兩倍,驗證定比定律。伙伴反問:電解 前為了讓水易解離,加了少許的鹽。怎知製出來的氫中沒有混雜氯氣?李維正當年少氣盛,二話不說,在倒置收集氣體的空果醬瓶口,點根火柴湊上前去。果醬瓶登 時「砰」然爆裂,只剩一圈瓶口在手上。
若只是平實記載「童年往事」,那麼李維這本《週期表》就只是化學家自戀的流水帳,沒什麼值得驚異處。但李維不只追憶過去而已。在最後一段,李維這麼寫道:
初聽到這個名字,誰能不馬上反射性想到門德列夫的化學元素週期表呢。記得天下文化曾出版一本使用淺近語言,跟一般讀者介紹週期表的書,輕輕鬆鬆歷歷數來, 化學概念卻建立得清清楚楚。比起國高中化學教科書來,要有趣多了。看時報將這本書列為「科學人文類」,本以為也是如此「大眾科學」的書,誰知全然不是這麼 回事。
書名標榜「週期表」,只因作者普利摩‧李維本職是化學家,轉借十多種化學元素特質,比喻自己人生經歷某些值得以螢光筆鮮明標點的段落。幾個元素並列,隱然 是自己生命小小的週期表。實在是數篇自傳式的小說,跟科學、化學原理根本毫不相罕。被胡亂編派到曖昧的所謂「科學人文」來,真不曉得說什麼才好。
李維原文以義大利文寫成,譯者牟中原自英譯本轉譯,雖然轉了兩手,原味相信畢竟還是留存了許多。雖是化學家,經歷反法西斯諸戰爭,他猶然執著把思想心念化 成文字,以散文、詩、戲劇、小說等不斷發表出來,獲得諸多文學獎。換言之,「化學家」和「文學家」同樣是他的身分,沒有孰輕孰重,更不需要互相幫襯。
王浩威對本書的「導讀」裡寫得明白:在 1994 年,米蘭慶祝義大利脫離法西斯政權 49 週年,其中一則標語只寫了「勿忘 174517」幾個字。原來,174517就是李維當年淪落奧茲維茲集中營時的個人編號。可以想像,在義大利,李維是個家喻戶曉的文學作家,否則誰知道那 寥寥幾字暗示了什麼?李維的文學造詣未能被出版界肯定,被隱藏在科普書裡才得以介紹到台灣,實在是一大憾事。
相同的,由於李維與卡爾維諾都出生於杜林(都靈),不論中譯本封底和王浩威的「導讀」,都提到「卡爾維諾對李維十分推崇」云云。卡爾維諾目前已是台灣讀者 人人熟知的文學大師,「推崇」一語,倒像是李維必須得到卡爾維諾「加持」後,才能得到台灣讀者的肯定似的。這實在是過慮了。我想,李維自身的文學功力,便 足以使人信服。
王浩威的「導讀」裡,將書中『原子序』作了幾個區分。第一章「氬」追溯祖先脈絡;由「磷」到「鈰」各章記述他失去自由後的囚禁;從「鉻」至「釩」漫談戰後 一切、告別浪漫面對現實的轉變;最後一章的「碳」幾乎是地球萬物化合的終極形式,用來代表人生最後永恆的平靜。這樣的解剖十分有趣,值得作為參考。在這樣 簡短概述後,大家不難了解整本書的脈絡所在。
李維對各章節所取的代表元素,有的取其性質以為內容的暗喻,有的是事件過程的主角,也有兩三個是李維寓言小故事裡的事物本質金屬等。比如,第二章的 「氫」,就描述了李維年少時迷戀化學世界的往事。 那時他與伙伴,對實驗室裡種種化學反應,感到十分興奮神奇。用了氨水和硝酸想製造笑氣(氧化亞氮),不懂混合比例而失敗了。李維沮喪之餘發現乾電池,改玩 「電解水使氫氧分離」的遊戲(我們在中學時代都實驗過的,是不?),果然成功製出並收集了氫與氧,同時藉氣體體積恰成兩倍,驗證定比定律。伙伴反問:電解 前為了讓水易解離,加了少許的鹽。怎知製出來的氫中沒有混雜氯氣?李維正當年少氣盛,二話不說,在倒置收集氣體的空果醬瓶口,點根火柴湊上前去。果醬瓶登 時「砰」然爆裂,只剩一圈瓶口在手上。
若只是平實記載「童年往事」,那麼李維這本《週期表》就只是化學家自戀的流水帳,沒什麼值得驚異處。但李維不只追憶過去而已。在最後一段,李維這麼寫道:
我們離開,邊走邊討論。我的腿有點發抖,同時感到事後的戰慄和愚蠢的驕傲。我釋放了一個自然力,也證實了一項假說。是氫沒錯,和星星太陽裡燃燒的元素一樣。它的凝聚產生了這永恆而孤寂的宇宙。」(頁 25)加 了最後這一小段,整篇故事的思索縱深就廣大了起來。電解製得的氫,不只是少年時的胡鬧而已。它和宇宙星辰太陽們燃燒的能源是一樣的,而李維輕易就取得了 它,並自果醬瓶的炸裂窺見其中巨大的能量。無怪乎,他要覺得敬畏歎息,立志要投身化學世界了。也因投身化學界,才牽扯出隨後每個元素人生故事來,恰如氫是 宇宙中最簡單也最根本的始基元素一樣。
《週期表》這本書,沒有承載什麼了不得的道理。但是,許多人讀了它,也被它感動。因為,李維人生中的呼息與誠懇,在字裡行間時時可見。這些呼息與誠懇,又 和代表元素序列的巧思完美扣合,使人訝然發現:原來單純的元素裡,也可想見如此有情世界。我想,這就是《週期表》成功獨到的地方罷。
倖存者的聲音
.王浩威
97年初夏,到義大利水上之都參觀威尼斯雙年展。
結束了比安那列舉辦的頒獎觀禮後,離開這個過度擁擠的第一展覽會場,一群朋友走到舊日造船廠改建的第二會場。
1893年開始的威尼斯雙年展,曾經是未來派的大本營,希特勒痛斥為墮落藝術的討伐對象;到了二次大戰後,原本秉持世界一同的良意,比安那列區舊別館再加 上新設計的建築,都擁有了自己的國名,彷如聯合國般充斥著另一種國家主義。舊造船廠改成的第二會場,以大會主動邀約的藝術家為主,國家的旗幟終於消失。
我們一群人先出了第二會場,沿水道旁的巷子漫步,而後隨意找了一家平常小館,簡單進食。一位同行的義大利藝術家聊起了文學和藝術的關係,他說其實義大利一直都很重視文字的。他本身是位化學家,經營了一家化學工廠,卻是長期支持前衛藝術,包括蒐購和寫評論。
雖然一起走了好長一段路,我才終於有機會認識他,不禁問:「你的情形,跨界搞文藝的化學家,不就像普利摩.李維一樣嗎?」
他忽然一陣驚訝,問道:在台灣,有他的作品翻譯出版嗎?然後就滔滔不絕地說李維是多麼棒的作家,他的敏銳心思,他真誠的文學態度,當然,也談到了他的自殺帶來的遺憾。
1992年3月12日的晚上,普利摩.李維去世近五年左右,羅馬的街頭出現了長長的火炬隊伍,上千的火光在黑夜中前進。他們的聚集是反對義大利境內逐年崛 起的種族主義和新納粹風氣,特別是近年橫行的光頭族。在小巷口,一幅長長拉開的抗議布條只簡單寫著幾個數字:174517。
1994年4月25日,二十萬人聚會在米蘭慶祝義大利脫離法西斯政權四十九週年,其中一幅搶眼的旗幟寫著:「勿忘174517」。
174517,一個乍看毫無意義的隨機數字,在二次大戰尚未結束的1944年2月,赤裸裸地火烙在普利摩.李維的肌膚上。當時他才從一列囚禁的火車走下月 台。這是前後一年總共載送幾千人的許多次列車的其中一次。500個人從義大利Fossoli監獄送到德國日後惡名昭彰的「奧茲維茲」集中營。車上有29名 婦女和95名男子被挑上,依序烙印,編號174471到174565,而174517只是其中一號。剩下的400人,老幼婦孺等等,人數很龐大,處理卻很 簡單,直接送入瓦斯室處死。
人類歷史上最悲痛記憶的所在地奧茲維茲營,1943年底設立。當時納粹德國年輕人力投入了戰場,工廠人手急迫缺乏,於是一個徹底利用人力的集中營出現了。 二次大戰期間,在義大利境內有8000名猶太人被送出境,6000名送到奧茲維茲,只有356名在戰後生還回到故鄉。李維,這位被編號為174517的囚 犯,日後在美國小說家Philip Roth的訪談裡表示,他的倖存是一大堆因素賜予的,主要包括他的遲遲被捕,他適合這個強迫勞役制度的要求,當然,最重要的純屬幸運而已。
奧茲維茲的大門就刻著這樣的字句:Arbeit Macht Frei,勞動創造自由。1919年7月31日出生的李維,抵達奧茲維茲時是25歲。他被挑出來的原因,最先是年輕力壯的肉體,後來是他化學家的專長;最 後,當德國開始戰敗,健康囚犯都被強制撤離和謀殺時,他卻正因腥紅熱侵襲奄奄一息,被丟棄在營中而倖存。
這許多幸運的偶然,這樣微小的生存機率,在和死神不斷擦身而過的過程,倖存的人,包括李維,也就成為一個永遠無法相信生命的困惑者,卻又勢必扮演這一切災難的目擊證人。
和台灣讀者所熟悉的卡爾維諾一樣,李維從出生以來,一直都是在杜林。30年代的作家,也是文壇精神領袖帕維瑟,將卡爾維諾引進文壇,介紹到最重要的文化出 版社埃伊瑙迪(Einaudi)工作和出書。相反的,同樣是杜林人,同樣二次戰後寫作,只比卡爾維諾大四歲的李維,卻沒有這樣的一份幸運。一方面,戰後回 到杜林的他,就像《週期表》裡寫的,在這個近乎廢墟的城郊找到了一份工廠化學家的工作,也就少與杜林文人圈來往。然而,更重要的原因卻是他作品中的絕望和 憤怒。
在奧茲維茲的絕望處境裡支持他活下去的,就是盼望扮演這場悲劇見證人的決心。他將觀察和感受陸續寫在紙上,然後一一銷燬,只留在腦海而避免遭發現。
回到杜林,他和另一位同是倖存者的醫師Leonardo de Benedetti揭開集中營如何虐待和摧毀人體的科學報告,刊在醫學期刊。1947年,他開始在《人民之友》週刊發表有關集中營的文章。完整手稿分別給 了埃伊瑙迪、帕維瑟和金芝柏夫人(Natalia Ginzburg),反應極佳,可是埃伊瑙迪的出版社都沒興趣,最後是一家小出版社草草發行,第一版滯銷而庫存在佛羅倫斯的地下倉庫,某年水災全遭淹漬。
二次大戰後,乃至到了今天,人們一直不願去回想大屠殺這類的記憶,這一切歷史事件證明了人性可能的殘酷,既不僅屬於少數幾個民族,也不是人類的文明演化可 以消除的,而是永遠地,永遠地存在像你我這樣的所謂平凡或善良老百姓的潛意識深處。李維喊出來了,大家的痛處卻被觸及了,即使是良心知識分子也都有意無意 地迴避而不積極歡迎它的出版。
《如果這是個人類》在被拒十年後,1958年才由埃伊瑙迪出版。
50年代末期,二次大戰的災難還距離不遠,經歷過法西斯、戰爭、死亡和集中營的一代,發覺部份新一代歐洲青年開始投入當年的思考模式,新法西斯和新納粹風 潮開始蠢蠢欲動。學校的教科書還停留在過去,課本裡的歷史只記錄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因為這樣的發展,原先指望以遺忘作為原諒的文化界,才開始恐慌起來,許 多二次大戰期間的資料,包括《安妮的日記》在內,終於得以發行。初版才兩千冊的《如果這是個人類》,直到1987年為止,共售出75萬冊。
在《如果這是個人類》裡,集中營的主題一直持續著,聲音是憤怒和見證的;到了《復甦》,分貝開始下降,思考更加複雜。他的反省不再是只有少數的「壞人」,而是包括猶太人在內的集體的道德責任,恥辱和罪疚成為一再盤旋的主題。
《復甦》的「恥辱」一章最先完成於1947年,關於「所謂正直的人在他人果真做下錯事以前,早己隱約感到恥辱」的主題,到40年後他在死前發表的最後一本 重要作品《被溺斃的和被救活的》,進一步發展成對倖存者更深遠的分析,特別是他們的罪疚和恥辱。罪疚是指在某些場合中,儘管主動選擇的可能性將是渺小的, 但還是有可能時,倖存者對自己的沒有抵抗和沒有救助他人(雖然當時的情況根本不可能)而永遠承受自責。恥辱既是個人也是集體的。倖存者必須個別地承受別人 質疑的眼神:為甚麼人都死了而你還活著,同時也承受著集體的恥辱:我居然也是屬於這般禽獸的人類的其中一分子。
在這樣複雜的思考和分析後,李維開始肯定為何有些人在承受囚禁和侮辱時,可以勇敢活下來,在自由之後反而自行結束生命。他說:「自殺的行徑是人性的而不是 動物的,它是縝密思考的舉止,不是衝動或不自然的選擇。」奧地利籍哲學家Hans Mayer(別名Jean Amery)在1978年自殺,生前寫了一篇「奧茲維茲的知識份子」,警告下一代一定要抗拒冷漠和不在乎。李維在書中,也用了一整個章篇來討論這問題,結 論都是悲觀而不確定的。
這本書出版的同一年,1986年6月,奧地利前納粹分子華德翰(Kurt Waldheim)當選為該國總理,引起歐洲知識分子的一片憤怒和辯論;當然,義大利也不例外。李維在他的聖經背後寫了一首詩:
如果沒有多少的改變也不要怯懦了。/我們需要你,雖然你只是較不疲累罷了。/……再想想我們所犯的錯吧:/在我們之間有一些人,/他們的追尋還是瞎眼地出 發,/像是矇上眼布的人憑依摸索。/還有些人海盜般出航;/有些人努力繼續堅持好心腸。/……千萬別驚駭了,在這廢墟和垃圾的惡臭裡:/我曾經赤手清除這 一切,/就在和你們一樣的年紀時。/維持這樣的步伐,盼望你可以做到。/我們曾經梳開慧星的髮叢,/解讀出天才的秘密,/踏上月球的沙地,/建立奧茲維茲 和摧毀廣島。/瞧,我們並不是啥都不動的。/扛上這負擔吧,繼續現在的困惑。/千萬啊,千萬不要稱我們為導師。
這一年的年底,李維再次陷入嚴重的憂鬱症。1987年年初,在最後的一次訪問裡,他說:「過去和現在的每一刻,我總覺得要將一切都說出來……我走過迢迢的 混亂,也許是和集中營經驗有關。我面對困難的情形,慘透了。而這些都是沒寫出來的。……我不是勇敢強壯的。一點也不是!」
3月,他連續兩次前列腺手術,生理的惡化讓憂鬱症更沈重。4月8日清晨,義大利國家電視台的新聞,宣稱普利摩.李維從他家的三樓墜落死亡。
普利摩.李維不僅是奧茲維茲的倖存者,不止是書寫集中營的回憶和反思。
1995年9月,旅途行中路過倫敦,遇見了在英國遊修科學史的朋友。他說,最近才因為課堂老師的介紹,讀完一本棒極了的書《週期表》。從薩爾茲堡搭車到蘇黎士,再搭機到倫敦的途中,我也就再買一本《週期表》。
李維從沒失去他出身的化學本行。只是,在人的問題和化學的科學之間,身為科學家的他不再是看不見的觀察者,所有所謂客觀的科學都開始有了主觀的故事和歷史。李維用人文的眼神凝視科學,顛覆了幾百年在科學與人文的爭執中,永遠只有科學在打量著人文的處境。
他曾經寫詩、寫評論,也寫過完全符合嚴格西方定義的長篇小說:《如果不是現在,又何時?》。然而,大多的評論家公認《週期表》是他最成功的文學創作。這本 1975年出版的「小說」,在濃厚的自傳色彩中將化學元素化為個人的隱喻,彷如也是宣告他的記憶開始努力從集中營的經歷中再回到一切還沒發生的原點。
第一章的氬開始追溯祖先的脈絡,從古老猶太傳統到杜林的定居,而李維是最後登場的一個角色。從氫到鋼,李維渡過了他的青春期到第一份差事。這是《週期表》的第一部份,也是最愉快的人生,他發現了自己擁有傾聽的能力,而別人也有告訴一切的意願。
第二階段是磷到鈰,從他失去自由到Lager(營)處的囚禁。第三階段則是鉻到釩,談及戰後的一切,在重新適應原來城市的過程,已經失去了昔日用浪漫眼光看待化學的悠哉了。他必需面對現實的需要,重新架構自己的價值觀和視野。
碳出現在最後倒數的階段,一種「時間不再存在」的元素,是一種「永恆的現在」。特別是,李維指出,這樣的平衡狀態將導致死亡。碳和人類的肉體是不同的,它 擁有永恆的質性,李維選擇它暗喻自己化學生涯的結束和作家身分的重生,卻也不知不覺地預言了在面對創傷記憶的漫長奮鬥後,四十年的煎熬渡過了,最後還是選 擇了一種永遠平靜下去的結束。
結束了比安那列舉辦的頒獎觀禮後,離開這個過度擁擠的第一展覽會場,一群朋友走到舊日造船廠改建的第二會場。
1893年開始的威尼斯雙年展,曾經是未來派的大本營,希特勒痛斥為墮落藝術的討伐對象;到了二次大戰後,原本秉持世界一同的良意,比安那列區舊別館再加 上新設計的建築,都擁有了自己的國名,彷如聯合國般充斥著另一種國家主義。舊造船廠改成的第二會場,以大會主動邀約的藝術家為主,國家的旗幟終於消失。
我們一群人先出了第二會場,沿水道旁的巷子漫步,而後隨意找了一家平常小館,簡單進食。一位同行的義大利藝術家聊起了文學和藝術的關係,他說其實義大利一直都很重視文字的。他本身是位化學家,經營了一家化學工廠,卻是長期支持前衛藝術,包括蒐購和寫評論。
雖然一起走了好長一段路,我才終於有機會認識他,不禁問:「你的情形,跨界搞文藝的化學家,不就像普利摩.李維一樣嗎?」
他忽然一陣驚訝,問道:在台灣,有他的作品翻譯出版嗎?然後就滔滔不絕地說李維是多麼棒的作家,他的敏銳心思,他真誠的文學態度,當然,也談到了他的自殺帶來的遺憾。
1992年3月12日的晚上,普利摩.李維去世近五年左右,羅馬的街頭出現了長長的火炬隊伍,上千的火光在黑夜中前進。他們的聚集是反對義大利境內逐年崛 起的種族主義和新納粹風氣,特別是近年橫行的光頭族。在小巷口,一幅長長拉開的抗議布條只簡單寫著幾個數字:174517。
1994年4月25日,二十萬人聚會在米蘭慶祝義大利脫離法西斯政權四十九週年,其中一幅搶眼的旗幟寫著:「勿忘174517」。
174517,一個乍看毫無意義的隨機數字,在二次大戰尚未結束的1944年2月,赤裸裸地火烙在普利摩.李維的肌膚上。當時他才從一列囚禁的火車走下月 台。這是前後一年總共載送幾千人的許多次列車的其中一次。500個人從義大利Fossoli監獄送到德國日後惡名昭彰的「奧茲維茲」集中營。車上有29名 婦女和95名男子被挑上,依序烙印,編號174471到174565,而174517只是其中一號。剩下的400人,老幼婦孺等等,人數很龐大,處理卻很 簡單,直接送入瓦斯室處死。
人類歷史上最悲痛記憶的所在地奧茲維茲營,1943年底設立。當時納粹德國年輕人力投入了戰場,工廠人手急迫缺乏,於是一個徹底利用人力的集中營出現了。 二次大戰期間,在義大利境內有8000名猶太人被送出境,6000名送到奧茲維茲,只有356名在戰後生還回到故鄉。李維,這位被編號為174517的囚 犯,日後在美國小說家Philip Roth的訪談裡表示,他的倖存是一大堆因素賜予的,主要包括他的遲遲被捕,他適合這個強迫勞役制度的要求,當然,最重要的純屬幸運而已。
奧茲維茲的大門就刻著這樣的字句:Arbeit Macht Frei,勞動創造自由。1919年7月31日出生的李維,抵達奧茲維茲時是25歲。他被挑出來的原因,最先是年輕力壯的肉體,後來是他化學家的專長;最 後,當德國開始戰敗,健康囚犯都被強制撤離和謀殺時,他卻正因腥紅熱侵襲奄奄一息,被丟棄在營中而倖存。
這許多幸運的偶然,這樣微小的生存機率,在和死神不斷擦身而過的過程,倖存的人,包括李維,也就成為一個永遠無法相信生命的困惑者,卻又勢必扮演這一切災難的目擊證人。
和台灣讀者所熟悉的卡爾維諾一樣,李維從出生以來,一直都是在杜林。30年代的作家,也是文壇精神領袖帕維瑟,將卡爾維諾引進文壇,介紹到最重要的文化出 版社埃伊瑙迪(Einaudi)工作和出書。相反的,同樣是杜林人,同樣二次戰後寫作,只比卡爾維諾大四歲的李維,卻沒有這樣的一份幸運。一方面,戰後回 到杜林的他,就像《週期表》裡寫的,在這個近乎廢墟的城郊找到了一份工廠化學家的工作,也就少與杜林文人圈來往。然而,更重要的原因卻是他作品中的絕望和 憤怒。
在奧茲維茲的絕望處境裡支持他活下去的,就是盼望扮演這場悲劇見證人的決心。他將觀察和感受陸續寫在紙上,然後一一銷燬,只留在腦海而避免遭發現。
回到杜林,他和另一位同是倖存者的醫師Leonardo de Benedetti揭開集中營如何虐待和摧毀人體的科學報告,刊在醫學期刊。1947年,他開始在《人民之友》週刊發表有關集中營的文章。完整手稿分別給 了埃伊瑙迪、帕維瑟和金芝柏夫人(Natalia Ginzburg),反應極佳,可是埃伊瑙迪的出版社都沒興趣,最後是一家小出版社草草發行,第一版滯銷而庫存在佛羅倫斯的地下倉庫,某年水災全遭淹漬。
二次大戰後,乃至到了今天,人們一直不願去回想大屠殺這類的記憶,這一切歷史事件證明了人性可能的殘酷,既不僅屬於少數幾個民族,也不是人類的文明演化可 以消除的,而是永遠地,永遠地存在像你我這樣的所謂平凡或善良老百姓的潛意識深處。李維喊出來了,大家的痛處卻被觸及了,即使是良心知識分子也都有意無意 地迴避而不積極歡迎它的出版。
《如果這是個人類》在被拒十年後,1958年才由埃伊瑙迪出版。
50年代末期,二次大戰的災難還距離不遠,經歷過法西斯、戰爭、死亡和集中營的一代,發覺部份新一代歐洲青年開始投入當年的思考模式,新法西斯和新納粹風 潮開始蠢蠢欲動。學校的教科書還停留在過去,課本裡的歷史只記錄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因為這樣的發展,原先指望以遺忘作為原諒的文化界,才開始恐慌起來,許 多二次大戰期間的資料,包括《安妮的日記》在內,終於得以發行。初版才兩千冊的《如果這是個人類》,直到1987年為止,共售出75萬冊。
在《如果這是個人類》裡,集中營的主題一直持續著,聲音是憤怒和見證的;到了《復甦》,分貝開始下降,思考更加複雜。他的反省不再是只有少數的「壞人」,而是包括猶太人在內的集體的道德責任,恥辱和罪疚成為一再盤旋的主題。
《復甦》的「恥辱」一章最先完成於1947年,關於「所謂正直的人在他人果真做下錯事以前,早己隱約感到恥辱」的主題,到40年後他在死前發表的最後一本 重要作品《被溺斃的和被救活的》,進一步發展成對倖存者更深遠的分析,特別是他們的罪疚和恥辱。罪疚是指在某些場合中,儘管主動選擇的可能性將是渺小的, 但還是有可能時,倖存者對自己的沒有抵抗和沒有救助他人(雖然當時的情況根本不可能)而永遠承受自責。恥辱既是個人也是集體的。倖存者必須個別地承受別人 質疑的眼神:為甚麼人都死了而你還活著,同時也承受著集體的恥辱:我居然也是屬於這般禽獸的人類的其中一分子。
在這樣複雜的思考和分析後,李維開始肯定為何有些人在承受囚禁和侮辱時,可以勇敢活下來,在自由之後反而自行結束生命。他說:「自殺的行徑是人性的而不是 動物的,它是縝密思考的舉止,不是衝動或不自然的選擇。」奧地利籍哲學家Hans Mayer(別名Jean Amery)在1978年自殺,生前寫了一篇「奧茲維茲的知識份子」,警告下一代一定要抗拒冷漠和不在乎。李維在書中,也用了一整個章篇來討論這問題,結 論都是悲觀而不確定的。
這本書出版的同一年,1986年6月,奧地利前納粹分子華德翰(Kurt Waldheim)當選為該國總理,引起歐洲知識分子的一片憤怒和辯論;當然,義大利也不例外。李維在他的聖經背後寫了一首詩:
如果沒有多少的改變也不要怯懦了。/我們需要你,雖然你只是較不疲累罷了。/……再想想我們所犯的錯吧:/在我們之間有一些人,/他們的追尋還是瞎眼地出 發,/像是矇上眼布的人憑依摸索。/還有些人海盜般出航;/有些人努力繼續堅持好心腸。/……千萬別驚駭了,在這廢墟和垃圾的惡臭裡:/我曾經赤手清除這 一切,/就在和你們一樣的年紀時。/維持這樣的步伐,盼望你可以做到。/我們曾經梳開慧星的髮叢,/解讀出天才的秘密,/踏上月球的沙地,/建立奧茲維茲 和摧毀廣島。/瞧,我們並不是啥都不動的。/扛上這負擔吧,繼續現在的困惑。/千萬啊,千萬不要稱我們為導師。
這一年的年底,李維再次陷入嚴重的憂鬱症。1987年年初,在最後的一次訪問裡,他說:「過去和現在的每一刻,我總覺得要將一切都說出來……我走過迢迢的 混亂,也許是和集中營經驗有關。我面對困難的情形,慘透了。而這些都是沒寫出來的。……我不是勇敢強壯的。一點也不是!」
3月,他連續兩次前列腺手術,生理的惡化讓憂鬱症更沈重。4月8日清晨,義大利國家電視台的新聞,宣稱普利摩.李維從他家的三樓墜落死亡。
普利摩.李維不僅是奧茲維茲的倖存者,不止是書寫集中營的回憶和反思。
1995年9月,旅途行中路過倫敦,遇見了在英國遊修科學史的朋友。他說,最近才因為課堂老師的介紹,讀完一本棒極了的書《週期表》。從薩爾茲堡搭車到蘇黎士,再搭機到倫敦的途中,我也就再買一本《週期表》。
李維從沒失去他出身的化學本行。只是,在人的問題和化學的科學之間,身為科學家的他不再是看不見的觀察者,所有所謂客觀的科學都開始有了主觀的故事和歷史。李維用人文的眼神凝視科學,顛覆了幾百年在科學與人文的爭執中,永遠只有科學在打量著人文的處境。
他曾經寫詩、寫評論,也寫過完全符合嚴格西方定義的長篇小說:《如果不是現在,又何時?》。然而,大多的評論家公認《週期表》是他最成功的文學創作。這本 1975年出版的「小說」,在濃厚的自傳色彩中將化學元素化為個人的隱喻,彷如也是宣告他的記憶開始努力從集中營的經歷中再回到一切還沒發生的原點。
第一章的氬開始追溯祖先的脈絡,從古老猶太傳統到杜林的定居,而李維是最後登場的一個角色。從氫到鋼,李維渡過了他的青春期到第一份差事。這是《週期表》的第一部份,也是最愉快的人生,他發現了自己擁有傾聽的能力,而別人也有告訴一切的意願。
第二階段是磷到鈰,從他失去自由到Lager(營)處的囚禁。第三階段則是鉻到釩,談及戰後的一切,在重新適應原來城市的過程,已經失去了昔日用浪漫眼光看待化學的悠哉了。他必需面對現實的需要,重新架構自己的價值觀和視野。
碳出現在最後倒數的階段,一種「時間不再存在」的元素,是一種「永恆的現在」。特別是,李維指出,這樣的平衡狀態將導致死亡。碳和人類的肉體是不同的,它 擁有永恆的質性,李維選擇它暗喻自己化學生涯的結束和作家身分的重生,卻也不知不覺地預言了在面對創傷記憶的漫長奮鬥後,四十年的煎熬渡過了,最後還是選 擇了一種永遠平靜下去的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