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初與陳巨擘遊哈佛大學 (住張力的宿舍沙發. 在哈佛大學書店便宜買到這套:書即錄音帶
它伴我好幾天的通勤歲月 後來跟阿擘談John Cage 他說他"見過" John Cage 我羨慕得很......沒想到在紐約時報中文網讀到此篇

The Charles Eliot Norton Lectures
音樂
每個人都體會過「約翰·凱奇時刻」
報道2012年09月06日

Christian Hanse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紐約地鐵里上演約翰·凱奇的《4分33秒》。
2012年9月5日是美國前衛作曲家約翰·凱奇誕辰100周年。他打破傳統作曲技法,作品極具爭議,他影響深遠的理念是:一切皆可稱為音樂,每個人都可以創作與聆聽音樂——編注。我最近在在紐約上城地鐵A線經歷了一次特別的約翰·凱奇(John Cage)時刻。
你知道什麼是“凱奇時刻”對吧?不管你有沒有意識到,我們都有過那樣的時刻。它們隨意外事件而發生,令我們感受到一種不可思議、似乎從天而降的音樂體驗,這樣的時刻可以隨時隨地出現。今年是凱奇100周年誕辰,各種樂隊獻上了很多正式的“凱奇時刻”,比如茱莉亞音樂學院(Juilliard School)的學生們,還有“如此打擊樂團”(So Percussion)、“伊克圖斯打擊樂團”(Iktus Percussion)與日本鋼琴家Taka Kigawa,以及“弗拉克斯四重奏與朋友們”(Flux Quartet and friends)等樂隊。他們激情洋溢地演繹了凱奇的音樂,在聽眾們心中喚起了這樣的“凱奇時刻”。
![]()
但是非正式的時刻則需要等待。我自己最心愛的“凱奇時刻”發生在一年前,當時我扭傷了腳踝,去做核磁共振造影。操作人員告訴我機器的噪聲可能有點煩 人,但最後我卻忍不住專心聆聽起那台機器重複的節奏型與音調,乃至不斷變化的泛音。我非常享受這種聲音,不過到最後我發現核磁共振機的音樂其實更像早期的 菲利普·格拉斯(Philip Glass,美國作曲家,作品經常重複簡短的旋律和節奏模式,同時加以緩慢漸進的變奏,被稱為簡約音樂——譯註)而不是凱奇。
那天在地鐵上,我其實根本就沒有想到凱奇。我剛在格林威治村的一個教堂里聽完一場舒伯特的《C大調弦樂五重奏》,樂隊的表演漂亮、飽滿,我本來根本就不應該想起凱奇。擁擠的地鐵車廂一開始也不會讓我想到他。但我注意到周圍的噪音很不尋常。
在地鐵上,大部分噪音來自列車本身:它的喧鬧淹沒了人們的交談,乘客們大都默默凝視着自己的雙腳,或者閱讀,戴耳機聽音樂。但那個星期二的晚上,車廂里的人好像都在聊天,拚命想讓自己的聲音壓過列車的聲音與身邊其他人的說話聲。
我一般都不去理會這些喧鬧,但這次我身子向後一靠,閉上雙眼,做了那件凱奇經常建議人們做的事情——專心聆聽。我並沒費心去把各種對話區分開,更沒 專心聽人們到底在說什麼。我只是去把握聲音的整體:所有人聲與機械的聲音。雖然吵鬧,但我覺得它非常有音樂性,一旦開始以這種角度去聆聽,我就再也無法停 下來。
一波又一波的談話生機勃勃、音域適中,沒有最低男低音歌手,也沒有極高的女高音。但是聽一段時間就可以把各種音調區分開來,就像一個管弦樂隊。敘事的語調平緩地流動着,襯托着由爭論聲帶來的強勁激烈的節奏。
車廂里的人們至少在說三種語言,每一種都有自己獨特的旋律性與節奏感。我左邊女子的歡聲笑語瞬間改變了這塊巨大聲音掛毯的色彩,抵消了在我右邊人們的爭論。
與此同時,金屬機械的嘯叫提供一種尖銳的固定音型,與人聲相混雜,而列車在鐵軌上行駛的隆隆聲一直都是那麼輕微,是巴洛克時代數字低音(basso continuo,一種巴洛克時期的作曲方法,以低音旋律作為基礎。——譯註)的高科技現代版。列車每進一站,剎車漸弱的尖聲、車門開關的聲音、人們上下 車所帶來的音量平衡的輕微改變,還有人們繼續進行中的交談,這一切彷彿相連樂章之間的轉換。
我聽着聽着,不覺想到凱奇最著名的作品《4分33秒》,在某種程度上,它也是凱奇最受誤解的作品,它通常被描述為凱奇“無聲”的作品;就連凱奇自己 都這麼說。它也經常被那些對凱奇的音樂哲學理念毫無興趣的人用來開玩笑,他們覺得“一段無聲的音樂”這個說法根本就是自相矛盾的。
但是,儘管凱奇要求《4分33秒》的演奏者們保持安靜,他並不希望這段音樂聽上去完全是“無聲”的。這段音樂是他為鋼琴家大衛·圖德(David Tudor)所創作,首演於1952年8月在紐約伍德斯托克附近瑪沃里克音樂廳(Maverick Concert Hall)的一場小型音樂會上。這座音樂廳其實原本是坐落在樹林里的一座開放式的大倉庫,至今這裡仍在舉辦雄心勃勃的夏日系列音樂會。音樂廳的部分魅力來 自四周的聲音:鳥兒的歌唱、蟋蟀的啼鳴、風吹拂樹葉、雨落下的聲音與樂手們奏出的美妙音符融合在一起。
凱奇自從20世紀30年代起一直都在創作講求技巧的音樂,但從40年代起,他覺得音樂是可以從空氣中誕生出來的,這就是《4分33秒》的意義所在。 演出時鋼琴家打開琴蓋,靜坐30秒,蓋上琴蓋,然後再打開琴蓋,持續安靜2分23秒,作為第二樂章,之後是1分40秒的最後一個樂章(在瑪沃里克1952 年的演齣節目單里是這樣的。根據發表的樂譜,三個樂章的長度分別是33秒,2分40秒和1分20秒)。鋼琴確實沒有發出聲音,但身在瑪沃里克的觀眾們卻可 以聽到很多豐富的聲響;但是有些人將這個作品視為挑釁,大為震怒,從而影響了他們的傾聽。
一次乘坐地鐵的經歷能不能當作《4分33秒》在生活中的表演?完全可以。凱奇後來把這個作品的演出說明改編為樂譜,可以適用於任何樂器或樂隊在任何時間的演出。重讀凱勒·加恩對這部作品的精彩研究著作《並非寂靜:約翰·凱奇的<4>》(No Such Thing as Silence: John Cage’s 4’33”,耶魯大學出版社,2012年)時,我發現凱奇最後覺得這個作品根本不需要表演者。 4>
我分別聽過鋼琴家、打擊樂團、雙簧管樂手、大提琴手與管弦樂隊表演的《4分33秒》,但沒有一個版本像我此刻聆聽的、紐約A線地鐵全體發聲者的“《4分33秒:地鐵加長版》”這樣令人興奮。這場大合奏完全是概念性的,而所有參演者並沒有意識到他們在參加這場演出。
凱奇一定能理解這一幕。
“每一天我都在自己的生活與工作中應用那部作品,”1982年,他對作曲家威廉姆·達科沃斯(William Duckworth)說,“我每天都在傾聽它。”
他補充說:“我並不是坐在那裡去聽它;而是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上面,我發現它會一直持續下去。”
我和凱奇交談過兩次,一次是1992年6月的一次電話採訪,他當時在巴黎;幾個星期後我在他的一場音樂會上遇到了他,這場演出是現代藝術博物館夏日 花園系列活動的一部分。我希望等秋天到來,他慶祝80大壽的時候能再次和他交談。但在8月12日——20年前的一個星期日——他不幸死於中風。我再也沒能 做成他的採訪,只能為他寫下訃文。
當時一切都亂成一團,簡直就是凱奇的作品《羅拉托里奧》(Roaratorio,凱奇1979年的前衛風格作品,靈感來自喬伊斯的小說《芬尼根守靈 夜》,是他“偶然音樂”理論的代表作品,提琴、吟唱、朗誦與各種生活環境中的聲音混雜在一起,聽上去如同瘋狂混亂的集合。——譯註)的媒體版。編輯們把凱 奇帶着花生醬三明治去參加高級派對之類軼事傳真給我,打電話讓我別忘了寫他在藝術和舞蹈方面的貢獻;同事們紛紛打電話問我:“你聽說這個那個了嗎?”我一 邊忙着核實摩斯·肯寧漢(Merce Cunningham,美國著名舞蹈編劇,是凱奇的長期男友——譯註)是否希望被列為凱奇尚在人世的伴侶(後來他說不願意);一邊想着該怎麼把凱奇非凡的 藝術生涯說得盡量簡潔客觀。
寫完那篇訃告之後,當時在《每日新聞》當音樂評論員的蒂姆·佩奇打電話說要過來為紀念凱奇喝一杯,還說來我家路上可以順便買半打啤酒。30分鐘後,他出現在我家門前,手裡拿着一張白色紙條說:“你看這個。”
那是他買啤酒的收據。價錢正好是4.33美元。
你知道什麼是“凱奇時刻”對吧?不管你有沒有意識到,我們都有過那樣的時刻。它們隨意外事件而發生,令我們感受到一種不可思議、似乎從天而降的音樂體驗,這樣的時刻可以隨時隨地出現。今年是凱奇100周年誕辰,各種樂隊獻上了很多正式的“凱奇時刻”,比如茱莉亞音樂學院(Juilliard School)的學生們,還有“如此打擊樂團”(So Percussion)、“伊克圖斯打擊樂團”(Iktus Percussion)與日本鋼琴家Taka Kigawa,以及“弗拉克斯四重奏與朋友們”(Flux Quartet and friends)等樂隊。他們激情洋溢地演繹了凱奇的音樂,在聽眾們心中喚起了這樣的“凱奇時刻”。

Chris Ramirez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約翰·凱奇的《4分33秒》是為1952年瑪沃里克音樂廳的一場演出而作,音樂廳離紐約伍德斯托克不遠。
那天在地鐵上,我其實根本就沒有想到凱奇。我剛在格林威治村的一個教堂里聽完一場舒伯特的《C大調弦樂五重奏》,樂隊的表演漂亮、飽滿,我本來根本就不應該想起凱奇。擁擠的地鐵車廂一開始也不會讓我想到他。但我注意到周圍的噪音很不尋常。
在地鐵上,大部分噪音來自列車本身:它的喧鬧淹沒了人們的交談,乘客們大都默默凝視着自己的雙腳,或者閱讀,戴耳機聽音樂。但那個星期二的晚上,車廂里的人好像都在聊天,拚命想讓自己的聲音壓過列車的聲音與身邊其他人的說話聲。
我一般都不去理會這些喧鬧,但這次我身子向後一靠,閉上雙眼,做了那件凱奇經常建議人們做的事情——專心聆聽。我並沒費心去把各種對話區分開,更沒 專心聽人們到底在說什麼。我只是去把握聲音的整體:所有人聲與機械的聲音。雖然吵鬧,但我覺得它非常有音樂性,一旦開始以這種角度去聆聽,我就再也無法停 下來。
一波又一波的談話生機勃勃、音域適中,沒有最低男低音歌手,也沒有極高的女高音。但是聽一段時間就可以把各種音調區分開來,就像一個管弦樂隊。敘事的語調平緩地流動着,襯托着由爭論聲帶來的強勁激烈的節奏。
車廂里的人們至少在說三種語言,每一種都有自己獨特的旋律性與節奏感。我左邊女子的歡聲笑語瞬間改變了這塊巨大聲音掛毯的色彩,抵消了在我右邊人們的爭論。
與此同時,金屬機械的嘯叫提供一種尖銳的固定音型,與人聲相混雜,而列車在鐵軌上行駛的隆隆聲一直都是那麼輕微,是巴洛克時代數字低音(basso continuo,一種巴洛克時期的作曲方法,以低音旋律作為基礎。——譯註)的高科技現代版。列車每進一站,剎車漸弱的尖聲、車門開關的聲音、人們上下 車所帶來的音量平衡的輕微改變,還有人們繼續進行中的交談,這一切彷彿相連樂章之間的轉換。
我聽着聽着,不覺想到凱奇最著名的作品《4分33秒》,在某種程度上,它也是凱奇最受誤解的作品,它通常被描述為凱奇“無聲”的作品;就連凱奇自己 都這麼說。它也經常被那些對凱奇的音樂哲學理念毫無興趣的人用來開玩笑,他們覺得“一段無聲的音樂”這個說法根本就是自相矛盾的。
但是,儘管凱奇要求《4分33秒》的演奏者們保持安靜,他並不希望這段音樂聽上去完全是“無聲”的。這段音樂是他為鋼琴家大衛·圖德(David Tudor)所創作,首演於1952年8月在紐約伍德斯托克附近瑪沃里克音樂廳(Maverick Concert Hall)的一場小型音樂會上。這座音樂廳其實原本是坐落在樹林里的一座開放式的大倉庫,至今這裡仍在舉辦雄心勃勃的夏日系列音樂會。音樂廳的部分魅力來 自四周的聲音:鳥兒的歌唱、蟋蟀的啼鳴、風吹拂樹葉、雨落下的聲音與樂手們奏出的美妙音符融合在一起。
凱奇自從20世紀30年代起一直都在創作講求技巧的音樂,但從40年代起,他覺得音樂是可以從空氣中誕生出來的,這就是《4分33秒》的意義所在。 演出時鋼琴家打開琴蓋,靜坐30秒,蓋上琴蓋,然後再打開琴蓋,持續安靜2分23秒,作為第二樂章,之後是1分40秒的最後一個樂章(在瑪沃里克1952 年的演齣節目單里是這樣的。根據發表的樂譜,三個樂章的長度分別是33秒,2分40秒和1分20秒)。鋼琴確實沒有發出聲音,但身在瑪沃里克的觀眾們卻可 以聽到很多豐富的聲響;但是有些人將這個作品視為挑釁,大為震怒,從而影響了他們的傾聽。
一次乘坐地鐵的經歷能不能當作《4分33秒》在生活中的表演?完全可以。凱奇後來把這個作品的演出說明改編為樂譜,可以適用於任何樂器或樂隊在任何時間的演出。重讀凱勒·加恩對這部作品的精彩研究著作《並非寂靜:約翰·凱奇的<4>》(No Such Thing as Silence: John Cage’s 4’33”,耶魯大學出版社,2012年)時,我發現凱奇最後覺得這個作品根本不需要表演者。 4>
我分別聽過鋼琴家、打擊樂團、雙簧管樂手、大提琴手與管弦樂隊表演的《4分33秒》,但沒有一個版本像我此刻聆聽的、紐約A線地鐵全體發聲者的“《4分33秒:地鐵加長版》”這樣令人興奮。這場大合奏完全是概念性的,而所有參演者並沒有意識到他們在參加這場演出。
凱奇一定能理解這一幕。
“每一天我都在自己的生活與工作中應用那部作品,”1982年,他對作曲家威廉姆·達科沃斯(William Duckworth)說,“我每天都在傾聽它。”
他補充說:“我並不是坐在那裡去聽它;而是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上面,我發現它會一直持續下去。”
我和凱奇交談過兩次,一次是1992年6月的一次電話採訪,他當時在巴黎;幾個星期後我在他的一場音樂會上遇到了他,這場演出是現代藝術博物館夏日 花園系列活動的一部分。我希望等秋天到來,他慶祝80大壽的時候能再次和他交談。但在8月12日——20年前的一個星期日——他不幸死於中風。我再也沒能 做成他的採訪,只能為他寫下訃文。
當時一切都亂成一團,簡直就是凱奇的作品《羅拉托里奧》(Roaratorio,凱奇1979年的前衛風格作品,靈感來自喬伊斯的小說《芬尼根守靈 夜》,是他“偶然音樂”理論的代表作品,提琴、吟唱、朗誦與各種生活環境中的聲音混雜在一起,聽上去如同瘋狂混亂的集合。——譯註)的媒體版。編輯們把凱 奇帶着花生醬三明治去參加高級派對之類軼事傳真給我,打電話讓我別忘了寫他在藝術和舞蹈方面的貢獻;同事們紛紛打電話問我:“你聽說這個那個了嗎?”我一 邊忙着核實摩斯·肯寧漢(Merce Cunningham,美國著名舞蹈編劇,是凱奇的長期男友——譯註)是否希望被列為凱奇尚在人世的伴侶(後來他說不願意);一邊想着該怎麼把凱奇非凡的 藝術生涯說得盡量簡潔客觀。
寫完那篇訃告之後,當時在《每日新聞》當音樂評論員的蒂姆·佩奇打電話說要過來為紀念凱奇喝一杯,還說來我家路上可以順便買半打啤酒。30分鐘後,他出現在我家門前,手裡拿着一張白色紙條說:“你看這個。”
那是他買啤酒的收據。價錢正好是4.33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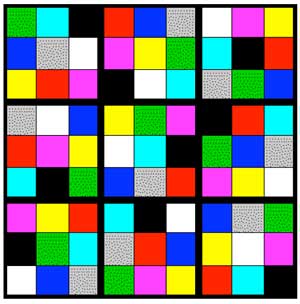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a talk I gave at the recent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a talk I gave at the recent 